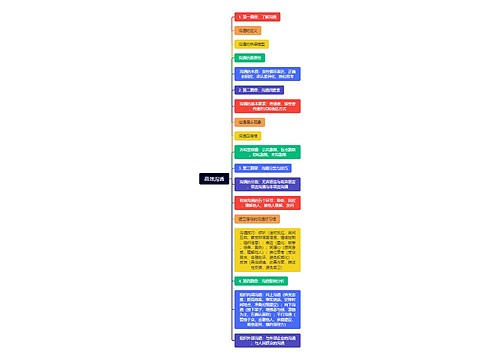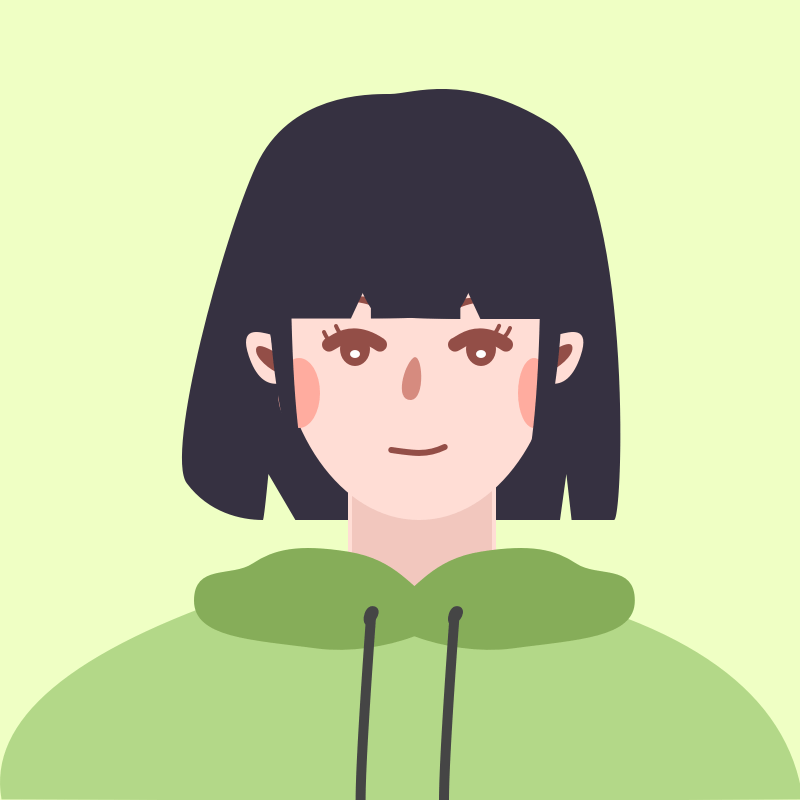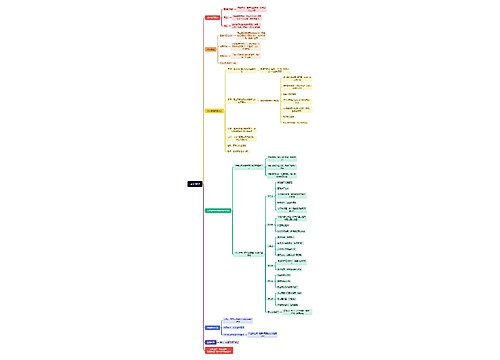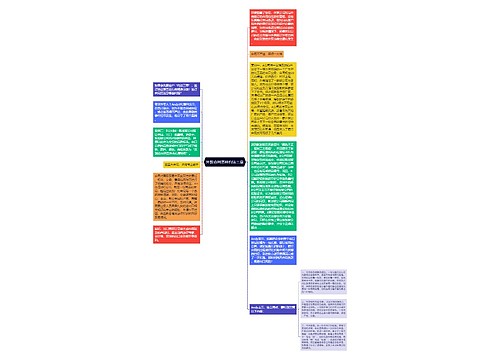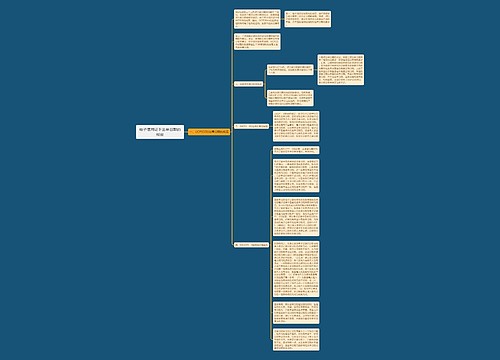对于处理一个具有涉外因素的案件来说,本案的法律适用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关键性问题。究竟适用国际公约,还是当事人选择适用的法律,抑或是内国的相关实体法律来作为解决涉案多式联运纠纷的准据法,是正确裁决的前提。根据国际私法原则,适用法律的一般顺序遵循以下排列:首先适用已缔结的国际公约,然后是在不违反内国强行法规定的基础上适用当事人选择的法律,最后按“最密切联系原则”来确定案件所适用的准据法。本案涉及包含海运与空运方式的多式联运,在界定多式联运经营人的赔偿责任和责任限额方面,各大公约与国内立法的精神是一致的。《联合国国际货物多式联运公约》第十九条,以及我国《海商法》第一百零五条的规定,均指明了当货物在多式联运某一运输区段发生灭失或损坏的情况下,赔偿事宜应适用调整该区段运输方式的有关法律规定。这即是所谓的“网状责任制”,也是目前国际上通行的原则。涉案货物尚未交付给收货人以前,在巴西圣保罗机场清关受阻而致损,应认定此时仍然在航空运输过程中。空运始发地与目的地(韩国与巴西)均为调整航空运输的《华沙公约》的缔约国,这符合公约的适用条件。且《华沙公约》第四章关于联合运输的规定中第三十一条第一款规定,“对于一部分用航空运输,一部分用其他运输方式联合办理的运输,本公约的规定只适用于符合第一条件的航空运输的部分”。因此,如果在涉案空运中发生了货…
毁损灭失的情况,则应适用《华沙公约》来调整相关当事人之间具体的权利义务关系。
然而问题的关键是,本案中被运输的货物并未“灭失”或“损坏”,涉案经济损失是由货物的迟延交付所造成的,而迟延交货并不属于“网状责任制”的适用对象,换言之多式联运迟延交货所导致损失的法律适用与迟延事故的具体发生区段并无关联。因此无须再考察迟延交货究竟发生在多式联运中的哪一个运输区段。涉案争议围绕迟延交货而展开,这一争议是与整个多式联运相关而非与哪一个特定运输区段相联系,故应排除《华沙公约》对于整个多式联运法律关系的调整。
接下来须审查当事人对适用法律有否约定。空运单与提单存在着法律性质上的差别。由于空运速度快,运输期间短,故尽管法律未明令禁止空运单进行转让,但多数空运单上都载明是不可转让的,因而其也就不具备物权凭证效力。实质上在空运方式下也无须利用转让单证的方式来实现货物交易。空运单是随空运货物同行的,故并不像海运提单那样在运输期间由托运人或收货人所持有,因此空运单背面条款之效力认定也与海运提单有所不同。海运提单背面条款尽管为承运人单方制作,缺乏合意性,但提单持有人是托运人或收货人,他们至少有机会了解提单背面条款内容;而涉案空运单的持单人是承运人本身,在接受了托运货物后仅将空运单正面传真给了托运人,因此无法认定其背面条款具有双方意思表示一致的特征,而背面条款载明所适用的《华沙公约》也就不能被认定为双方合意选择适用的法律。?既然不适用公约和当事人选择的法律,最终就必须运用“最密切联系原则”来确定涉案准据法。
本案中,合同订立地、起运地以及被告住所地均在中国,无疑中国法应作为与案件具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被确定为准据法,具体适用海商法中关于多式联运的规定。但是,与《联合国国际货物多式联运公约》相比,海商法中并未规定在多式联运的情况下,货物迟延交付导致损失时承运人应承担的赔偿责任。法院最终在判决里援引了民法通则的相关条文,追究了当事人迟延交付货物的违约责任。应该说,这样的处理结果是合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