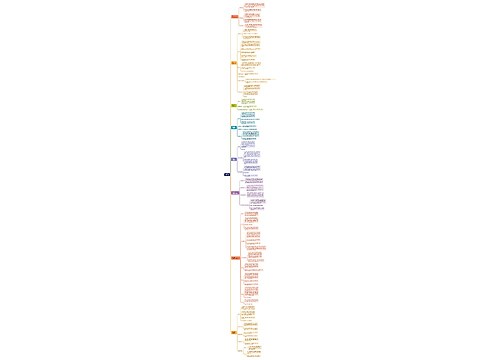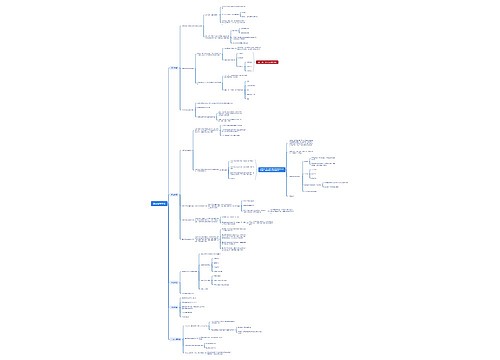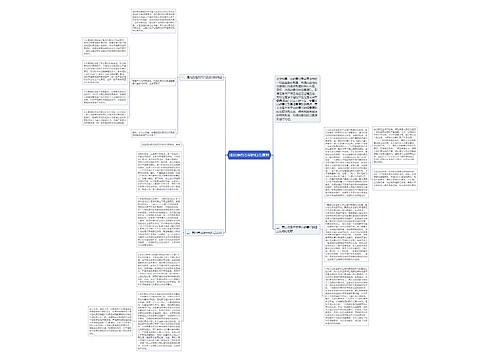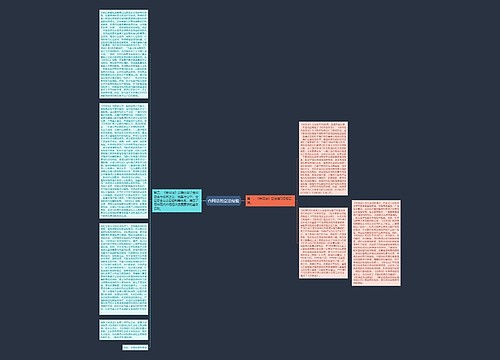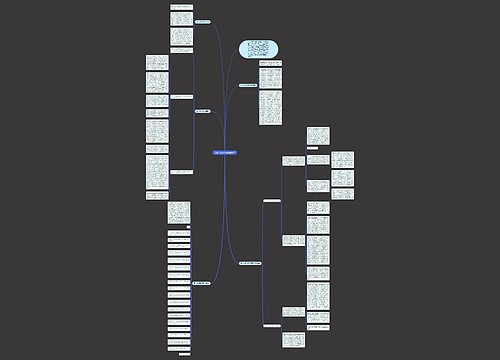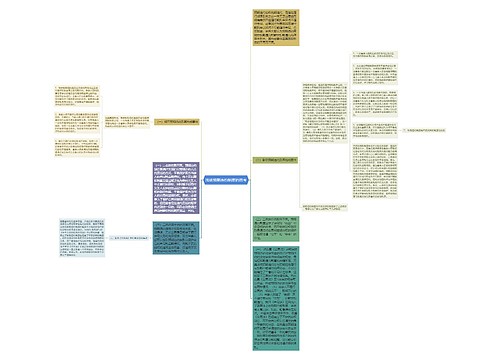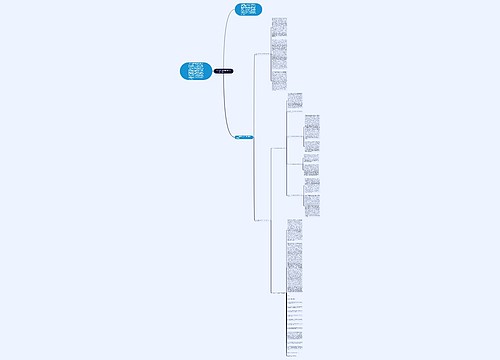合同自由,既包括合同内容的自由,也包括合同形式的自由。然而,在我国的很长一段历史时期,不仅合同内容受到诸多不合理的限制,而且,连合同形式也被“强制”了。按照《经济合同法》的规定, 除即时清结者外, 经济合同应采用书面形式。《涉外经济合同法》也规定, 涉外经济合同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合同形式的“枷锁”无疑加重了当事人的缔约成本,束缚了交易的开展,是对私人自治的严重干涉。为了卸下了这一沉重的“枷锁”,统一《合同法》不仅确立了合同形式的自由原则,而且还创造性地规定了形式欠缺的治愈规则。按照《合同法》第36条的规定,即便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要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合同,但当事人未采用书面形式也不必然导致合同无效。在此时,如果出现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情况,则该合同仍然成立。
在肯合同形式自由的同时,统一《合同法》上关于合同自由的内涵也不断丰富。在1999年颁布的《合同法》中,决定是否订立合同;选择与谁订立合同;订立怎么样的合同;如何订立合同以及合同的变更或解除这些内容都属于当事人自治的范畴。按照《合同法》第128条的规定,甚至连合同纠纷的解决方式也可由当事人自由约定。 此外,《合同法》的规范设计上,也普遍采用了任意性规范的模式,从而给予了私人自治以广阔的空间。
“我们自由,是因为我们生活在民法之下。”而“契约自由在整个私法领域具有重要的核心地位” .因此,统一《合同法》颁布的意义,不仅是在于确立了市场交易的统一规则,更为重要的是,其确立了“合同自由”的基本原则。“公法易逝,私法长存”。实际上,私法之所以能绵延不断,不断繁荣的基础就在于《合同法》所确立和坚守的“自治”之精神。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说1999年统一《合同法》的颁布是我国民事立法,乃至整个经济生活走向“自治”的标杆和旗帜,值得永远铭记。当然,合同自由亦非绝对。现代合同法已然从合同自由向合同公正转型,因此,如何妥当地纯化合同自由,实现《合同法》向正义的升级,则无疑是我们当前需要重点思考的问题之所在。(西南政法大学·黄忠)
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2009年11月24日第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