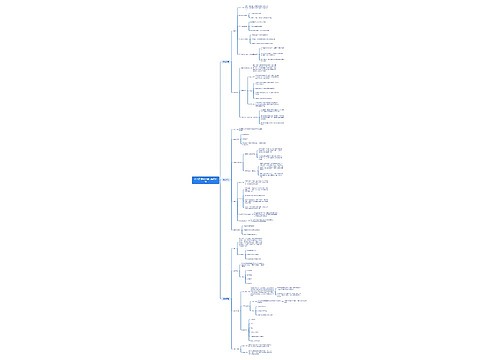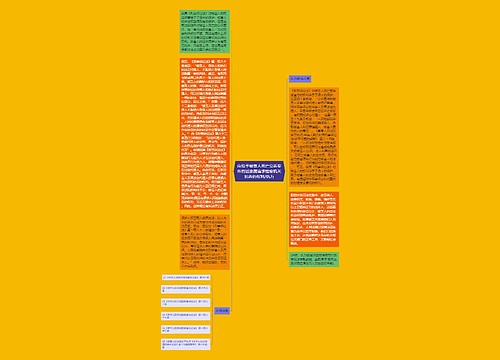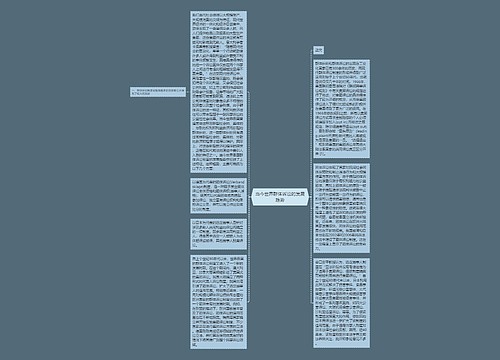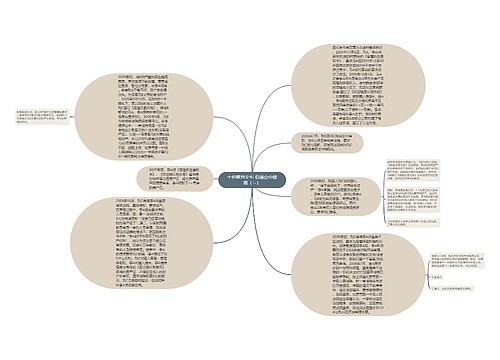律师与法官作为法律职业工作者,当然都必须按照法律的规定进行诉讼代理活动和审判活动。从总体来看,无论是律师,还是法官,一般都受过一定程度的法学教育。在法学教育过程中,所接受的法律知识也大体上是一致的。无论律师,还是法官在对待某一具体案件中所涉及的法律问题时,其认识也是基本上一致的。但律师和法官之间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和法律适用方面仍然存在着差异。律师与法官在诉讼活动中,他们的思维方式有所不同,对案件的认识也就有所不同。这种不同的主要原因在于,律师与法官各自的社会角色不同。律师是“民间的法律工作者”,法官“是国家的法律工作者”。在我国,法官甚至还具有“官方”特色,在某些情况实际上是“政府的”法官。因为法官与政府权力和政治权力都有着十分密切的内在联系。在日本,法官被认为是“官方的”法曹。律师则是“民间的法曹”。
在诉讼中,法官的主要工作就是认定事实、适用法律、作出裁判。法官在诉讼中,无论在刑事诉讼,还是民事诉讼中,都应当处于绝对中立的地位,超脱于公诉人和被告人,超脱于原告和被告。律师则不一样。律师在诉讼代理活动中,总是为其中一方的利益进行诉讼代理。尤其是在民事诉讼活动中,要么作为原告的诉讼代理人,要么作为被告的诉讼代理人。这就决定了律师总是以被代理人的意志进行着诉讼代理活动。当事人所期望的利益最大化,也就决定了律师也必须以自己的法律知识和诉讼技巧来实现被代理人的最大利益,当然这种追求必须是在法律规定或允许的范围内。律师必须在最大的限度内争取被代理人的利益和权利,在最小的范围或最小的程度上,让被代理人承受责任和界定义务。
基于律师的职业特点,尤其作为诉讼代理人的这种特殊角色,因此,律师在诉讼活动中会从尽可能有利于被代理人的角度去理解法律的规定。我们知道,法律无论它规定得多么详细也不可能将社会上的万千现象加以具体规定,总会给人们以解释的空间和余地。而且法律作为一种规定或表述,总会因解释不同而有所不同。尽管不是对每一个条文都可以作出完全不同的解释,但对每一个条文规定的解释往往因为人们的认识角度不同而存在着差异。作为当事人代理人律师也就必然要利用法律的解释空间,最大限度地为被代理人争取最大的利益。因为律师作为代理人时,只能作为一方当事人的代理人,这就决定了律师在代理被代理人进行诉讼时,仅仅是从被代理人的角度,也只能从被代理人的角度来思考如何为自己的被代理人争取最大的利益,因此,他的视角是单一的和单向度的。
而作为法官,他们是超越当事人双方的,是作为中立的裁判者来审视整个案件事实,从超越当事人各自的利益的立场来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的。因此,他的思维与律师的思维方式有所不同。法官的理念是根据秉件的事实情况,正确的适用法律。这样必然会全盘地来考虑整个案件的情况,包括原、被告当事人之间的衡平,而不会从一方当事人的角度来考量案件事实。在刑事诉讼当中法官将会充分考虑公诉人和被告人双方的陈词。在许多情况下,法官甚至会将一个特定的具体案件置于整个社会的宏观背景之下,来考虑案件的处理,适用法律。当法律的规定存在自由解释空间时,法官的解释将是基于一种衡平和中立的解释,与律师尽可能最大化地争取一方被代理人的利益是有所不同的。
律师在诉讼活动中向法院的陈述,向法院提出的事实材料,都是从有利于为被代理人争取最大利益的角度出发的。律师除了代理当事人向法官提出事实主张外,代理人还将主动地去挖掘和发现对当事人有利的事实。而且,律师还会向法官提出自己对案件法律适用的主张,尽可能以自己的法律认知去影响法官对案件的法律认知,使法官没有自己的独立见解。法官对案件事实认定和适用法律的认知也许与一方或双方律师的法律见解不一致时,律师将全力以赴地力图改变法官的认识。另一方面,诉讼制度要求法官从诉讼双方对立中去发现真实和真理。这也是诉讼制度的基本功能之一。
我们注意到,在我国个别法官对律师,主要是诉讼中的律师,存在着一种偏见,认为律师不是在追求和实现法律的正义,而是在法院的审理和裁判制造麻烦。造成这种偏见的原因之一,就在于法官以自己的社会角色认知来认识律师,而不是从律师的角度来理解律师对法律的认知,从而把最大限度维护当事人的利益视为一种不道德的行为。因此,把律师视为对裁判案件顺利裁判的障碍,认为律师会使案件复杂化,即通常所说的“搅混水”,这些法官的眼里当事人是灰色的,律师也是灰色的。
这种认识当然是错误的。因为一方面,作为律师,利用自己的法律和诉讼技术为当事人谋求最大的法律利益就是在追求和实现法律正义。法律既然有利益空间,那么,在这一空间中寻求最大利益也是正义的。另一方面,还应当看到,个人利益的最大化与法官所理解的法律正义尽管有可能存在着冲突和不一致,但由于当事人双方利益的冲突,加之诉讼的对抗制结构,使得具有不同且对立利益的当事人通过律师在追求利益最大化时,即为各自的被代理人实现利益的最大化时,就形成了一个彼此冲突的事实和法律认知。原告的律师要为原告实现法律上的最大利益,被告的律师也要为被告实现法律上的最大利益,这样,实际上就形成了一种法律认知上的制约。而法官正是在双方律师因不同的利益而追求法律的最大利益的过程中,了解、理清法律事实,了解应当怎么样处理才能够衡平当事人双方的利益,才能够实现法律规定所内涵的正义和立法者的真实意图。中立的法官是在对立的利益最大化追求中,找到法律所要求的利益平衡点,公正地作出裁决。因此说法官总是在诉讼中向律师学习法律,吸取律师的法律智慧是有道理的。
由于律师的职业所决定,因此对律师的职业道德要求也与法官有所不同。律师的职业道德就是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地维护被代理人的利益,减少被代理人的损失。律师的职业道德并不要求从全社会的利益,甚至从局部社会利益来加以考虑。要求律师也必须超脱被代理人的利益,从社会的利益和群体的利益来考虑如何认识法律和适用法律是不正确的。对于那些被人们,也包括为法官们十分憎恨、厌恶、唾弃的人,律师也会为其主张权利,尽力陈词。律师是理性的。在人们的感情认识的背景下,律师的背景难免带有“灰色调”。法官的角色决定了法官的基本职业道德要求是中立裁判,不偏不依的。只要做到中立,不偏不倚,全面的审视和适用法律,就基本满足了法官的基本道德要求。在人们的眼里,法官的背景色调是亮丽的,只要自己不去把它抹黑。
在买践中,我们注意到这样一种现象:法官在审理案件是往往以自己的职业道德和自己的角色来对待律师,要求律师也要按照自己的职业道德要求和角色来处理案件。这是一种角色错误。法官应当从律师的角度来理解律师,而不是指责和压制律师。在开庭审理当中,有的法官常常会压制双方的代理律师,而双方的代理律师又想尽可能的在法官面前,陈述自己的主张、理由和认识。这样在法庭上常常会发生一些冲突,庭审往往成为法官与律师争吵的场所。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除了案件对法官的压力、法官干预形态外,不能理解律师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实际上,律师的道德要求就是为被代理人争取最大的利益。要追求最大的利益,就必然要穷尽案件事实当中对自己被代理人最有利的所有事实和理由,会把所有事实全部在法庭上予以提出,要求法官予以斟酌。在对案件事实的认识上和对法律的认识上,律师也会提出各种各样的理由和主张来维护被代理人的利益。作为法官就应当认真、耐心、仔细地倾听双万诉讼代理人的意见,而不是认为自己已经清楚了,去压制双方代理律师的法律意见和陈述。作为法官,他是在双方当事人充分陈述的基础上来作出裁判的,而不是先入为主,简单化地对案件有一个认识态度。在没有全部听取代理律师对案件和对法律的陈述以后,不可能作出最为公正的法律裁判。这一点在实践中是比较突出的。个别法官中“官”意识或权力支配意识也影响了法官平和地对待当事人和律师。笔者在日本和香港旁听审判时,注意到这些法官对待当事人和律师的态度与内地法官有所不同。这也是许多参加或旁听过海外庭审的人的共同感受。在案件审理法官律师就像是开法律研讨会一样,与双方律师进行十分细致的交流。当然,这种差异的存在也与我国的诉讼体制有关和审判观念有关。
总体而言,律师的社会定位是弱者的助力者、支持者。律师最大的社会作用是维护权利,通过维权来实现正义。我们应当意识到,对权利的侵害往往来自于目的正当、理由正当,甚至维护公民权利,为公民谋福利的权力的行使过程中,行政权和司法权,警察权、检察权和审判权的行使都有可能。这些权力在行使当中一旦超越法律的规定无论实体违法,还是程序违法,都可能对公民权利造成侵害。这些权力的行使便不是天然就是公正的。审判权的行使也不是自然就是中立的。对于这些权力的制约除了其他权力的制约以外,律师利用法律所赋予的权利制约权力也是一种十分有效的制约力量。律师通过自己的法律知识使当事人能够充分利用法律上权利去维权,实现对违法行使权力的对抗。没有来自律师的维权,刑事被告人权利就会受到侵害;民事审判就可能偏跛。
在我国的大量立法中,有许多是部门立法,即由一个主要实施该法律或相关权力的机构来制定法律或修改法律。这种部门立法的最大弊端在于所制定的法律或法规是从实施法律或法规的部门的考量角度或利益出发的。尽管法律或法规在起草过程中,会征求多方意见,但一旦法律或法规的基本架构一旦形成便难以修改,因为法律、法规一旦确定框架或基本架构以后,所有的修改都将受到该基本架构的约束。例如,目前正在制定的《民事执行法》就是由最高人民法院来主要起草的。而法院就是民事执行法的主要实施者。即使最高法院在主观动机上会充分考虑民事执行中各种利益,但客观上是很难摆脱部门视角的限制的。要避免这种部门立法的弊端,除了采用吸收多方专家组成专门立法起草小组起草外,由民间起草然后加以综合、平衡也不失为一个好的方法。由于律师的特殊维权角色,律师作为一种制约权力的社会力量应当积极地参与各种主要法律、法规的制定,提出自己的法案。
笔者在日本学习期间发现,只要是制定或修改日本的主要法律,日本全国律师联合会总要提出自己的法案。日本法务省在最后提交的法案中也一定会吸收律师法案的内容。因为,如果不采纳律师法案的内容,也就是说,如果日本律师不同意的话,该法律就很难得以顺利实施。因为律师法案往往代表了大多数弱者或单个国民“散在”的利益。律师的这种代表性与人民代表的代表性是有所不同的。在日本律师的代表性更具有“民间性”和“在野性”。与此相对,至今我国律师尚未提出过自己独立的法案,顶多只是在个别场合对法案发一些议论。在我国律师没有成为一种相对独立的社会力量。这一点与法治发达国家的律师有所不同。当然,导致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原因大概与我国低阶段的民主、法治发展有关。
以上不深不浅论及了律师与法官的诸多不同,并还借此稍加展开。笔者所谈到的这些不同对于我们正确处理律师与法官的关系,以及正确理解律师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不同是有很多方面,但有没有相同之处?
由于律师和法官具有社会的其它职业者所没有的点。正是由于律师和法官的这些共同点,使他们成为法律共同体的一个组成部分。从职业道德操守看,虽然有不同之处,但也同样有相同之点。这些相同之点又不同于人们所共同遵守的社会道德。即在法律工作中依照法律的理性要求去规范自己的行为,服从法律的理性定言命令是最高的职业道德要求。因此,在法律工作中应当与政府权力和政治保持相对的隔离,以保持自己对法律的忠诚。
作为一个具有以上共同特性的法律共同体的组成部分,律师和法官应当相互理解,而不是相互对立。人们也应当把他们视作一个文化概念上的共同体,从法律共同体的角度来看待律师和法官。正因为律师和法官的共同特性,律师与法官应当可以相互换位,这样更有利于思维相度和视角的互补。正如笔者前面所提到,律师是“民间”的法律工作者,而法官是“国家的法律工作者”,两者的社会角色是不同的。律师和法官的换位,不仅仅是基于思维相度和视角的互补,还在于通过律师法官的一体化或法官从律师中选任,从而实现公民对司法裁判的参与。公民对司法的民主参与的机理是,律师的民间角色使律师实际上成为广大公民最直接的维权代言人,律师成为法官作为案件的裁判者,也必然在裁判中,体现广大公民的意见。有律师经验和思维习惯的法官与没有律师经验和思维习惯的法官相比,相信前者对法律的适用更贴近社会民众。因此,从政治的高度看,法官从律师中选任是法治民主化的一种重要途径。目前,在我国尽管有法官转换为律师,但还尚未有律师向法官转换的。即使有也是极个别情况。今后,在我国的司法改革中应当将法律工作者一元化作为一项十分重要的改革措施提出来,并加以实施。日本目前正在轰轰烈烈地推行着司法改革,其中一项主要的改革提案就是所谓“法曹一元化”。
从法律共同体的角度看,在进行司法改革时,也应当统一考量。也就是说,司法改革并不仅仅限于法院和法官制度的改革,应当全盘地来考虑律师制度、法官制度和法学教育制度。律师和法官以及其他法律工作者的培养都应当统一地考虑,统一培养的基准和过程。律师和法官在法律认识上,尽管出发点和思维方式上有所不同,但都应当尽可能在法律规定的本质范围内来理解法律。这就要求有一个法学教育的共同认知,不至于律师和法官在对法律的理解上相差太远,甚至完全对立。因此,不管是律师还是法官以及其他法律工作者,应当经过同样的法学培养模式和路径。为了培养共同的法律认知,统一的司法考试是一个较好的方法。目前,实际上只有律师的司法考试是全国统一的,检察官、法官等法律工作者则没有纳入统一的司法考试之中,这一点无疑应当进行改革。

 U582679646
U582679646
 U882673919
U8826739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