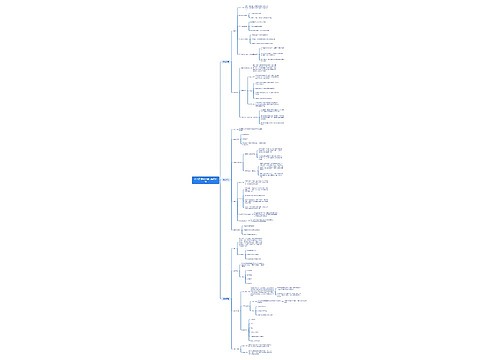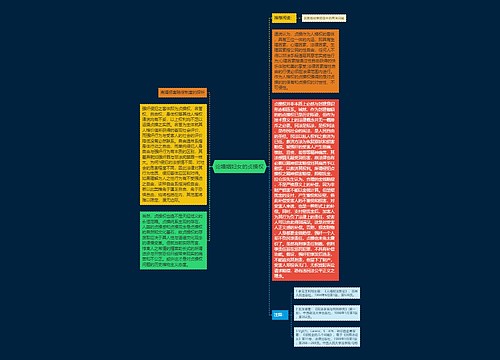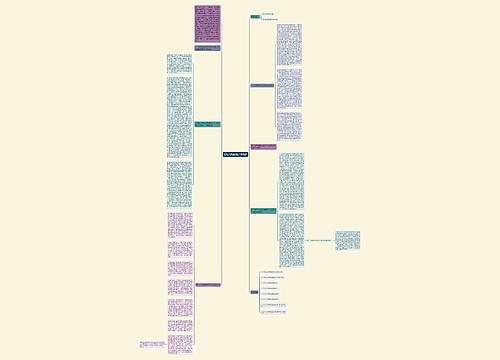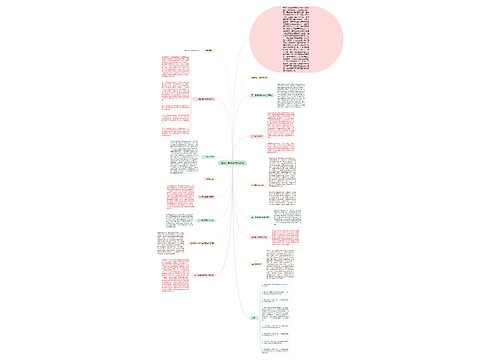我致电: “……这以前‘奉诣成婚’都是要诏告天下的啊,你倒好,不但不告还连同我送红包的权利都剥夺了。”
女友颇有些无奈: “一个女人有了孩子,那里还有自我?起初他不同意结婚:说时机不成熟,劝我把孩子做掉,这是我生命中第一个孩子啊-我怎么忍心杀了他(她)。这一僵持就是几个月,眼看肚子一天天大起来,要不是我以两条命相逼,他现在还是个快乐的单身汉。”
我的心突然有被丝线拴扯的痛,搜索过全部安慰人的话,最后只吐出一句:“没事了,你的孩子会比你更漂亮的,好好保重身体啊,我还盼着做干妈呢。”
女友的婚姻总算成就了,当前的法律对“奉子成婚”这种行为没有明令禁止,唯一涉及到的法条是《婚姻法》第五条:结婚必须男女双方完全自愿,不许任何一方对他方加以强迫或任何第三者加以干涉。可她的情况一来构不上胁迫,(因为女友并没有以男方及其亲属的生命财产的安全相威胁),二来也不属于第三者的干涉(因为胎儿在未出生时还不具备民事行为能力,不能作为独立的民事主体而存在)。法律的问题解决了,虽说孩子不比圣旨,可在这种语境下多多少少还是有点强制的味道,我感觉到莫名的悲哀。
2002年9月1日生效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已经明确了男性的生育权,并且随之产生了妻子私自堕胎丈夫获赔的判决。我对此类判决理解是:法院并不否认《妇女权益保障法》中关于妇女有不生育自由的权利,但根据“新法优于旧法”的原则,男性的生育权比女性的不生育自由权更应受到保护。笔者不是女权主义者,只是相信来自头顶星空的规则。前述吾友的故事还算不幸中的万幸-双方的关系纳入到了法律的庇护之下。但设想女友的情况更糟一点,男方仍然不答应结婚,那女友的生育权该如何来保障?生育权的主体最终是谁?法律到底保不保护未婚妇女的生育权?胎儿有民事权利能力吗?基于以上问题,笔者将在本文中作出分析回答,意在抛砖。
第一块砖:生育乃性之成本
辅助生育技术自1978年为英格兰蓝爱德伍德医生首创成功后,性就不再是使妇女怀孕的唯一方式了,但怀孕仍然不可避免地要被计算在性的成本之内。波斯纳先生将性所服务的目的(性的收益)分为三组:生育的、享受的和联谊的。杨立新教授将性利益定义为一种独立的人格利益。并进一步阐述他具有人身自由和精神自由的双重属性,男女双方通过作为的方式实现这种利益,通过不作为的方式保持它。从而获得自身的幸福和快乐。笔者非常赞同这两位的观点,但更愿意从悲观的角度来剖析。“生一个不想要的孩子就是为性快感支付的一种沉重的税”,性的利益为双方共享,但因为生孩子的妇女要承受心理上的焦虑、生理上的不适和只有她自己才了解的痛苦,而依目前的医学技术还不能把受精卵移植到男人身体里去孕育,所以这种税最终是由妇女来承担的(男人当然也可以以他们损失了几枚精子作为辩护)。
这跟共同犯罪的构成非常类似(《圣经》里面淫欲罪也是7宗罪的一种):主观方面,男女有两情相悦的共同故意;客观方面,实施了偷尝禁果的行为(性交);犯罪主体,是二个16岁以上具有完全行为能力的人。按照《刑法》此二人应该被科以同等的刑罚。但事实是,如果两人没有结婚,男方一旦认定了不要孩子而女方又没有做“未婚妈妈”的勇气或者不愿意象吾友那样采取极端方式的话,她唯一的出路恐怕就是用中止妊娠来放弃自己的生育孩子的权利。相反,如果女方不愿意要自己身上的这块肉,还必须经男方的同意,否则就在法律上构成侵权。总之,“犯罪”所得利益归男方所有,后果一概由女方来承担。
在立法上如此重视父权夫权以及所有男性的权利,而对妇女的关切不敏感,这很容易让人假定有相当多的法律必定是男性努力的结果,他们成功地把妇女的利益(最广义的)再分配给了自己。
第二块砖:避孕失败怎么办?
按照波斯纳先生的分类,吾友性所服务的目的也许是享受的或者联谊的,反正不是生育的。现实生活中,造成这种后果的原因多为避孕失败,于是产生了避孕失败由谁负责的问题,是由女方“一人做事一人当”吗?男方的责任仅仅是道义上的吗?可否追究避孕药具销售、生产商的责任?医院要求做流产手术必须由丈夫签字的规定可行吗?
第三块砖:独身女人生育权不应保障
《吉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规定“达到法定婚龄决定终身不再结婚并无子女的妇女,可以采取合法的医学辅助生育技术手段生育一个子女”。本条规定看似立法对于非主流群体的人文关怀是对女性权利的尊重,但实质上是从立法上纵容女性的不理智,并且以牺牲伦理道德和孩子的权益作为代价。首先,站在作为绝对弱势群体的孩子们的角度去思考,他们没有能力要求大人们做什么或不做什么,他们只能在多年之后恨自己的母亲-把自己当作宠物一样来满足自己认为需要的生活方式,而不考虑能否给予自己健康的成长环境。我想任何一个母亲都不愿意为自己养一个仇人吧。其次,由于此条例规定不构明确,造成操作难度大。“决定终身不再结婚”,如果在按此法生育后又想结婚,以此条来限制就违反了《婚姻法》结婚自由的规定和《立法法》的规定,而同意结婚即意味着这条规定的限定条件落空。再次,笔者认为生育权乃公民与生俱来的自然权利,不反对非婚生育(法律也没有明令禁止)。相反我国《婚姻法》有规定“非婚生子女享受与婚生子女同等待遇”,这是因为无论结婚与否孩子都能寻找到自己的父源,除孩子被合法收养,他与自己的亲生父亲的权利义务关系不会阻断。而以采取合法的医学辅助身育技术手段生育的子女,在法律上是没有父源的,他(她)生下来就“只知其母,不知其父”并且永远没有父亲,社会伦理遭破坏的同时孩子心灵上的残缺也难以避免。真可谓:解决问题一个,带来问题一堆。
第四块砖:胎儿的权利
胎儿在母亲的子宫里宣言:您可以决定不要我,但当您决定要我的时候就请您对我负责!也许有人会说你这个标题本身就是空穴来风,我国《民法通则》规定:公民的民事权利能力始于出生终于死亡。那么未出生的胎儿在法律上不享有任何权利。笔者承认,但不得不提醒读者大人一个唯一的例外,那就是我国《继承法》第二十八条关于胎儿预留份额的规定。这个特别法的规定在某种意义上推翻了普通法。笔者以为胎儿的权利应得到进一步的延伸,那就是限定一个做父母的最低标准。
有件事总让我百思不得其解:我们为什么容许任何人不经训练就担负人类最重要的养育后代的职责,尤其是在存在一些无知的父母可能严重扭曲下一代的人格的状况下。父母拥有摧毁生命、戕害孩子灵魂的无比力量。想想看,医生如果未经教育与训练根本不可能执业;甚至我们得经过考试才能开车上路,以免祸及无辜,在所谓文明的现代社会,公路上还拉起了重重的保护网。可是,即使是多无知的家伙,只要会性交,就可以成为父母。也就是说,为人父母的惟一资格限制就是具备猪的能力,然后就可以合法成为中国人的父母。即使我们找个人来家里修侧所,也要有比这更高的资格。
我们无法选择自己的父母,但可以选择改变现状,在有生之年不断地提升自己爱的能力,在作父母之前进行基本的训练。可能有人会说这样的举措对于有着13亿人口的中国来说真是太艰难了,却正是因为我们是人口大国才要更加地注重人口素质(包括身体的精神的和心理的)的提高,从限定一个做父母的最低标准做起,从绝望中寻找希望,一个民族终将辉煌。
法律尽管浩如烟海,也是有边界的,国家的司法资源也是有限的。来自人内心的约束才是最完美的法则,尤其对天下的父母和即将要做父母的人而言。
方丈说:天下事了又未了,何须以不了了之。世外人法无定法,然后知非法法也。四川大学法学院·李游

 U582679646
U582679646
 U882673919
U8826739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