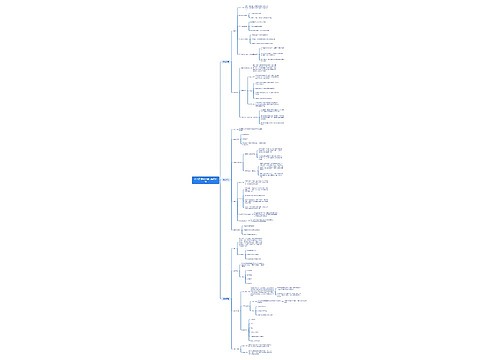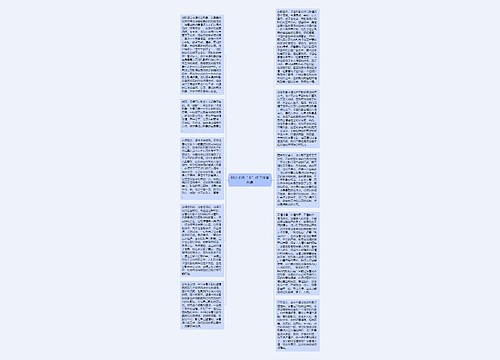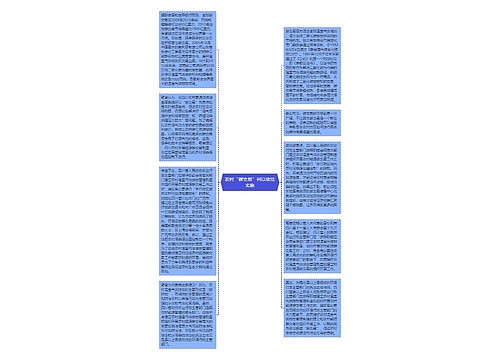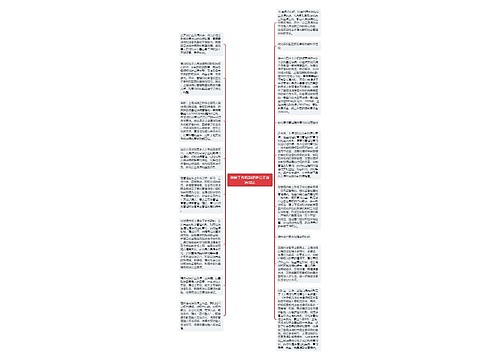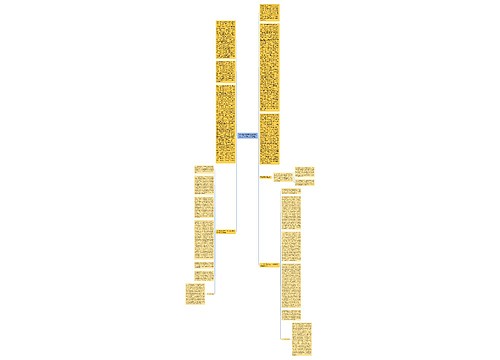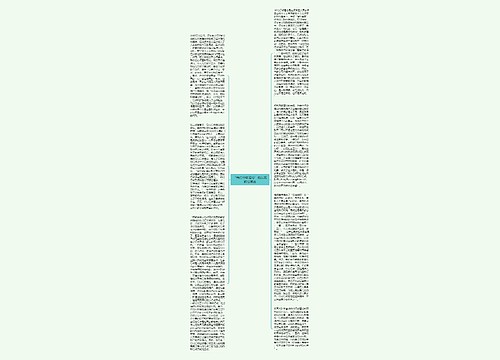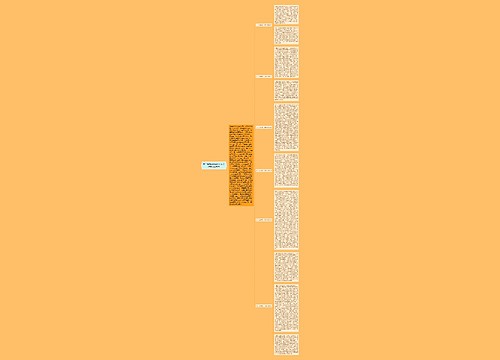皇帝,在今人的心目中是古时“至高无上”的专制主义化身,其手操刑、赏“二柄”,挟持天下,生杀予夺,任由喜怒;臣民敢有不唯唯诺诺,逆来顺受者,便会遭家破人亡之祸。最为今人乐道的还有皇帝那三宫六院、锦衣玉食、身居九重、无以伦比的“排场”生活。当我们将“皇帝”想得如此简单时,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古代没有法律可以制约皇帝,皇帝是“说一不二”的。而没有法律,正是“专制主义”的特征。一些史学名家,比如易中天也这样认为:中国古代没有真正的法律。
其实,中国古代皇帝与法律的关系如果真像我们想象或误解的那样,就不是“一部二十五史从何谈起”,而是“五千年的文明从何谈起”的问题了。如果我们穿越时空与古人对话,我想,即使一般的百姓也会对我们今天的误解感到不解,因为从大量的史料中我们可以看到即使皇帝也生活在法律的制约之中。
先说立法,中国古代社会也不是皇帝一个人说了算的。众所周知,自秦统一后,“律”是中国古代王朝统一颁行的法律,颁行律的权力归属中央,其是新王朝“与民更始”的标志。历朝历代对律的颁行格外精心,一般的程序是,王朝建立或新帝即位后,下诏制定或修订法律。参加的人员由朝中重臣、地方大员、精通经学和律学的专家组成。据《晋书・刑法志》记,晋文帝制定《泰始律》时,由贾充等十四人“典其事”(即主持修律之事),在制定的过程中,对历代颁行的律之体例、条文、实践状况进行了分析,又广纳朝臣、律学家的建议,最终形成20篇720条27657言(字)的《泰始律》,最后由皇帝下诏颁行天下。
闻名中外的唐律,其制定经过更是不以皇帝的意志为转移。贞观与永徽时期,受命领衔制定唐律及其律疏(即律的解释,元人将唐律文与疏文合编为一体,称为《唐律疏议》)的宰相长孙无忌,在《进律疏表》中,提到参与修律者的名单有19人,更为重要的是,长孙无忌说唐律是历史经验的结晶,是对历朝历代的法律“沿波讨源”的结果:“摭金匮之故事,采石室之逸书”。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对国家或皇家所藏的历代档案中有关“律”的原始记载进行了分析研究,采其精华。这样一部凝聚着历史经验的法律,果如制定者自信的那样“信百代之准绳”。可见,中国古代的立法,并非是皇帝“出言即法”,在立法的过程中,皇帝要受到“祖宗之法”即以往“故事”的制约,制度没有给他“为所欲为”的机会。
再说一下皇帝与司法。时下有一种“很学术”的说法,即中国古代的典章制度,都是帝王或统治者粉饰世道的样子货,在实践中并没有真正地实现,尤其是皇帝,具有最高的司法权,可以任意破律毁法。实事求是地说,中国古代的皇帝,从制度上说是有“立断权”的。一桩案件,在没有进入司法程序之前,皇帝不仅有权裁断,而且可以不顾法律的规定―――这也许就是人们说皇帝“口含天宪”的原因。但是,立断的案件毕竟偶然且有限,如果案件的审理进入了法定程序,皇帝也就不那么好干涉了。
汉文帝时期,有一位著名的廷尉(类似现在的最高法院院长),名叫张释之。一天,汉文帝出巡至中渭桥,有一人从桥下跑出,惊了文帝的坐骑,侍卫将此人捉拿,文帝虽然生气,但是没有“立断”,而是将其送到张释之那里。在审讯中,这位“犯罪嫌疑人”说自己是长安县人,听到清道之声,便躲避在桥下。等了很长一段时间,看到仪仗已经过去,便误以为皇帝的乘舆车骑也已过去,于是从桥下跑出,不想却正冲撞了皇帝的坐骑。张释之认为此种状况按令属“犯跸”行为,跸,为禁止人通行的条令。汉“乙令:‘跸先至而犯者罚金(铜)四两’。”于是张释之按令处此人罚金四两。文帝“怒曰:‘此人亲惊吾马,吾马赖柔和,令他马,固不败伤我乎?而廷尉乃当之罚金?’”在文帝看来,廷尉对惊了自己坐骑的人处罚金了事,实在是处罚过轻。但张释之据“令”力争,告诫文帝:“法是天子与天下人约定的共同守则。廷尉是为天下守护法律的人。如果皇帝当时‘立诛’此人,而不是交与我廷尉处断,那大家也无话可说。但是案子既然送到了法司廷尉处,我只能按法办事。”文帝沉默良久,只好说“廷尉议是”。
如果说汉文帝是一位明君,如此后的唐太宗、明太祖、清康熙、雍正、乾隆等一样,克己守法并不足以说明法律对皇帝的约束,那么,我们还可以看到如隋炀帝那样暴虐的君主竟也有同汉文帝一样的“守法事迹”。《隋书・源师传》记:隋炀帝任命源师为大理少卿(类似最高法院副院长)。炀帝荒淫,常常恐惧被暗杀,于是敕令宫中卫士须臾不得离开职守。但卫士中的一位长官,私自让卫士外出。炀帝将这位不听话的长官交给大理寺(中央审判机关)审判。源师“据律奏徒”,即根据律文判以徒刑,炀帝则下令处斩。源师劝谏炀帝的话与张释之如出一辙:“如果陛下当场杀之,则不涉及到法律。但陛下把他送到了大理寺,大理寺就要按法律办事。”隋炀帝也如汉文帝一样“乃止”,服从了法官的裁断。
从上述的立法、司法的事例中可以看出,中国古代皇帝与法律的关系绝非一句“皇帝不受法律约束,皇权凌驾于法律之上”可以概括。作为一种绵延了两千余年的“皇帝制度”,皇帝与法律的关系是复杂的、相互制约的。正是这种复杂性,造成了中国古代的专制与法律并存。
法国启蒙学者魁奈这样描述中国古代的“专制”:“用专制一词来称呼中国政府,是因为中国的君主独掌国家大权。专制君主,意指主管者或当权者,因为这个称呼可以用于执行法定绝对权力的统治者,也可以用于篡夺专制权力的统治者,而后者执政不论其好坏,其政府都不受基本法则的保护。这样就有了合法的专制君主与为所欲为的或不合法的专制君主之分。”魁奈显然将中国的皇帝归为“合法的专制君主”,因为“中国的制度建立于明智和确定不移的法律之上,皇帝执行这些法律,而他自己也审慎地遵守这些法律。”
也许是受了魁奈的影响,二十世纪初,梁启超作《开明专制论》,以为中国儒、墨、法三家皆为“开明专制主义”。正是这“开明”两字,将中国古代的皇帝权力合法化,而又将其置于了法律的约束中。今人那种“有专制,无法律”的简单思维模式,正是我们误解中国古代皇帝与法律关系的原因。

 U582679646
U582679646
 U882673919
U8826739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