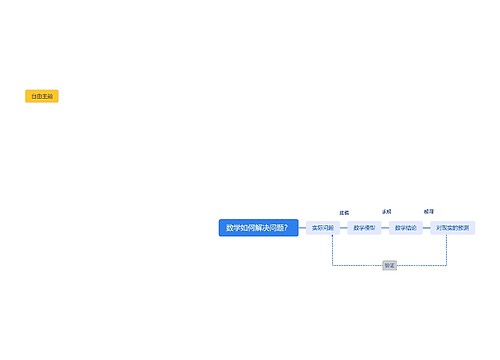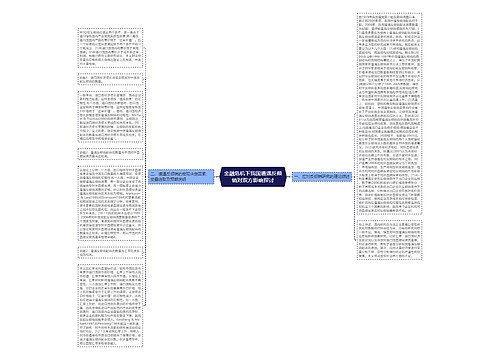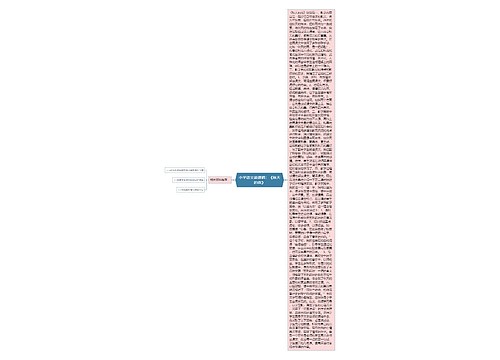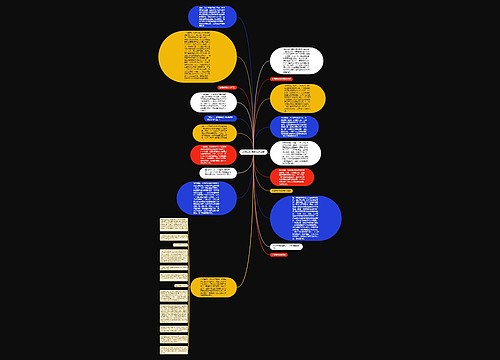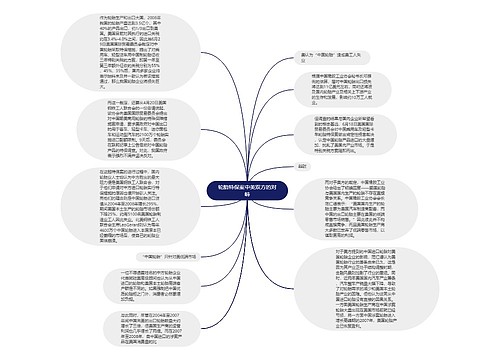前文述及倾销的客观影响是进口国国内产业寻求反倾销的直接诱因,反倾销对进口国国内产业具有相当大的保护功能是进口国反倾销的直接推动力,然而,如果没有从法律上、机制上找到可以运用的工具或者相关规定,则反倾销的前述功能也是很难达到的。
根据WTO《反倾销协定》,进口国可以对损害性倾销(1njurious Dumping)即造成进口国国内产业损害的倾销行为采取反倾销措施。协定具体设定了认定倾销和损害的实体和程序规则。在采取反倾销措施过程中需符合相应的实体和程序规则。这些规则赋予了进口国主管机构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协定还特别规定在出现反倾销争议时,如果WTO审理争议的专家组认为协定的有关规定可以做出一种以上允许的解释时,如进口国主管机构的措施符合其中一种允许的解释,则该措施应被认定为符合本协定。除了有关进口国主管机构开展反倾销调查及采取反倾销措施的自由裁量权的规定之外,协定还对发起反倾销调查做了规定,但这些规定显然不能完全阻止进口国主管机构对并没有造成损害的倾销或者对根本没有倾销的销售发起反倾销调查。
值得注意的是,在从法学视角理解反倾销时,需要将程序性问题纳入考虑,因为它们往往会影响相关利害关系方的实体权利和义务,比如,在反倾销程序中,如果调查机构认定某出口厂商系不合作,则该厂商被征收的反倾销税通常会比没有被认定为不合作的厂商要高,尽管该厂商也许根本就没有从事倾销行为。当然,WTO所设立的争端解决机构对各成员履行其在《反倾销协定》项下的义务的监督,有利于在一定程度上控制各成员对其自由裁量权的不适当运用。但是,另一方面,争端解决机制在解决反倾销争端方面的作用仍然是有限的(邓德雄,2003)。 此外,倾销通常被视为是不公平贸易行为,甚至与出售假冒商品、盗用商业机密、虚假广告等行为一起被纳入不公平竞争手段的行列(查尔斯·R·麦克马尼斯,1997)。有些国家的反倾销立法还区分不同国家,对某些特定国家采取歧视性做法,这些歧视性做法既有实体方面的,也有程序方面的。其中最为突出 的是美国和欧盟等采取的非市场经济国家或转型经济国家的做法,这些做法通过实体和程序的紧密结合,能够产生与实际情况并不相同的结果,而这种结果并不违反各自的国内立法,或者说这是其各自国内立法的目的所在,起码是受其各自国内立法所纵容。
GAO(2006)对美国25起既对中国又对市场经济国家采取的反倾销措施做了对比分析,指出适用于中国的统一税率的平均数比适用于市场经济国家的“所有其它”税率(all others duty rate)的平均数高出了61个百分点(98%~37%)。需要指出的是,这是在中国出口厂商并没有完全放弃应诉,有些时候甚至极为积极应诉并积极配合调查的情况下得到的税率,这种税率与市场经济国家企业的“所有其他”税率相比,差距尚且如此之大,更不用说其与在同等水平上应诉并合作的市场经济国家的企业相比的差距有多大了。
Cliff Stevenson(2005)也认为欧盟委员会目前非市场经济国家/转型经济国家的反倾销做法可能会存在替代国价格和成本较高的情形;但同时指出欧盟委员会非市场经济国家/转型经济国家的做法没有进行改革的任何有力的理由。对于出口国而言,只要非市场经济国家或者转型经济国家做法存在,则很难在反倾销应对中取得客观真实的结果。
可以说,WTO规则及各国反倾销立法为进口国实现通过反倾销保护国内产业竞争力提供了法律上和机制上的依据,同时也较容易被进口国及其国内产业不适当利用甚或滥用。近年来,有关反倾销领域的双边和多边摩擦不断、争端四起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这种不适当利用甚或滥用。实际上,据统计,反倾销争端的数量超过了在任何其他WTO协定项下发生的争端的数量(Edwin Vermulst,2005)。
五、反倾销规则的产生和实施中的政治考虑与反倾销的蔓延
如前所述,反倾销规则的产生和具体内容并不完全是建立在经济学理论的基础之上。在反倾销规则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夹杂着很多政治方面的考虑。艾尔·L·希尔曼(2005)等人运用政治经济学理论,将贸易保护政策内生化,对西方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政策进行了研究,认为自利行为或称为利己行为的原则同样也适用于政策的制定者(或者是潜在的政策制订者,如政府中职位的竞选者)。政治支持的动机成为了保护主义决定的基础。胡方(2001)专门对日本和美国经济摩擦的理论与实态进行了研究,认为日美经济摩擦及其激化正是日美经济实力相互消长的表现。“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直到目前,美国的对外贸易赤字一直都处于十分高的水平,这不仅使美国对其国际经济地位感到忧虑,而且还成为世界经济动荡不安的一大根源。”由此可见,经济摩擦包括运用反倾销等贸易保护措施在内所导致的摩擦,并不必然就是简单的倾销与非倾销、公平与不公平贸易的问题,它应当说有更深层次的经济和政治原因。

 U182637395
U182637395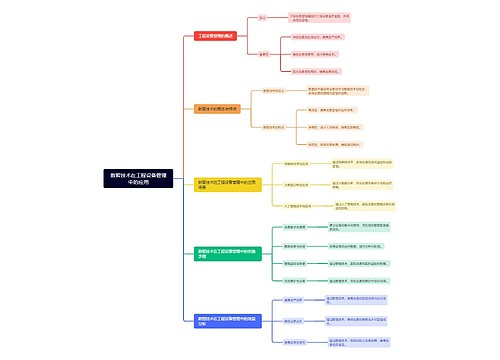
 U575789758
U5757897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