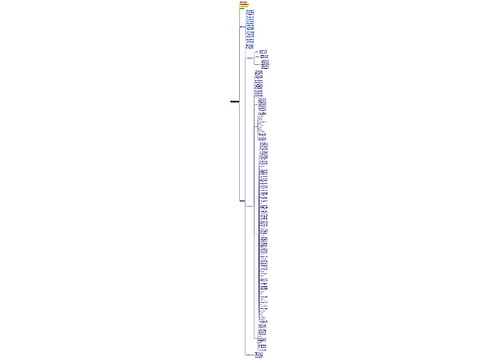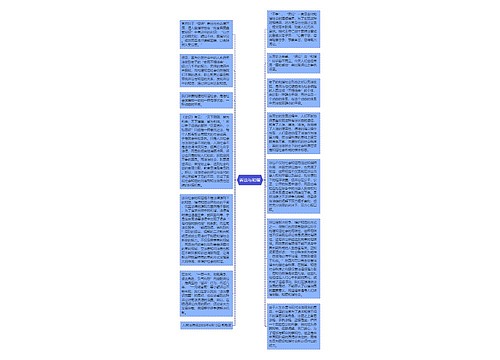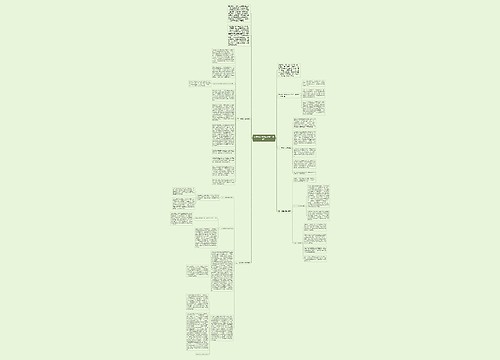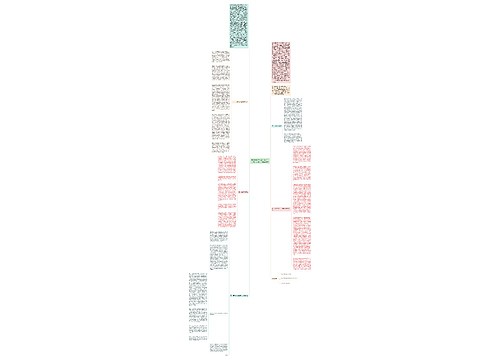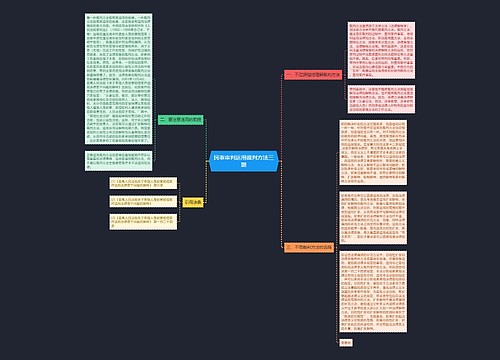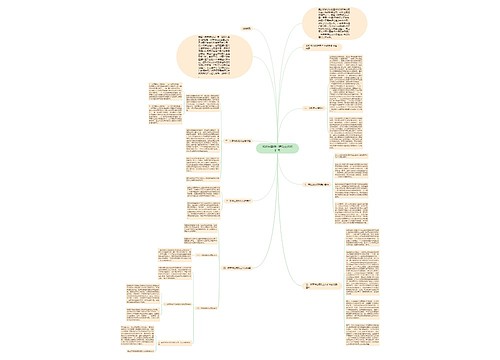从前文的分析不难看出,严格执法和司法造法之间难免发生冲突,而在中国现实状况下,强调严格执法可能比任何人为地在法律之外搞所谓“创新”都重要得多。如此说来,本案中齐某某的受教育权岂不是得不到保护?我们认为,解决“无法可依”的难题在于刷新宪法是政策性纲领而不能在法律文书中直接引用的传统观念,即改变宪法在司法实践中被“虚置”状况,实行宪法司法化。
宪法司法化主要是指宪法可以像其它法律法规一样进入司法程序,直接作为裁判案件的法律依据。一个制定法只有在法院解释之后才成为真正的法律。宪法如果不进入司法领域,则只是表面的法,而真正的法,只能在法院的判决中发现。其实宪法司法化已不是什么新鲜玩艺,早在1803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审理治安法官马伯里诉麦迪逊一案(Marbury V Madsion)时,首席大法官马歇尔(John Marshall)在该案的判决中宣布:“立法机关制定的与宪法相抵触的法律无效”。此案奠定了美国司法审查制度(Judicial Review),即联邦法院法官可以宪法为依据审查联邦国会的立法和行政部门的命令是否符合宪法。由此开创了宪法司法化的先河。继美国之后,奥地利于1919年创立了宪法法院。法国在1946年建立了宪法委员会,作为宪法的监督和保障机关。1958年,经过一系列的改革,法国建立了宪法会议,这一组织,积极介入公民宪法权利争议的案件中,以有影响力的案例实现了对公民宪法权利的保障。德国在1949年通过基本法,建立了独立的宪法法院系统专属处理权力机关之间的宪法争议和个人提出的宪法申诉。目前,宪法司法化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司法实践的经验总结,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建立了宪法诉讼的机构和程序。宪法司法化之所以受到世界各国的青睐主要是基于以下几点。
首先,凡是法律都应当作为裁判的准则由某一特定的机构反复适用,不能在法院适用的法律不是真正的法律。宪法是法,它应当同其他法律一样都具有直接的法律效力,宪法的效力不一定都体现在惩罚上,而是要表现在它是判断一切纠纷的最高标准上,它是最高的法的价值判断。其明显的例证便是美国的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一案中最高法院确立了“隔离不平等”原则推翻了Plessy V. Ferguson一案中确立的“隔离且平等”的原则, 宪法成为判断案件的最高准则和价值依据 .宪法规定了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等具有全局意义的问题,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树立法律权威首先要树立宪法的权威。因此,对于违宪争端,应当建立以司法为中心的违宪审查制度。
其次,宪法司法化是公民法律意识、权利意识增强的必然要求。我国法制化的进程就是公民权利意识逐渐觉醒的过程。没有救济就没有权利,没有救济的权利就不是权利。宪法是母法,我国宪法规定的各项基本权利绝大多数已由其他法律具体化和量化,公民对已经被具体化和量化的基本权利的侵犯可以直接寻求司法救济,但是对于没有被具体化和量化的基本权利的侵犯,如果不从其它法律的源头即宪法中寻求司法救济,那么基本权利不再是基本权利,甚至不再是权利。在权利意识逐渐觉醒的时代,这些“沉睡”的权利不再是“无主物”。宪法司法化是司法最终解决或者最终救济原则的必然要求。宪法救济使得公民的某些处于“悬空”状态的基本权利有了法律保障,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宪法司法化是公民基本权利保障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最后,从我国法律规定及司法实践来看,宪法司法化并非没有其生存空间。宪法第五条规定:“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 然而如何认定“相抵触”、如何追究违宪行为?宪法司法化恐怕是最重要的一环。再者,正如有人指出:“宪法不作为裁判依据的所谓惯例其实缺乏明确的法律的规定,现行立法并未明确规定宪法不能作为法院裁判的依据。宪法不入诉讼的障碍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司法机关长期形成的‘作茧自缚’式的司法惯例 .” 此次最高人民法院的批复无疑是对旧观念的突破,如果能以此为契机,对我国宪法司法化作出可行的制度安排,那么就重视程度而言本案的确是中国宪法司法化的第一案。其实宪法司法化一直存在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我国民事诉讼法上规定的“选民资格案件” 、以及我国宪法解释制度的存在就是我国宪法司法化的一个明显例证。
综上所述,宪法司法化是严格执法和司法造法的调和剂。严格执法在个别情况下会导致“无法可依”,而司法造法则会引起裁判的随意性。宪法司法化恰恰介于两者之间,它能使宪法的母法地位与法官的自由裁量有机结合,即填补了严格执法中的空白之处,又防止了法官司法造法的主观随意性。在宪法争端日益趋多的今天,宪法不应保持沉默,建立以司法为中心的违宪审查制度势在必行。
[①] 王利明:《司法改革研究》,法律出版社2001版,第219页。
[②] 王利明:《司法改革研究》,法律出版社2001版,第233页。
[③] 王利明:《司法改革研究》,法律出版社2001版,第227页。
[④] [美]本杰明?卡多佐:《司法过程的性质》,苏力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84页。
[⑤] [美]本杰明?卡多佐:《司法过程的性质》,苏力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80页。
[⑥] “…… We conclude that in the field of public education the doctrine of ‘separate but equal’ has no place. Separate educational facilaities are inherently unequal. ……”
节选自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347 U.S. 483(1954), MR.CHIEF JUSTICE WARREN delivered the opinion of the Court.
[⑦] 这一判决的依据是美国宪法第14条修正案。该条规定:“……No state shall make or enforce any law which shall abridge the privileges or immunities of the United States; nor shall any States deprive any person of, liberty, or property, without due process of law……”
[⑧] 其一是1955年最高人民法院在给新疆省高级人民法院的批复中认为宪法不宜引为论罪科刑的依据;其二是1986年最高人民法院在给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的批复中对是否引用宪法条文判案采取了回避的态度。正是这两个司法解释的误导,中国法院形成了拒绝适用宪法判案的思维定势和司法惯例。
[⑨] 刘武俊:《以诉讼激活弥合“宪法鸿沟”》,载法制日报2001年8月19日第3版。
[⑩] 如1998年北京市民族饭店员工王某等16人换届选举时,民族饭店没有给他们发放选民证,也没有通知他们参加选举。于是,他们以该饭店侵犯宪法上规定的选举权为由,向北京市西城区法院提出起诉讼,要求饭店承担法律责任。
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研究生·王超 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周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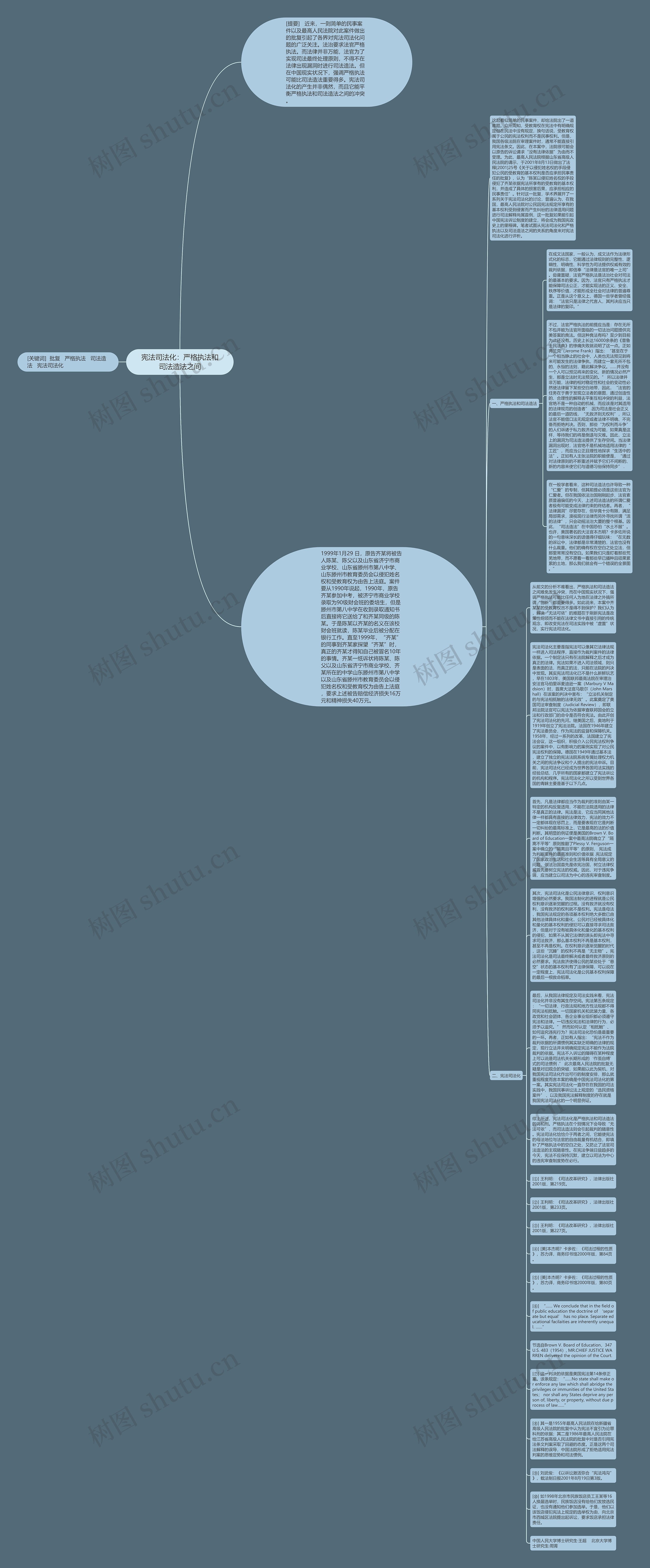
 U633687664
U633687664
 U882667602
U8826676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