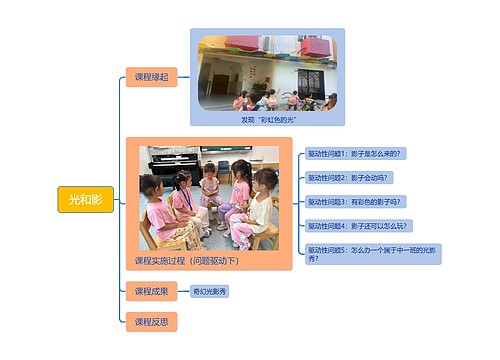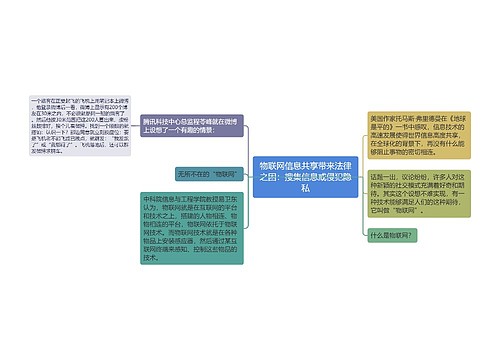上述异议引出了一个值得认真探讨的问题——检察机关在抗诉监督的过程中能否对已被法院认定的案件事实重新调查取证?能否依据调取的新证据提出抗诉?欲给出上述问题的正确答案,需要对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抗诉的法定情形作深入的剖析。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85条对抗诉的法定事由总共规定了四种情形,即(1)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的;(2)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3)人民法院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裁定的;(4)审判人员在审理案件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与民事诉讼法第179条规定的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法定事由相比,抗诉监督的法定事由少了“有新证据足以推翻判决、裁定的”一种。在检察机关可以提出抗诉的四种情形中,与认定事实错误直接相关的是第一种情形。
原裁判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实际上是指法院在缺乏充分证据的情况下对当事人争议的案件的主要事实作出了认定。这主要包括四种情形:其一是法院依据一方当事人提供的显然是不充分的证据就认定其主张的事实存在,如仅依据与当事人一方有亲戚关系的两个证人提供的对该当事人有利的证言就轻率地作出认定;其二是对同一争议事实,主张事实存在的一方提出了本证,否认的一方则提供了相应的反证,法院在未能确定反证不真实的情况下就采信了本证。之所以把这种情形也归入主要证据不足,是由于反证的存在,本证的证明力已被抵销或严重削弱;其三是法院作为认定案件事实依据的主要证据存在着重大瑕疵。第三种情形虽然给人以认定事实证据充分的表象,但重大瑕疵一旦被揭露,法院的裁判便如沙上建塔,顷刻倒塌。其四是指法院未依法调查收集证据,致使一方当事人主张的事实因证据不足而未被认定其存在。对当事人主张的事实不予认定,实际上也是法院关于事实上主张的一种评价和判断,其产生的法律后果与法院认定当事人主张的事实不存在并无二致,因而不予认定其实也是法院认定事实的一种形态。当法院依法有义务调查收集证据而未履行其义务,致使主张事实存在的一方当事人因举证不足而不被认定时,不能不认为法院是在证据不充分的情况下就过早地作出了对事实的认定。
在上述认定事实主要证据不足的四种情形中,第一、第二两种检察机关即使不调查收集证据也能够提出抗诉,而对第三、第四两种情形,检察机关为了形成正确而有力的抗诉意见常常需要调查取证。笔者认为,在以下两种情形下,检察机关依据其调查所获得的新证据提出抗诉,不仅是履行抗诉监督的职能所必须的,而且具有明显的合理性和正当性。
(一)检察机关为证明原裁判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存在的重大瑕疵而对证据及相关的事实进行调查
当检察机关怀疑原裁判所依据的主要证据为虚假或伪造时,检察机关通过调查取证以确定自己的怀疑是否有根据显然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如果不进行必要的调查,检察机关就难以揭露当事人伪造或变造证据的事实,就无法针对这类错误裁判提出确有根据的抗诉。
法院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存在重大瑕疵包括证据形成的过程不合法和证据系伪造、变造两种主要情形,因而检察机关抗诉时对证据的调查也主要针对这两种情形进行。在实务中检察机关有不少通过调查获得新证据抗诉成功的实例。前者如汪太平诉涉县燃料公司房屋损害赔偿案件。在该案件中涉县法院依据涉县质量监督站付林榜出具的鉴定结论判决燃料公司赔偿房屋维修费5万余元,燃料公司向涉县检察院申诉后,检察机关对鉴定结论这一主要证据的形成情况进行了调查。查明鉴定人付林榜无《鉴定作业证明》,无从事鉴定的资质,又是一个人前去鉴定,违反了必须由两名以上鉴定人参加鉴定的程序规则。后者如刘小娥诉刘蔚华要求返还房屋一案。在该案中,上诉人刘蔚华于二审期间向法院提供了一份房屋所有人刘英芳生前所立的遗嘱,遗嘱中表示去世后房屋由我妹刘蔚华继承,法院委托西安市公安局对遗嘱进行鉴定,鉴定结论为“署名刘英芳的遗嘱书是刘英芳所写”。二审法院以这份遗嘱为主要证据判决系争的三间房屋由刘小娥(系刘英芳之养女)、刘蔚华各继承一半。终审判决宣告后,西安市人民检察院受理刘小娥申诉后委托公安部、陕西省公安厅对这份存在诸多疑点的遗嘱进行了鉴定,结论均为“署名刘英芳遗嘱的字迹不是刘英芳所写的”〔3〕
(二)法院对依法应当由其调查收集的证据未调查收集时,检察机关可以针对这类证据调查取证
我国民事诉讼第64条确立了证据的调查收集以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为主,法院在必要时给予协助的模式,一方面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另一方面又规定“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由于民事诉讼法关于法院应当调查取证的情形规定得较为原则,最高人民法院于1992年颁发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73条将由人民法院负责调查收集的证据具体化为四种情形,即(1)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2)人民法院认为需要鉴定、勘验的;(3)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互有矛盾,无法认定的;(4)人民法院认为应当由自己收集的其他证据。
2001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颁发了《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该规定对以往的司法解释作出了重大的变更。首先,它不再将“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互有矛盾、无法认定的”作为由人民法院负责调查收集的证据,并明确规定:“因证据的证明力无法判断导致争议事实难以认定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举证责任分配的规则作出裁判。”其次,它明确了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仅指下列两种情形:(1)涉及可能有损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其他人合法权益的事实;(2)涉及依职权追加当事人、中止诉讼、终结诉讼、回避等与实体争议无关的程序事项。
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是将民事诉讼法的规定进一步具体化,属于广义上的民事诉讼法,对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均有约束力。在调查收集证据问题上,各级法院须按最高人民法院确立的证据规则行事,否则即属于违法。检察机关在此问题上的职责是监督法院是否切实遵守民事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确立的调查取证规则。值得注意的是,检察机关需要依据最高法院确定的规则实施监督,而不能仅依据自己作出的规定进行监督。如果最高人民法院确立的调查取证的规则发生了变化,检察机关就需要按照新的规则实施监督。
根据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确立的新规则,检察机关在抗诉监督中可以收集的证据包括:(1)当事人或诉讼代理人对因客观原因无法收集的证据,已向法院申请调取并提供了相应的证据线索,法院未进行调查收集或未认真调查收集的;(2)应当由法院调查的有关程序事项的证据中能引起再审的证据,法院未调查收集的。例如,败诉的一方当事人以一审法官有应当回避的法定情形而未回避作为理由提出上诉,二审法院在审理时竟未对此进行调查,便以当事人举证不足为由驳回了上诉,检察机关在决定是否抗诉时可收集一审法官存在应当回避情形的证据。(3)涉及可能有损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的事实的证据,法院在审理中未收集的。这类问题主要存在于双方当事人恶意串通,以诉讼方式谋取非法利益的场合。当事人进行这类诉讼前,一般都事先做好充分准备,在法庭审理时也不会轻易暴露,所以法官也不易察觉。另一方面,恶意诉讼对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第三人合法权益的损害也常常是在诉讼终结后的一段时间内才会显现。因此,尽管最高人民法院将这类证据规定为法院依职权调取的证据,但法官在审理过程中却往往没有调查收集。检察机关是社会公共利益的维护者,理所当然地应调查收集这类证据。
从以上分析中得出的结论是:检察机关只要是依据民事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设定的规则对法院的认定事实活动实施监督,并为了履行监督职责进行调查取证,其调查收集证据和提出新证据的行为便具有合理性和正当性,但如果越出了这一范围,检察机关调查取证活动的正当性就可能产生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