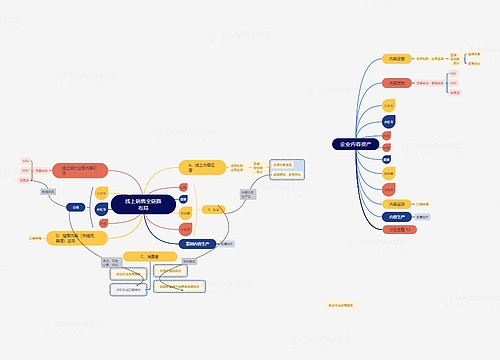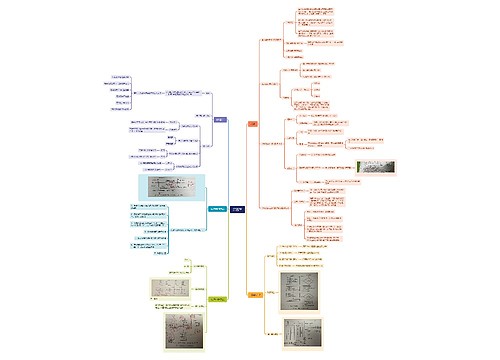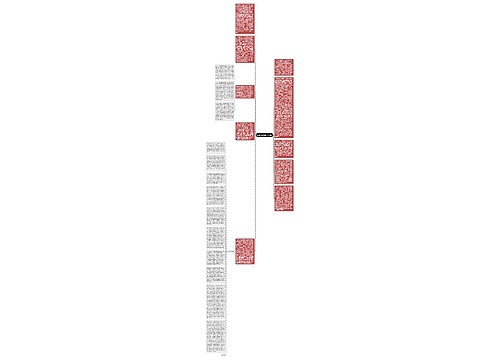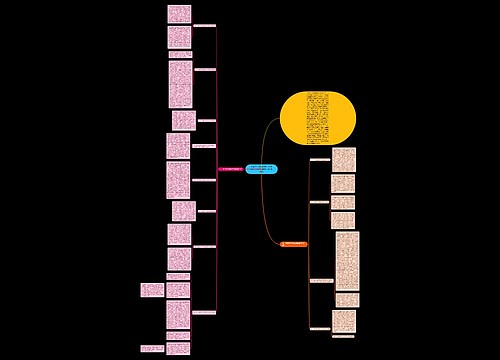“法治就是以规则来治理国家。实现法治的路径大体可分为两种:实体法治和程序法治。中国应该选择哪一种道路?”薛刚凌在许多同行不认为还有问题的地方,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他们认为,程序法治是当然的选择。事实上,很多人根本不相信在程序法治之外,还另有其他的法治路径存在——法治就是程序法治。
薛刚凌教授提醒大家:另外一种法治模式实际是存在的。她在日前中国法学会与本报等单位联合主办的“青年法学家论坛”发表演讲,阐述了两种法治发展路径的区别——
实体法治主要是通过建构以权利义务配置为核心的实体法律制度来实现国家法治的目标,强调法律的功能主义和制度建构价值。实体法治注重国家、社会、市场和个人之间关系的构建,并在中央与地方之间、地方之间以及个人之间进行合理的权利(力)界分,以利益调整为重心、以结果公正为导向,崇尚纵向的自上而下的秩序,依赖于制度研究者、设计者和决策者的明智。在一定程度上,实体法治可以被描绘为行政式的法治,依赖立法和行政权威,司法的地位并不特别突出。这一模式在德国、法国等大陆法系国家比较盛行。
程序法治主要通过程序法律制度的建构和完善,实现国家治理的法治化,强调法律的理性主义和自由价值,以过程为重心,以市民社会的高度发达和市民的广泛参与为前提,尊重以自由为基础的个体之间的平等、理性以及个人的价值和尊严。程序法治强调博弈,依赖司法,司法权力在国家权力体系中占据着突出地位。可以说,程序法治是一种司法式的法治。这种类型以英国、美国等国家为主要代表。
也许是由于有英语教育背景的精英人数远远多于其他外语教育背景的精英,也许是痛感于我国长期以来“重实体、轻程序”的状况,新程序主义学派的声音近年在学界格外洪亮。但薛刚凌教授指出,当下的中国不宜走程序法治的道路,采用实体法治为主,兼顾程序法治的模式,才是最合理的选择。
实际上,薛刚凌本人也有留美背景,并且对英美法系情有独钟。“从学术理念上说,我认为英美法系比大陆法系更高级。民众通过博弈参与规则的创造,当然比精英代为立法更能保障自己的权利。”但是,她说,“实体法治和程序法治各需要有一套条件来支撑。选择哪一种法治化道路,要看文化背景、历史传统、社会结构等等。中国的实际情况,与英美法系相距十万八千里!你硬要把它改造成英美法系国家,是不可能的。”
她举例说,在英美法系中,法律的源泉就是司法,通过司法来创造秩序并维持秩序,公众把法官当成法律的化身来尊敬。但在中国,法官怎么可能获得如此高的社会地位?
再譬如说,主张程序至上的学者过分考虑对犯罪嫌疑人权利的保护,这和中国、东亚传统文化中“有罪必罚”的观念就完全脱节。在同一个论坛上,有在读大学生就“英国的审前羁押率只有百分之二十几,为什么中国极少使用取保候审”向西南政法大学孙长永教授提问,热切主张进行侦查制度改革的孙长永教授在回答时也提到一个事实,“日本的羁押率超过60%.”
社会条件如此。你可以说这些都是不合理的,都应该推倒重来。“但我们不是在一张白纸上画画儿。”薛刚凌说,“关键是能否在现有的条件下找到制度生长的基础。我主张实体法治为主,兼顾程序法治,可以说是一种渐进的,从传统中寻求超越的思路。它符合社会发展的需求,不会引起秩序重构中的动荡,成本低、效率高、阻力小、社会可接受性强,有利于我国法治的良性发展和法治目标的最终实现。”
走实体法治道路,首重立法而不是司法。“大量的腐败现象都是因为制度供给不足,各个环节都靠潜规则运行。”专职研究行政法的薛刚凌教授说。
薛刚凌教授承认,虽说比实行程序法治难度小一些,但实现实体法治也仍然任重而道远。参与立法者的数量和素质都远远不足。各种主体的权利义务配置极度混乱,立法的要素、条件、顺序等系统考虑不够。尤其是地方立法,往往是当地党政领导觉着眼前什么事情重要,就提出要立什么法。因为条件不具备,立出的法规只具有政策宣示价值,浪费了宝贵的立法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