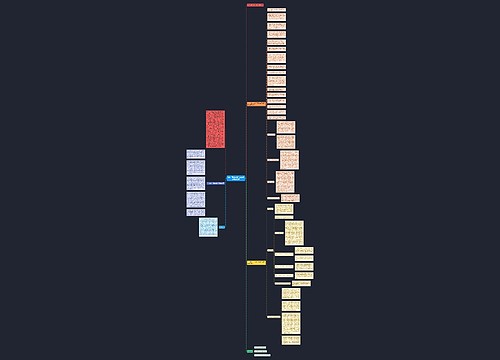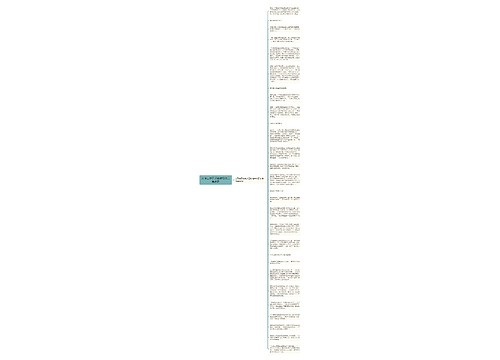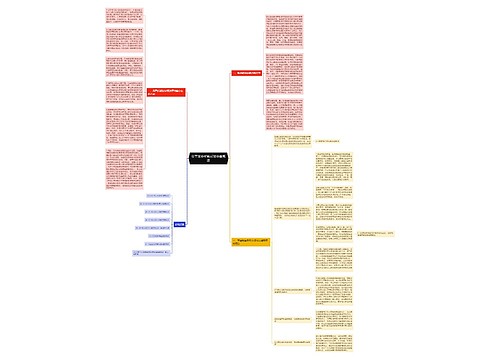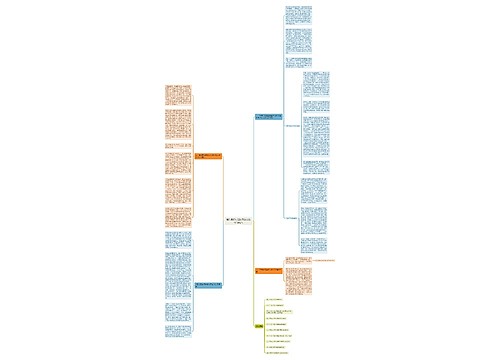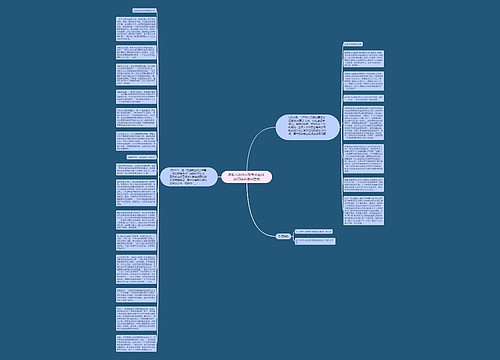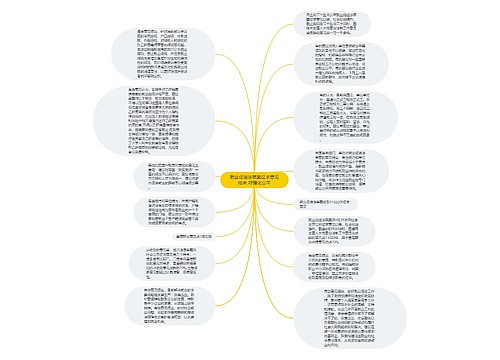我国女职工特殊权益保护制度研究思维导图
甜味仙女
2023-03-05

制度
研究
保护
权益
职工
特殊
我国
规定
妇女
劳动
妇幼权益
女性就业
女性就业歧视
摘 要:女职工特殊保护,是指国家根据女职工身体结构和生理机能的特点以及抚育子女的需要,在劳动方面对其特殊权益的法律保障。我国女职工特殊权益保护还存在着执法不严、监察不力、内容滞后、无法可依、维权成本太高等方面的问题。应该树立科学的立法观,完善女职工特殊权益的各项制度,加强女职工特殊权益保护与自我保护意识的培养,强化对损害女职工特殊权益违法行为的刑事制裁,使女职工特殊权益保护向着社会化的方向发展。
树图思维导图提供《我国女职工特殊权益保护制度研究》在线思维导图免费制作,点击“编辑”按钮,可对《我国女职工特殊权益保护制度研究》进行在线思维导图编辑,本思维导图属于思维导图模板主题,文件编号是:f4edb570f14d8422eb569511c113ee67
思维导图大纲
相关思维导图模版
我国女职工特殊权益保护制度研究思维导图模板大纲
关键词:女职工特殊保护 问题 思考
我国政府从来都重视女职工特殊保护立法。在国际法方面,我国批准了国际劳工组织《1935年井下劳动(妇女)公约》、《1951年同工同酬公约》和《1990年关于作业场所安全使用化学药品公约》;批准了联合国文件《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的歧视》和《社会、经济和文化公约》。在国内法方面,国务院1988年发布了《女职工劳动保护规定》,原劳动部1990年发布了《女职工禁忌劳动范围的规定》。同时,在妇女权益保障法(1992年颁布,2005年修改)和《劳动法》(1993年颁布)中对女职工特殊保护设有专章规定。
一、我国女职工特殊权益保护立法概况
在法律层面上,我国已经建立起内容比较全面、标准比较高、体系比较完善的女职工特殊权益保护法律体系。
(一)女职工特殊权益保护的内容
我国现行的劳动法律、法规和规章对女职工在劳动过程之中,在月经期、孕期、产期和哺乳期期间,在有关设施方面,在劳动合同期限方面和女职工劳动保护权益受到侵害时的救济手段方面的特殊权益保护,都进行了比较具体的规定。
(二)修改后《妇女权益保障法》的亮点
首先是增加了条款,丰富了内容。《妇女权益保障法》由原来的54条增加为60条;将第4章中的“劳动权益”更名为“劳动和社会保障权益”并将其原来的7条10款增加为8条14款。
其次是将妇女特殊权益保护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之中。《妇女权益保障法》第2条第款规定:“国家保护妇女依法享有的特殊权益”第3条规定:“国务院制定中国妇女发展纲要,并将其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
修改后的《妇女权益保障法》对女职工特殊保护作出具体规定。《妇女权益保障法》第22条规定:“国家保护妇女享有与男子平等的劳动权利和社会保障权利。”第23条第2款规定:“各单位在录用女职工时,应当依法与其签订劳动(聘用合同或者服务协议,劳动(聘用)合同或者服务协议中不得规定限制女职工结婚、生育的内容。
第26条规定:“任何单位均应根据妇女的特点依法保护妇女在工作和劳动时的安全健康,不得安排不适合妇女从事的工作和劳动。妇女在经期、孕期、产期、哺乳期受特殊保护。”第27条第1款规定:“任何单位不得因结婚、怀孕、产假、哺乳等情形,降低女职工的工资,辞退女职工,单方解除劳动(聘用)合同或者服务协议。”第28条规定“国家发展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医疗卫生保健事业,保障妇女享有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医疗卫生保健等权益。”
然而,法定的权利不等于已经享受到的权利近几年来,在“以发展经济为中心”的口号下性别意识被日益地淡化甚至退出了“历史舞台”除了公务员和国家干部身份的女职工的特殊保护权能够实现以外,其他部门的大部分女职工,特别是女工人,事实上并没有完全享受到法律赋予的特殊保护权利。例如,在《中国妇女发展纲要(1995年至2000年)》的11类目标项目没有实现的两类目标中,其中的一项目标就是女职工的特殊保护;再如,多年来,虽然国家的一直保持着8-9%以上的发展速度,然而,却没有带来女职工乃至妇女的全面发展,女职工特殊保护的权利被逐渐忽视而问题不断。
二、我国女职工特殊权益保护存在的问题
我国女职工特殊权益保护存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监察不力、内容滞后、无法可依、女职工维权成本高等现象。
其一,女职工在从事着法律禁忌的劳动。近几年来,不少的乡村个体锑矿、煤矿和乡村无证煤矿违法招收妇女从事矿山井下工作现象十分严重。个别乡村个体锑矿、小煤矿井下的一线工人,女职工占了一半以上。[1](149)某些男职工不愿意从事的劳动强度大、劳动环境恶劣、属于女职工禁忌劳动范围的工种或岗位,女职工在从事着,且恶性事故不断。例如,2004年2月15日,云南省富源县上则村无证开采小煤矿瓦斯爆炸,在27名遇难者中有10人是女性,在15名受伤者中有12人是女性。[2]
女职工劳动保护设施不到位。某些用人单位为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女职工劳动保护设施往往被其“忽略不计”。据山东省近年来对新建的非公有制企业进行的调查发现,没有一家企业同时依法配套卫生室、孕妇休息室、淋浴室和哺乳室。其中无卫生室的占64.4%,无孕妇休息室的占91.1%,无哺乳室的占97.8%,无淋浴室的占45.6%.[3](37)女职工“四期”保护权难于实现。在江苏的非公有制企业中,孕期、哺乳期女职工未能实行三级以上体力劳动强度保护和有毒有害禁忌保护的分别为38.1%和35.4%;怀孕7个月以上的哺乳期女职工仍从事加班或夜班作业的分别占22.5%和20.1%;从事低温冷水作业和三级以上体力劳动强度作业的女职工月经期间大多不能给予调换工作,有的仍安排其从事高空、低温、冷水作业和第三级体力劳动强度的劳动,对育龄女职工有毒有害工种的调离率几乎为零。[4](42)而一些发放工资都成问题的国有企业,也无力依法让其女职工享受到特殊保护权。
女职工作业环境恶劣。目前我国有毒有害企业超过1600家,受到职业病危害的人数超过2个亿,其中,约有1亿名是在中小企业就业的农村进城务工的劳动者,有1.36亿名是在乡镇企业从事工业劳动的农村劳动力。[5]据广东医学院对9家企业的调查,有6家经常使用有毒化学药品,高达70%的女职工每天都在和有毒化学药品打交道20%的女职工承认自己受到过性骚扰[6](54)。在一些诸如橡胶、制鞋和玩具等行业,大部分女职工长期工作在设备陈旧、工艺落后、作业环境差、事故隐患多的环境中,但却得不到任何保护,导致中毒、人身伤害事件屡禁不止。
女职工定期体检和产前体检难于实现。非公企业中的大多数企业不为女职工进行妇科病定期体检,以及怀孕女职工产前体检的费用不给予报销部分公有企业由于效益不好,干脆取消了此制度。
女职工流产、死产率比较高。由于女职工长期从事含汞等有毒作业,其流产、死产的发生率高达33.61%,而接触高浓度铅的女工的流产、死产的发生率更是高达35.3%;有关专家认为,在畸胎中,真正由于遗传因素造成的仅约占20%,环境原因的约占20%,其他60%的畸胎则可能是劳动环境、遗传原因相互作用的结果。[7](38)
其二,执法不严,监察不力。执法监察是实现女职工特殊保护权的一种重要的形式。然而,在每年的劳动执法大检查中,大部分省份的劳动执法大检查始终没有把女职工特殊保护纳入其执法检查的内容之中。据广东卫生部门2003年统计,广东存在职业危害隐患的企业有近100万家,接触职业危害的劳动者约1000万人,但被列入经常性监督的企业只有2万家。[7](54)
其三,部分条款内容滞后。部分执法主体已不复存在。现行女职工特殊保护的法律法规多为计划经济时期所制定,其大量使用的“有关部门”“有关主管部门”、“所在单位的主管部门”等概念,带来了救济部门的不确定性。
救济制度不完善。女职工特殊保护法律法规中的救济途径和方式多是以行政为主导,制裁形式多为“责令改正”、“行政处罚”和“罚款”之规如果说在计划经济时代行政制裁会发挥很大作用的话,那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行政制裁的适用范围和法律效力都表现出了很大的局限性,惩治的有效性和力度也会大打折扣。何况行政权和司法权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权力,用行政救济替代司法救济,其结果往往是权利的难于实现,甚至是权利的虚设。而对于个人权利的实现而言,更需要的是司法意义上的救济。
其四,无法可依现象逐渐凸现。对高新技术产业和知识密集型产业所带来的“污染”,国家未及时做出禁止性的规定。如随着高科技的发展,电磁波、微波、电磁场、高分子化合物等造成的污染和目前还未认识的诸多隐性的有毒有害的物质,对女职工身心健康的影响将无法估量,而原有的法律法规却都无此方面的规定。
女职工由于接触有毒有害物质所导致的流产、死产和畸形儿的现象已不是个别,但其责任该由谁来负责,其能否成为工伤的范围,女职工是否享有赔偿权和提起侵权之诉,却处于无法可依的局面。
对性骚扰问题未做出规定。性骚扰多发生在两性共同劳动的过程中,且多是强者骚扰弱者,男性骚扰女性,男上司骚扰女下属。据郑州晚报和新浪网的“性骚扰调查问卷”显示,调查者中有76%的女性遭遇过性骚扰。[8]在我国,虽然已经出现了对簿公堂的性骚扰案件,但由于取证难和无法可依,多以败诉告终。所以,为保住饭碗和名誉,许多女职工对性骚扰往往持沉默态度。在调查者中,有39.67%的对性骚扰悄悄躲开并加于忍耐,有31.91%的暗示对方放尊重点,有11.7%的大声提醒强烈反抗,仅有3.66%提起诉讼[8],但胜诉者寥寥无几。
其五,女职工维权成本太高。新《集体合同规定》第8条将女职工特殊保护的内容规定到其条款中,并在第14条中对女职工特殊保护加于具体说明。《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11条第4款将用人单位遵守女职工和未成年工特殊保护规定的情况纳入到其监察的范围中。并在第23条中规定,侵犯女职工特殊保护权利的,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责令改正,按照受侵害的劳动者每人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标准计算,处以罚款。由于罚款数额仅仅只是给予女职工特殊保护中的几个小数点,所以用人单位往往就会采取甘愿接受罚款也不愿意守法的手段。与此相反,女职工如果要获得这些法定权利的话,则往往需要几个月直至几年的时间。
违法成本的太低和维权成本的太高直接产生的社会效应是:侵害女职工特殊保护的现象十分普遍,但申请仲裁和提起诉讼的仅仅是个案。
其六,法定特殊保护权成为获得其它权利的桎梏。为规避对女职工特殊保护的规定,用人单位干脆不招女职工。不少用人单位为避免“性别亏损”和减少成本,招工时公开不招女性,或把女性作为被招收男性的一种配额来招收。如云南省近年来女性学生的就业率仅为男性学生的一半。为实现就业权,女职工被迫同意放弃应该享受的权利。为规避对女职工的特殊保护,不少用人单位在招工时有意避开女职工的生育期,或只招25岁以下的女性,或签订劳动合同时避开女职工的孕期、产期和哺乳期,或生育前即被终止劳动合同(导致不少女性25岁便进入失业队伍)或只招已经结了婚生了小孩的女职工。为了保住工作,有的女职工在青春期不敢谈恋爱,在生育期不敢怀孕,或怀了孕就偷偷地做流产手术,更不敢生小孩。
“是要孩子还是要工作”,竟成为一些女职工不得不面对的两难选择。而某地水电局竟规定,无配偶的合同制工人才可与其续签劳动合同,导致其单位的10名女职工为取得与其续签劳动合同的机会而集体向法院提出离婚诉讼[9],在中国的司法史上留下沉重的一笔。
用人单位违法行为合法化。有的用人单位在合同中公开规定女职工在聘用期间不得谈恋爱、不得怀孕和生小孩。如女职工怀孕或生小孩,其就会被调换到低薪或脏、苦、累的工作岗位,从而迫使其自动离职;有的用人单位实行高标准的计件工资,为包住饭碗,女职工尽管处于孕期或哺乳期,也“自愿”加班加点,且自动放弃加班工资;有的合同期的女职工在产假期满后不得进入工作岗位,只能领取基本生活费;有的女职工产假工资无保障、生育期间无保险,但从来不敢依法提出要求。
女职工的劳动关系被劳务化。有很大部分的女职工,特别是被教、科、文、卫、体单位聘用的女职工,由于单位不与其订立劳动合同,或与其订立的是劳务合同,所以其劳动关系往往被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和法院认定为劳务关系。而劳动关系被异化为劳务关系的结果是,女职工不但享受不到特殊保护的权利,且享受不到劳动法所规定的一切权利。
三、完善我国女职工特殊权益保护的措施
在《妇女权益保障法》修订和实施的基础上,必须完善我国女职工特殊权益保护的方法。
(一)树立科学的立法观
将性别意识纳入立法和执法的主流。性别主流化作为联合国争取男女平等的一种全球性的战略目标,其目的是为了保证男女都能平等地分享社会发展的成果,并最终达到社会性别的平等。依国际规则办事应该成为我国社会生活的基本要求,在我国有关立法和执法中,尤其是在女职工特殊保护立法和执法中,应该充分体现出其性别意识。
将2005年《妇女权益保障法》性骚扰条款的规定具体规定到女职工劳动保护规定之中。性骚扰已经成为一个世界性的课题,不少国家和地区对性骚扰进行了立法。1975年,美国联邦法院第一次把性骚扰定义为“被迫和不受欢迎的与性有关的行为”,并将其作为一种性别歧视而加以禁止;加拿大和法国将其规定为妨害风化罪;西班牙等国则将其归入侵犯性自由罪类。性骚扰不但是一种性别歧视,而且也是一种职业歧视。因此,应该将《妇女权益保障法》第14条的规定具体化在女职工劳动保护的内容中。而且性骚扰不仅仅只是女职工的问题,还应该将性骚扰写进《劳动法》。
同时,受到性骚扰的女职工在心理方面往往会受到极大的伤害和刺激,产生心理疾患、增加工伤事故和被社会歧视。如在性骚扰造成的心理伤害中,有78%的被骚扰者害怕或者不相信他人;47%的性格发生变化,不愿与人交往;34%的人认为被骚扰者想报复他人或社会;22%的人认为被骚扰者会受到社会的排斥。[7]因此,还应该在女职工劳动保护条款中加入对受到性骚扰女职工的心理抚慰和治疗的有关条款,以体现法律的人本精神。
将新出现的有毒有害工种及时补充进《女职工禁忌劳动范围》之中。2002年,国家将我国职业病的范围从1987年的9大类99种扩大为10大类115种,从更大范围保护了劳动者。同理,国家也应该及时对由于高新技术的发展而出现的对女职工有害的工种重新界定,并及时补充进《女职工禁忌劳动的范围》之中。
确立民事赔偿权。《职业病防治法》和《安全生产法》都规定,劳动者除了依法享受工伤保险权以外,依照民事法律尚有获得赔偿的权利的,有权向用人单位提出赔偿请求。此立法精神应该吸收到女职工由于工作环境的不卫生,导致流产、死产、畸形和人格权(受到用人单位的侮辱、贬损和体罚)受到严重的侵犯的情形,[10](18)以填补此方面立法的空白点。因此,在女职工劳动保护规定中,应该增加“女职工除了依法享有特殊保护权利以外,依照民事法律尚有获得赔偿的权利的,有权向用人单位提出赔偿请求”的条款。
(二)完善女职工特殊权益保护各项制度
建立专门的困难女职工法律援助制度和司法救助制度。2005年《妇女权益保障法》第52条第2款规定:“对有经济困难需要法律援助或者司法救助的妇女,当地法律援助机构或者人民法院应当给予帮助,依法为其提供法律援助或者司法救助。”
为切实保障女职工的特殊保护权的实现,应为困难女职工建立专门的法律援助制度和司法救助制度。
设立专门的女职工特殊保护司法机构。为加大对妇女权益的保障力度,2002年,哈尔滨市妇联与市中级人民法院联合成立了“哈尔滨市妇女维权法庭”,由专职法官对侵犯妇女权益的案件进行审理。2003年,北京市西城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设立了国内首家女职工权益保障庭,负责专门处理涉及女职工特殊保护的劳动争议案件。我国女职工从业人员已经接近总从业人员的一半,在有关部门设立专门的保护女职工权益的司法机构,应该是实现法律对女职工特殊保护的一种发展方向。
建立女职工特殊保护专项监察制度。早在1997年,上海市便颁布了《上海市劳动保护监察条例》,对劳动保护(包括女职工特殊保护)进行专项监察;2003年,北京市劳动监察大队对女职工特殊保护进行了专项的监察。2004年1月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发布的《集体合同规定》增加了女职工特殊保护的条款;2004年11月,国务院发布《劳动保障监察条例》,将女职工特殊保护作为其监察的重要内容。所以,加强专项检查是确保女职工特殊保护权实现的重要手段。
(三)加强女职工特殊权益保护自我意识的培养
2005年《妇女权益保障法》第5条规定:“国家鼓励妇女自尊、自信、自立、自强,运用法律维护自身合法权利。”第52条第1款规定:“妇女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有权要求有关部门依法处理,或者依法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或者向人民法院起诉。”据广州市总工会和安利最近联手进行的调查显示:在鞋业和皮革类职业病高发企业中,女工占到50%)80%,育龄妇女占60%以上,但了解苯伤害胎儿的女工不到10%,而且在工作时间不愿意使用劳动保护用品。[11]而对直接关系到其切身利益的《女职工劳动保护规定》、《女职工禁忌劳动范围规定》、《妇女权益保障法》、《劳动法》的了解率则分别为40.9%、58.1%、34.8%、21.7%;在其特殊权益受到侵犯时,不敢说的占25.5%,不愿说的占26.7%;要向企业主管部门反映的占40.2%;向法院提起诉讼和到当地劳动部门申诉的仅占7.3%和3.6%.[12](40)因此,加强对女职工特殊保护自我意识的教育已经刻不容缓。
(四)加强对违法行为的刑事制裁
我国现行刑法中与劳动有关的规定十分有限,这或许就是劳动执法“疲软”的根本原因。以下几个国家的一些有关规定,或许能给我们在修改劳动法时一些启示。如新加坡1968年《就业法》106条规定:“任何雇主不按照本部分的规定付给女性受雇人以报酬、或者违反本法第100条的规定,应是犯法行为并应处于500元以下的罚款,或6个月以下的有期徒刑,或罚款和徒刑两者并处。”第107条规定:“(1)女性受雇人不应雇用做任何地面下的工作。(2)任何人违反本条第(1)款规定雇用女性受雇人,根据本法应是犯法行为。”因此,加强对损害女职工特殊权益违法行为的刑事制裁,应成为女职工特殊保护权实现的一个根本途径。
(五)向着社会化的方向发展
女职工特殊保护权能否实现,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一个国家谋求人的全面发展的总体质量。[13]女职工特殊保护应该是全社会的责任,但就目前的制度安排,这一责任实际上基本由用人单位全部承担,同时还缺乏鼓励用人单位吸纳并保障育龄女职工特殊保护权的积极性的政策规定。目前,我国企业除了要为职工缴纳大约30%的社会保险费以外,还要缴纳30%-24%的所得税,我们不得不承认企业的负担确实很重。如北京市“女职工劳动保护费”是“生育保险费”的2.56倍,在国有企业甚至高达9.64倍,而且由企业全部承担。然而,企业独立承担女职工特殊保护费用正是导致女性就业难的问题,却远未引起社会的注意。[14](31)
因此,如果将女职工特殊保护社会化的话,不但法律规定的女职工的特殊保护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得于实现,还可从一定程度上缓解女性就业难的问题。
引用法条
[1]《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3]《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
[4]《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
[5]《集体合同规定》 第八条
[6]《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 第二条
[7]《集体合同规定》
[8]《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 第五条
[9]《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 第二十二条
[10]《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 第二十三条
[11]《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 第二十六条
[12]《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 第二十七条
[13]《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 第二十八条
[14]《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
[15]《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 第五十二条
[16]《劳动保障监察条例》
[17]《劳动保障监察条例》 第二十三条
查看更多
一、研究内容思维导图
 U682687144
U682687144树图思维导图提供《一、研究内容》在线思维导图免费制作,点击“编辑”按钮,可对《一、研究内容》进行在线思维导图编辑,本思维导图属于思维导图模板主题,文件编号是:4f21797dd3e8b08f1951dfc24e7be94f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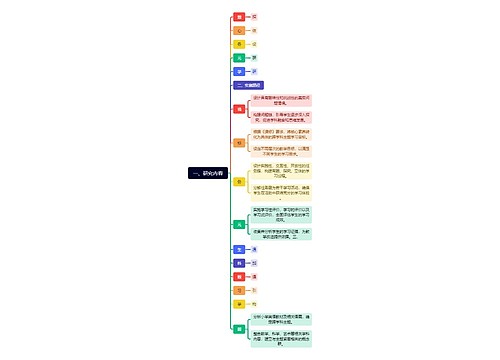
第六章 群体传播与组织传播_副本思维导图
 U882673919
U882673919树图思维导图提供《第六章 群体传播与组织传播_副本》在线思维导图免费制作,点击“编辑”按钮,可对《第六章 群体传播与组织传播_副本》进行在线思维导图编辑,本思维导图属于思维导图模板主题,文件编号是:1672f555831e7d9a3bb2cf2fb792cb4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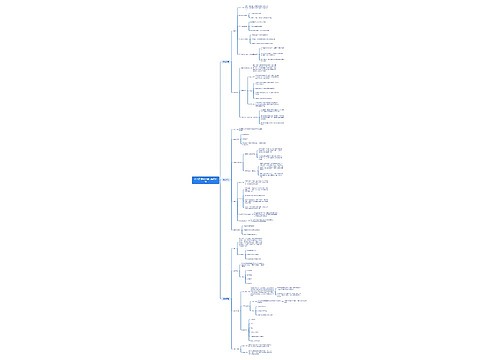
相似思维导图模版
首页
我的文件
我的团队
个人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