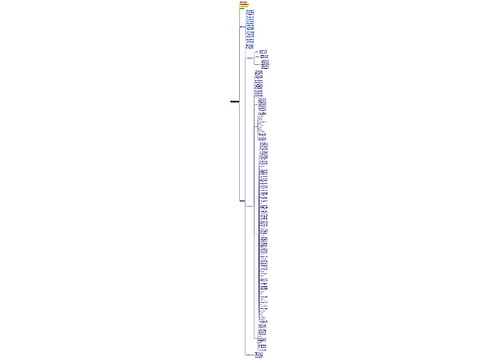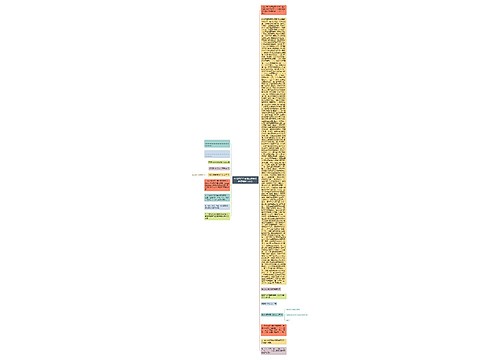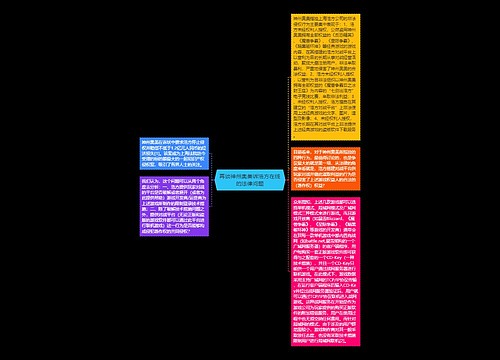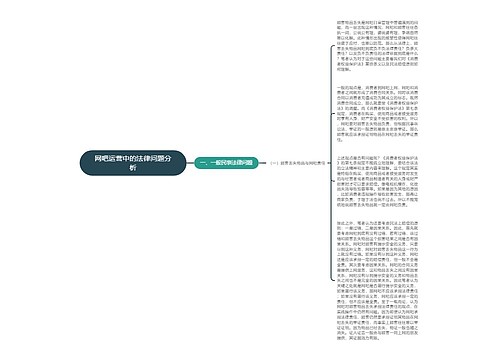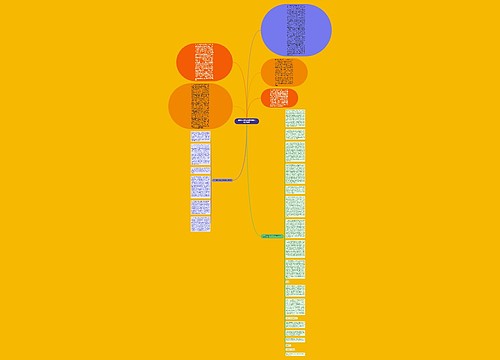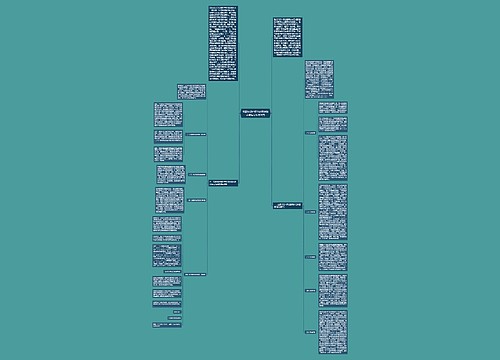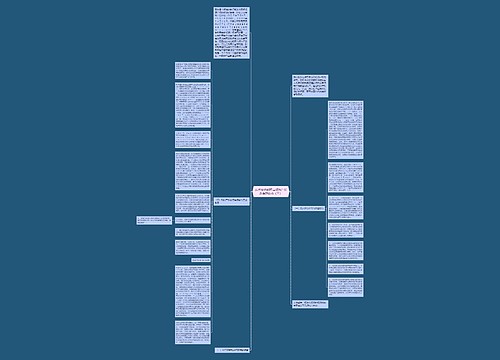由于现有作品的数字化是在网络环境下使用作品的前提,如何看待数字化行为的法律性质就成为需要首先明确的问题。毫无疑问,作品的数字化是作品的一种使用方式,那么作品的数字化行为是否属于著作权人的专有权利,他人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将作品进行数字化是否侵犯了著作权人的权利?依照著作权法的立法精神,从保护著作权人权利的立场出发,作品的数字化转换当然属于权利人的专有权利,应该在法律上予以承认,按照我国《著作权法》第十条的规定?作者享有复制权、翻译权和改编权。数字行为是否属于复制行为就成为法学界争议的焦点。国内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数字行为是类似翻译的演绎行为,作品的数字化产生新的作品,这种观点被称为“翻译论”;另一种观点认为是一种复制行为,数字化前后的作品是同一作品,这种观点被称为“复制论”。
“翻译论”者的主要论点是:“数字化后的作品和数字化前的作品之间的关系是单纯的演绎关系,它和把一件英文作品译成中文作品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传统的翻译和数字化过程之间唯一的区别在于前者是由人完成的,而后者是由机器机械完成的”。1
按照我国《著作权法》第十条(十五)的规定,所谓翻译权,即将作品从一种语言文字转换成另一种语言文字的权利。这里所指的“一种语言文字”,是指代表一个民族所特有的那种语言或文字。2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1991年提出的《关于伯尔尼公约议定书的备忘录》第31条之Ⅸ已经明确指出:“在公约里翻译的概念过去和现在都针对实际语言及人类语言。”3显然,语言文字的内涵中不包含二进制代码这种机器语言。作品的翻译是在原作品基础上的一种再创作行为,体现了翻译者对原作的独特理解,融入翻译者的智慧,因此翻译作品成为新的著作权客体,受著作权法保护。也就是说,翻译行为是一种带有原创性的行为,因此翻译行为既是一种作品使用方式,也是一种创作行为。以此来看待数字化行为,会发现数字化行为只是由机器完成的符号转换过程,其中没有创作性工作,没有产生新的作品。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如果将数字化行为视为翻译行为,势必承认机器可以成为作者,使机器成为权利主体,有违著作权法的立法本意和宗旨。因此,作品的数字化转换行为不属于翻译。 基于上述对“翻译论”的反对,“复制论”认为:著作权法保护的是人的创作,一部作品不论其权利归属如何,其最终的创作者只能是活生生的人,是自然人。而数字化是由机器完成的,机器不具备创作行为能力,更不能成为权利主体。一部作品经过数字化处理,并没有产生新的作品。
我国《著作权》法第十条(五)规定“复制权即以印刷、复印、拓印、录音、录像、翻录、翻拍等方式将作品制作一份或多份的行为”。很显然,复制的定义中并没有包含作品的数字化转换。对照上述法律规定的各种复制方式,数字化的过程类似于录音、录象过程。录音和录象的过程包含两个步骤:第一,把音像作品转换成电模拟信号的形式。第二,把电模拟信号形式的音像作品固定在磁介质上。根据上述规定,无论是把作品直接固定在载体上,还是把作品经过转换后再固定在载体上都属于复制。与此相类似,传统作品的数字化转换过程事实上也包括两个步骤:第一、把传统作品的原有形式转换成二进制数字编码;第二、把转换出来的二进制数字编码固定在某个载体上。因此,把传统作品的数字化转换看成是一种复制,与录音机、录象复制方式相并列是我国著作权法规的自然发展。4
笔者认为,作品的数字化转换是作品的一种新的使用方式,其法律性质属于复制,数字化前后的作品是同一作品。数字化后形成的作品的著作权仍然属于数字化前的作品的著作权人,权利的主体没有变更。如果未经权利人许可,擅自把权利人的作品进行数字化处理,就象传统的复制一样,都是对著作权人专有权的侵害。数字化是新技术条件下的一种新的复制方式,不论是通过键盘或者扫描输入计算机的数字化,还是需要投入大量技术、人力的复杂精细的数字化,改变的只是作品的载体,数字化之后的作品得到了比传统方式更好的保存,而没有产生新的作品。从实践中看,作品数字化的问题在许多发达国家已经有了明确的答案,例如美国1995年的白皮书指出,扫描印刷而成的数字化文件是该作品的复制件,照片、电影及录音制品的数字化都构成复制;欧盟1995年的绿皮书也指出,作品或其他受保护客体的数字化在复制权的范围内。1997年7月我国国家版权局拟订的版权法修订稿建议把“数字化”补充进现行著作权法第52条列举的复制行为中去,然而,新《著作权法》在对著作权进行权利整合的过程中,对此采取了较为谨慎的态度,并未在复制的下游概念中列举数字化的方式。
在明确了作品的数字化构成复制以后,便衍生出一个问题,应否授予作者“数字化权”。数字化权,又称电子权,是指作者在电子媒体使用或授权他人使用作品的权利。“数字化权”提出的实质就是在权利人授权他人特别是出版商出版发行其作品时,如果以电子媒体的形式出现,是否需要另外授权的问题。
对于一个享有双重著作权的客体比如杂志来说,杂志社对其杂志享有总体著作权,而单个作者对其个人的作品享有著作权,杂志社可以传统方式向公众提供其杂志,而且不需要经过各作者的再许可。现在的问题是,杂志社可否将其杂志数字化在电子媒介上,通过互联网络向公众传播。1997年的美国Tasini案或许为这一问题提供了参考。在本案中,几位独立撰稿人状告《纽约时报》等三家报刊擅自授权电子出版商将包含其文章在内的报刊内容编入电子数据库LEXISINEXIS和两张CD-ROM中,侵犯了每篇文章的版权。5美国法院判决被告的行为不构成侵权,原因在于集体作品的电子版没有超过美国传统版权法中的“修订本权”的范围。但是,如果出版商要把总体版权下的单个下游版权的作品上网,并且他们和作者之间没有约定,这种电子权是否属于作者的专有权的控制范围之内?对这个问题,美国法院没有回答。笔者认为,既然作品的数字化属于复制,作品上网当然属于复制权的控制范围内,而无须单独设立一项“数字化权”。应当明确,未经许可将现有作品进行数字化是一种侵权行为,“数字化权”是复制权的下位阶概念,而不是与其并列的一种权利类型,复制权中应当包含“数字化权”。这种改变是必要的,否则难以适应新技术的迅猛发展。作品的数字化是作品的一种使用方式,是新技术条件下的一种新的复制方式,其使用需要获得作者的特别授权。
作品的数字化转换作业,有的非常容易完成,如通过键盘进行的录入和利用扫描设备进行的数字化转换,但也有的需要投入大量的技术和劳动。对于前一种使用方式,数字化前后的作品并无本质的区别,对数字化后的作品也无须提供特别的保护。在后一种情况下,已经数字化了的信息,如果被第三人未经许可地使用,将置最初进行数字化的人于不利的地位,对数字化产业的发展产生极其不利的影响。出于这种原因,有关要求应运而生,即对这种数字化后的作品,新设立“数字化权”给予保护。本文为了和第一种意义上的数字化权相区别,在此将之称为“数字作品权”。“数字作品权”的含义:许可或禁止他人直接或间接复制其“数字作品”的权利。其性质是一种邻接权。
然而,在数字作品泛滥的今天,如果对这些数字作品都赋予数字作品权,导致任何人都不能廉价且容易地获得信息,将与信息时代的社会要求背道而驰,影响信息的流通和传播。另一方面,数字化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使数字化的成本不断降低,从这个意义上讲,创设“数字作品权”的必要性不足。
现行著作权法规定了著作邻接权,除录音、录像制品制作者外,亦赋予表演者和播放业者这种权利。这是由于这三个产业处于信息传播的重要领域,具有特别保护的强烈立法必要性。从对整个产业赋予著作邻接权的必要性看,直接对所有数字化行为,撒开法律保护之网进行全面调整,并不能说是妥当的。6
但是,假如出现不承认特定领域中的数字作品权,该领域的产业就不能生存,因此对该领域就应进行有限制的立法。这一点已被著作邻接权的立法所证明。从实践的角度看,只能对某些类型的“数字作品”创设权利,例如多媒体作品,而不宜对所有数字作品创设权利。
通过以上的讨论,我们可以看出,作品的数字化转换是一种复制行为,数字化前后的作品是同一作品,没有产生新的作品,机器更不能成为作者。只要对复制权的定义加以扩展,就能容纳数字化转换行为。“数字化权”的概念通常在两种意义上使用。在第一种意义上使用时,由于数字化行为可以被复制所包容而无须单独设立与复制权相并列的“数字化权”;在第二种意义上使用时不宜对所有的“数字作品”设立此项权利,而应区别不同的作品类型分别赋予相关的邻接权——数字作品权。
此篇文章原登载于《电子知识产权》杂志。本网站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三十二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三条的规定予以合法。
本网站依据国家相关规定准备了相应的稿酬,但由于客观原因无法支付。如您是这篇文章的著作权人或其他权利人,请与本网站联系。本网站在确认您的身份后将予以支付。
如果您有任何其他意见,请与本网站联系,本网站将在进行核实后24小时内采取相关措施。
电话:(010)65518443 邮件:deofar@vip.sina.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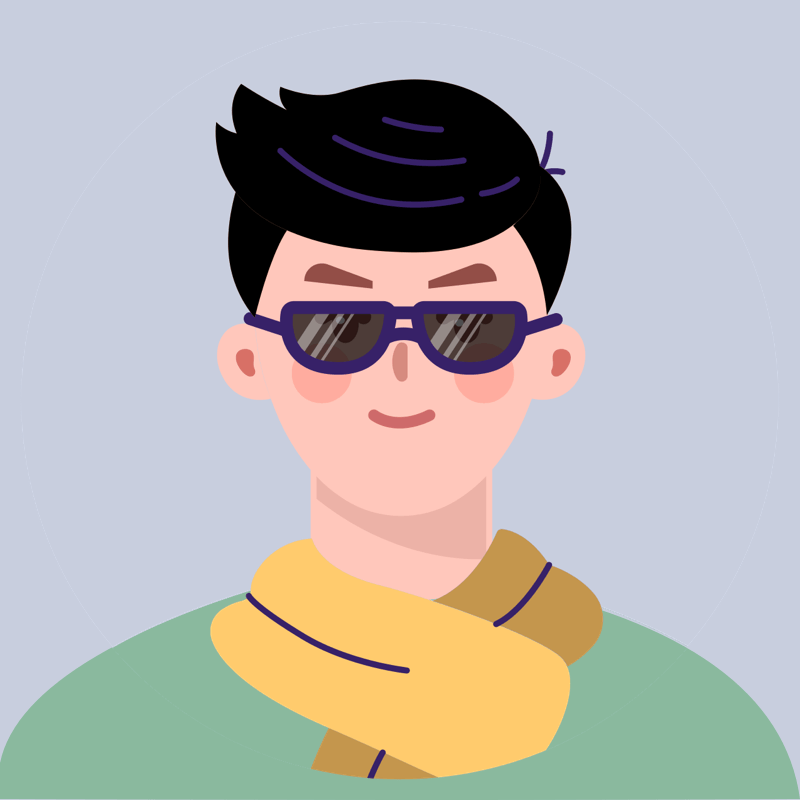 U245265618
U245265618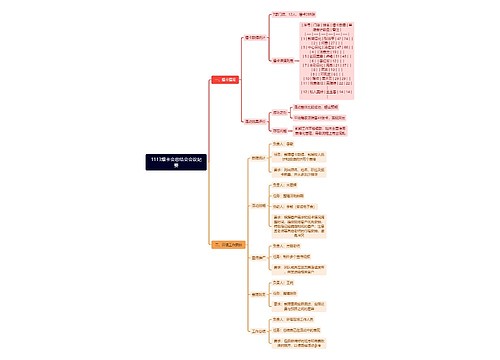
 U882667602
U8826676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