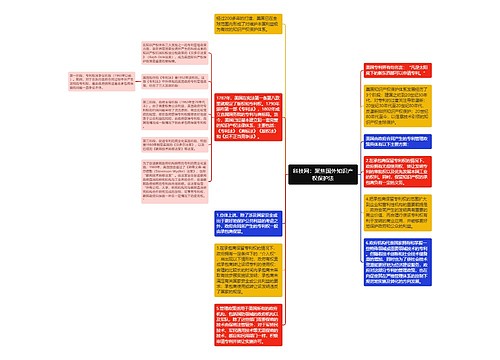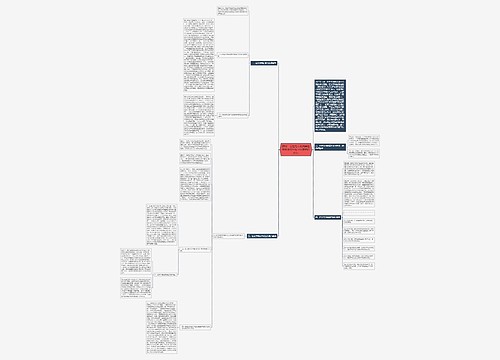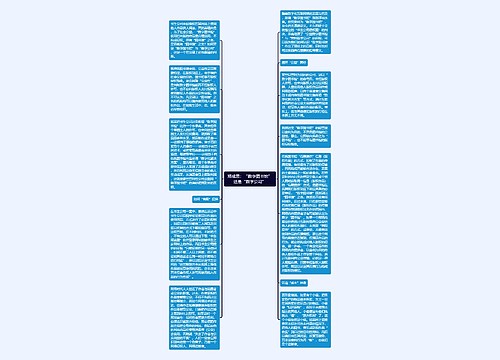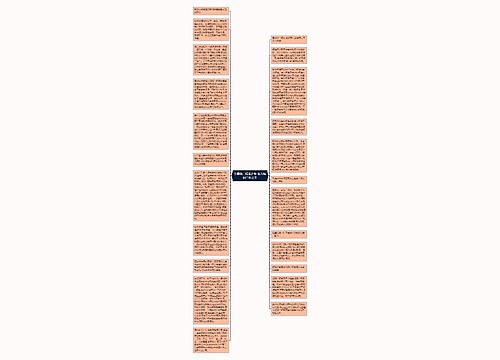于是我写信给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出版部,要求买一本《有关国家商标法概要》,因为在1980年初翻译完成后,该书的原本已交还中国贸促会。出版部的负责人显然没有我们今天许多人那种"经济头脑",他复信说书中的有些法条已经变更,所以当该组织准备出新版时,我准备买一本,该书要400瑞士法郎,有人劝我不必花这笔冤枉钱。不过我仍旧邮购了一本,结果连邮费花了我当时两个月的生活费。从伦敦的邮局收到该书时,我的心情是很激动的。我终于有了一本属于我自己的、我曾为译它而花费了那么大精力的《商标法概要》了。
回国后,这本书一直在我的书架上。有时我也用到它,特别是遇到知识产权法条或国际公约条文的翻译障碍时,就会想起该书曾出现过相同或类似的句子、条文或术语。但这样的使用机会毕竟很少。更多地使用,是让它作为一个时时推着自己往前走的动力,使我经常想起当初因何选择了知识产权这个研究方向,回忆起当初困难的条件。既然当初都挺过来了,现在更不应当有什么不可克服的困难。
在英国学习,我选择了伦敦经济学院研究生院。国内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著名法学家李浩培,均曾于20世纪30年代在该校学习。进入80年代,该校柯尼什教授又出版了当时在发达国家最有影响的知识产权教科书《专利、商标、版权与有关权》。这便是我选择该校的两个主要原因。
他对自己的教科书很满意,经常讲课讲到高兴时,就举起他的书,叮嘱同学们务必读懂某页的某一段,那是他自认为极精彩的论述。凡是有同学问及当代哪一本知识产权教科书最好,他总会毫不犹豫地回答"Mybook"。每当有人对他的论述提出异议时,在我的印象里,他总是毫不客气地拉下脸来把人家驳回去。在最初一段时间里,我对他的印象并不太好,感到他不过是在西方常能见到的"自大狂"中的一个。而中国人,至少在当时,还是更崇尚谦虚的。
一次偶然的课堂提问,彻底改变了我先前的印象。在他曾叮嘱过我们应读的一段论述中,我读后发现他的论述与他所引证的案例完全对不上路。我不知是自己英文理解力太差,还是专业水平过低。不过,为了弄清问题,我在一次有200多人听大课的场合找到了提问的机会。他听后先是一愣,仿佛没听懂我问什么。我头上的汗一下子出来了,准备好要被他轻易地驳回去,或用莎士比亚的语言说一句我未必能完全听懂的话---正像他经常驳回其他同学的异议那样。
不过我想象中的事没有发生。柯尼什接下去问:在哪一页上?他解释说他自己的书太厚,不可能记清所有内容各自所在的页码。当找到我的问题所在之处后,他低头盯着细看了一两分钟,抬起头来竟是一副抱歉的脸色。他说该案例的出处引错了,对不起我和其他读者,再版时一定改过来。这是我始料未及的!不过一下课,立即有同学来指责我这是"出风头",而且出得不高明。因为谁都知道柯尼什在国际知识产权界是公认的权威,一个小研究生要当众挑人家的错,只能显出自己不知天高地厚。
几天后,柯尼什找我去他的办公室,约我给他任编委的德国马普学会IIC杂志写一篇中国版权制度现状及发展的论文。我刚一听几乎手足无措。我并不担心自己的研究水平,但确实认为自己的英文水平根本不能胜任。"我连英国的电视片都不能完全听懂呢!"我半天才想出这么一句有点文不对题的话。"不要紧,要知道书面文字与口头语言可能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你可能直到毕业回国,口语都不能百分之百跟上,但我相信你现在就能完成这篇论文。""这可能是惩罚我?"当时我的脑子里确曾闪过这种念头,不过转瞬即逝了。因为柯尼什是个直性人,不会拐弯抹角---即使打算惩罚谁。
于是我开始了留学期间最艰苦的一段历程。首先我得学会打字---过去我不会,而我又绝不可能把手写稿交给导师。学打字并不太难,前后花了3天,然后是论文初稿。国内材料是备好了来的,国外材料还得收集,有些涉及英国之外的论著中的问题,还得与德国的Dietz博士、联合国知识产权组织的Bogsch博士等通信(当时尚没有传真,更不消说E-mail了),然后是动手写。不论怎么说,3个月之后,两万多字的打印稿交到了导师手中。
由于柯尼什把这篇论文来回改了6遍(也就是说,要我重新写了6遍),我有了更多机会与他面对面交谈,彼此也逐渐成了无所不谈的朋友。在论文之外,我们经常从当时举世关注的香港问题,谈到当时英国与阿根廷开战的马尔维纳斯群岛,又谈到新加坡的李光耀,等等。只是到了这时,我才把当初我提出那个书中差错的问题向他做了解释。没想到他完全不记得当时在课堂上是否使他难
堪了,但提出的那个错,他实实在在地在自己用的那本书上作了记号,以便再版时更正。
我问他,是不是因为我是他指导的学生,他就特别宽容一些。他说并不全是,而是多数对其教科书提出的异议,十足反映出提问者并没认真看他的书,就出来"Challenge"。他对自己的立论是有信心的,因为它是经过了认真研究才写出的。他说,切不要把自信与狂妄混为一谈。人要想做出点事业,首先要有自信。如果不论什么不负责任的异议都接受过来,那就搞不成学问了,但又不能认为自己一切都无可挑剔,否则就不会再往前走了。那就真的是狂妄了,就会在竞争中被甩下来。谈到这里他重复地说几遍。
他认为我当初在课堂上提出的问题,是书中实际存在的差错,他自己没有发现,被我发现了(其实我只是看不懂、拿不准,并未认定那是个差错),他自然应该感到高兴,因为至少在下一版自己的书中又可以少一个错误,向完美又进了一步。
我的这篇论文发表在了IIC1984年第2期上。论文发表后的一年多里,我接到了许多表示祝贺的来信,其中有联合国的、美国的、德国的、澳大利亚的知识产权界的名人。直到今天,我仍时时见到外国人论述中国版权制度的论著援引它。它是我被国际知识产权界认可的第一篇文章。在那之后的10多年里,我又以英文出版了5部独著与合著,并在国外学术刊物发表论文数十篇。此外,我还以中文出版了30部专著。相比之下,那第一篇论文显得很"初步",不过它的确是使我建立起自信的第一步。
柯尼什承认自己作品中会有差错,并欢迎刚刚起步的研究生去挑错的这段历史,也给了我很大的影响。我每出版一书,均会有许多议论、来信、文章乃至专著涉及它,其中不乏"挑差错"者。从我的第一部中文专著出版起,也有不少没有看懂而轻率"异议"者,有的"异议"者甚至有"专家"的头衔。但这些"异议"并未动摇过我沿认定的方向及继续研究并出成果的信心。对能够认真阅读它并挑出差错者,我均会去信表示感谢。如果再版时真正按人家的指正去更正了,则要在前言中加以说明。
我留学时第一篇被国际上认可的论文,是由于我给一位非常自信的权威挑了错才产生的。在我写这第一篇论文时,这位权威所说的一直伴我走过了这20多年的学术生涯,而且还会继续伴我走下去。

 U682687144
U682687144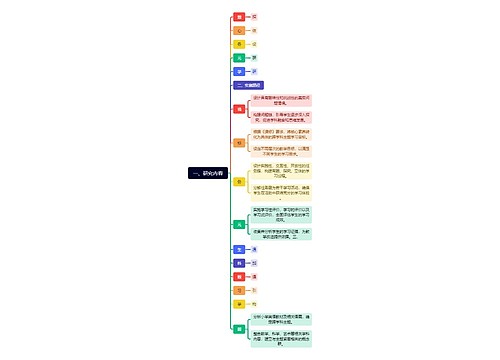
 U982199398
U9821993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