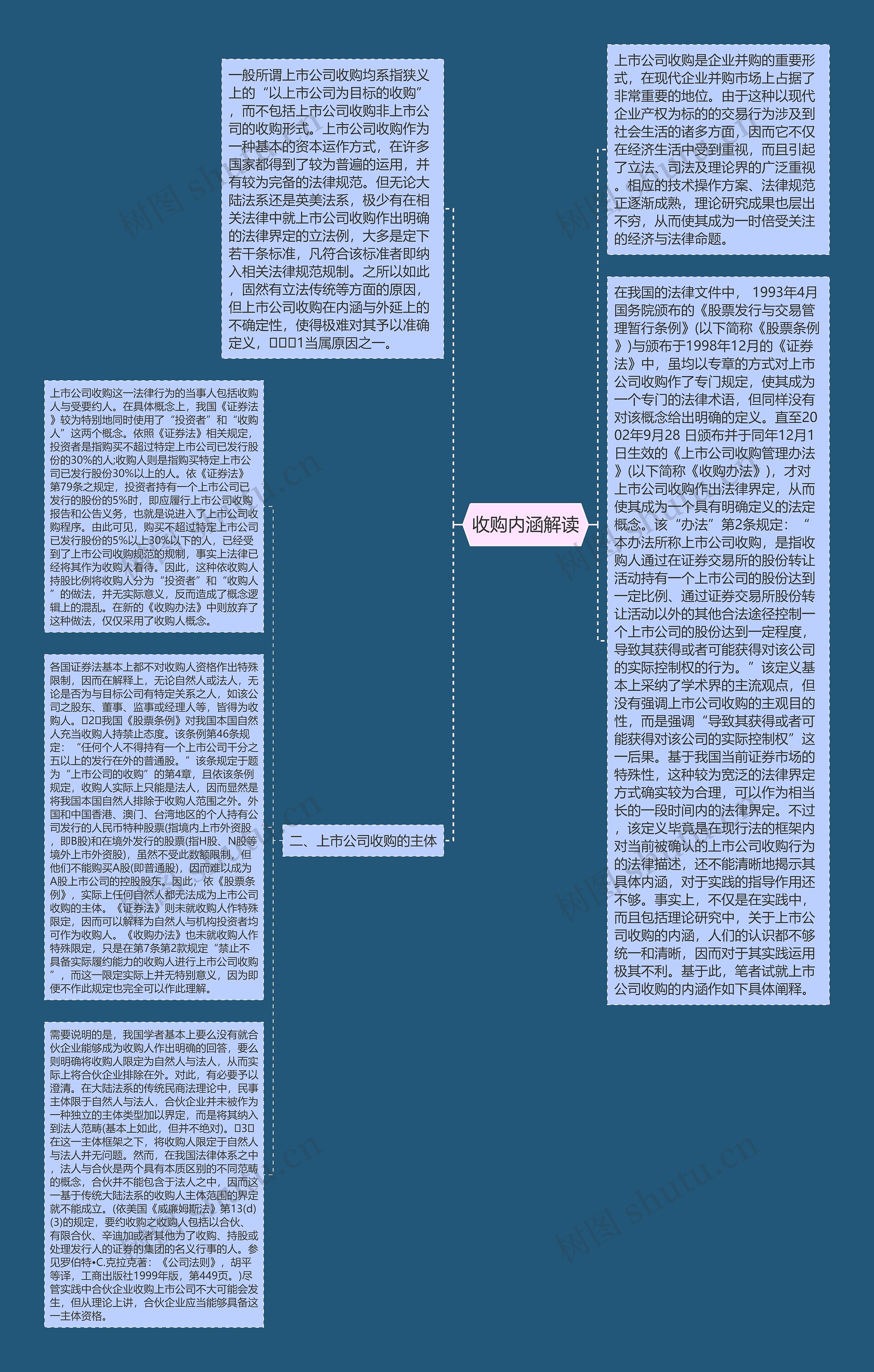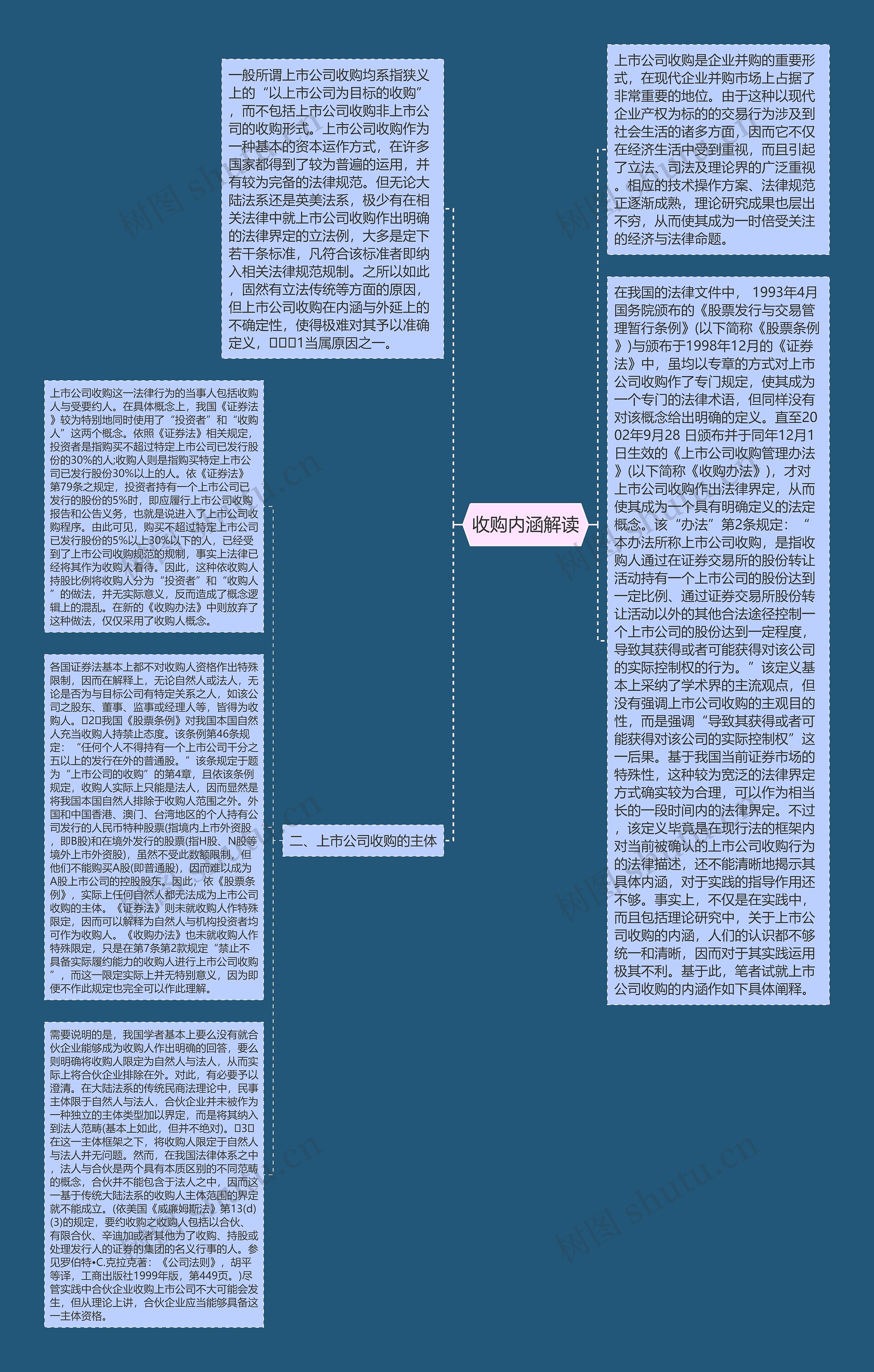上市公司收购这一法律行为的当事人包括收购人与受要约人。在具体概念上,我国《证券法》较为特别地同时使用了“投资者”和“收购人”这两个概念。依照《证券法》相关规定,投资者是指购买不超过特定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的30%的人;收购人则是指购买特定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30%以上的人。依《证券法》第79条之规定,投资者持有一个上市公司已发行的股份的5%时,即应履行上市公司收购报告和公告义务,也就是说进入了上市公司收购程序。由此可见,购买不超过特定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的5%以上30%以下的人,已经受到了上市公司收购规范的规制,事实上法律已经将其作为收购人看待。因此,这种依收购人持股比例将收购人分为“投资者”和“收购人”的做法,并无实际意义,反而造成了概念逻辑上的混乱。在新的《收购办法》中则放弃了这种做法,仅仅采用了收购人概念。
各国证券法基本上都不对收购人资格作出特殊限制,因而在解释上,无论自然人或法人,无论是否为与目标公司有特定关系之人,如该公司之股东、董事、监事或经理人等,皆得为收购人。2我国《股票条例》对我国本国自然人充当收购人持禁止态度。该条例第46条规定:“任何个人不得持有一个上市公司千分之五以上的发行在外的普通股。”该条规定于题为“上市公司的收购”的第4章,且依该条例规定,收购人实际上只能是法人,因而显然是将我国本国自然人排除于收购人范围之外。外国和中国香港、澳门、台湾地区的个人持有公司发行的人民币特种股票(指境内上市外资股,即B股)和在境外发行的股票(指H股、N股等境外上市外资股),虽然不受此数额限制,但他们不能购买A股(即普通股),因而难以成为A股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因此,依《股票条例》,实际上任何自然人都无法成为上市公司收购的主体。《证券法》则未就收购人作特殊限定,因而可以解释为自然人与机构投资者均可作为收购人。《收购办法》也未就收购人作特殊限定,只是在第7条第2款规定“禁止不具备实际履约能力的收购人进行上市公司收购”,而这一限定实际上并无特别意义,因为即便不作此规定也完全可以作此理解。
需要说明的是,我国学者基本上要么没有就合伙企业能够成为收购人作出明确的回答,要么则明确将收购人限定为自然人与法人,从而实际上将合伙企业排除在外。对此,有必要予以澄清。在大陆法系的传统民商法理论中,民事主体限于自然人与法人,合伙企业并未被作为一种独立的主体类型加以界定,而是将其纳入到法人范畴(基本上如此,但并不绝对)。3在这一主体框架之下,将收购人限定于自然人与法人并无问题。然而,在我国法律体系之中,法人与合伙是两个具有本质区别的不同范畴的概念,合伙并不能包含于法人之中,因而这一基于传统大陆法系的收购人主体范围的界定就不能成立。(依美国《威廉姆斯法》第13(d)(3)的规定,要约收购之收购人包括以合伙、有限合伙、辛迪加或者其他为了收购、持股或处理发行人的证券的集团的名义行事的人。参见罗伯特•C.克拉克著:《公司法则》,胡平等译,工商出版社1999年版,第449页。)尽管实践中合伙企业收购上市公司不大可能会发生,但从理论上讲,合伙企业应当能够具备这一主体资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