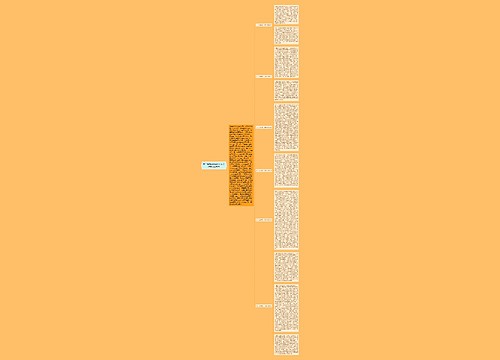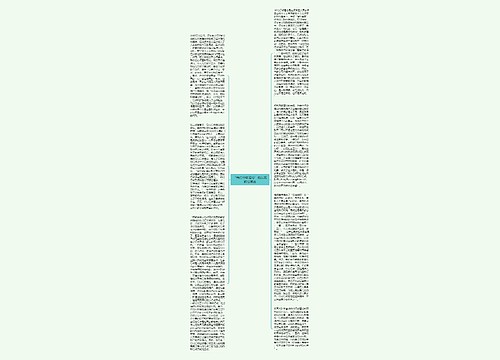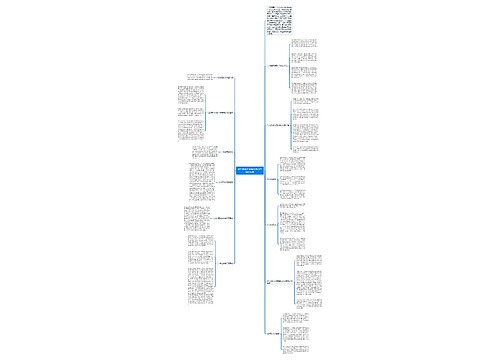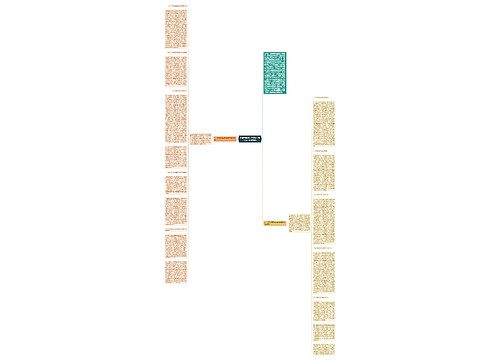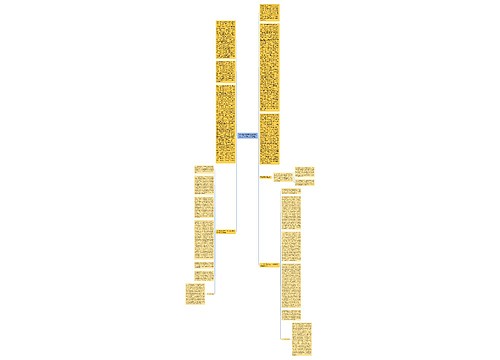第一,科学地界定了非法言词证据的内涵及外延。非法证据包括非法的言词证据和非法的实物证据。由于什么是非法实物证据,国内外都存有争议。这一次规定中,只科学地界定了非法言词证据。《非法证据排除规定》开宗明义,在第一条就规定:“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取得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属于非法言词证据。”非法言词证据概念的核心问题是如何界定“非法”问题,“非法”有一般违法和严重违法,所取得的证据有非法证据与瑕疵证据之分。笔者认为,关键是要紧紧抓住是否侵犯了被讯(询)问人的宪法所规定的基本权利,不能把一般的程序违法的证据统统称之为非法证据加以排除。例如,《办理死刑案件证据规定》第十四条就规定了证人证言的收集程序和方式有瑕疵的,通过有关办案人员的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可以采信。
另外,关于“非法手段”的内涵和表述问题,也是界定非法证据概念的一个关键问题。我们习惯于把非法界定为“刑讯逼供”和暴力、威胁等。其实这种界定与我国参加并批准实施的一些国际条约的对“非法”所规定的内容相比,仍不够明确。综合一些国际条约关于“非法”的界定,一般包括:①暴力取证;②精神折磨的方法取证;③用不人道的方法所获取的证据;④使用药品取证等等。
第二,明确规定了排除非法证据的诉讼阶段。根据《非法证据排除规定》,非法证据的排除,在刑事诉讼法的审查批捕、审查起诉、庭审宣读起诉书后,法庭辩论结束前均可进行依法排除。
第三,排除非法证据的范围。根据《非法证据排除规定》,对于非法言词证据,包括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证人证言、被害人的陈述,适用绝对排除的原则,该规定第二条明确指出:“非法言词证据,应当依法予以排除,不能作为定案根据。”对于非法实物证据,适用相对排除,即附条件排除的原则,该规定第十四条指出:“物证、书证的取得方法严重违反法律规定,致使严重影响公正审判的,该物证、书证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非法实物证据是否排除,以是否严重影响公正审判为条件。这样规定是由于实物证据不同于言词证据,当前我国取得实物证据的手段、条件尚不完备,我们对非法证据排除的范围还不能像英美各国那样,全部实行绝对排除,对非法实物证据只能实行有限排除,附条件地排除。
第四,比较详细具体地规定排除非法证据的程序。《非法证据排除规定》对如何排除非法证据规定了具体的操作规程,这些具体的程序对于避免因为采纳非法证据而导致冤假错案的发生将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些程序包括:①程序的启动。《非法证据排除规定》的第四、五、六条规定了比较详细的启动程序,一是启动的主体由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提出;二是启动的形式,可以是书面的,也可以是口头的,口头告诉的由人民法院工作人员或辩护律师作出笔录,并由被告人签名或者捺指印;三是启动的时间,可以在开庭前,也可以在起诉书副本送达后开庭前,或开庭中;四是启动的内容,包括涉嫌非法取证的人员、时间、地点、方式、内容等相关线索或者证据。对于由辩方启动说明以上各项内容,笔者认为这是当事人行使辩护权的一项重要的诉讼权利,不能混同为举证责任,更不能随意提什么“证明责任倒置”。②法庭审查和法庭调查。③控方负举证责任及证明方法。《非法证据排除规定》不仅明确了非法证据证明责任由公诉方承担,而且还明确规定了证明的方法,如提供讯问笔录,提交原始的讯问录音录像,提请法庭使有关在场人员出庭作证,依法通知讯问人员(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等等。④双方质证程序。第七条的最后一款规定:“控辩双方可以就被告人审判前供述取得的合法性问题进行质证、辩论。”⑤法庭处理程序。根据《非法证据排除规定》“对被告人审判前供述的合法性,公诉人不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或者已提供的证据不够确实、充分的,该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根据这些规定,法庭对被告人审判前供述的合法性问题作出裁定:如公诉人的证明达到确实、充分的尺度,能够排除被告人审判前供述属非法取得的,法庭确认该供述的合法性,准许当庭宣读、质证;否则,法庭对该供述予以排除,不作为定案的根据。
《办理死刑案件证据规定》不仅确立了刑事诉讼的若干证据规则,更重要的是该规定的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用了三十六个条款详细地规定了各类各种证据的审查、认定和证据的综合审查和运用。其突出的特点是彰显程序,反映过程,联系实际,解决问题,体现正义。
我国1996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关于证据的规定只有8个条款,包括:①证据及其种类;②证据收集的一般原则;③运用证据的原则;④向单位和个人收集证据;⑤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⑥证人证言的审查判断;⑦证人的资格与义务;⑧证人及其近亲属的保护等。就以上8条规定的内容而言,原则、笼统、可操作性不强。新出台的规定针对刑事证据的收集、审查、定案等诉讼各个环节的运用,作了比较详细的规定,一改过去的原则、笼统之弊,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对刑事诉讼法的修正和发展,是刑事诉讼法再修改的前奏。
关于全案证据的综合审查和运用,尤其是法官如何准确地行使自由裁量权,怎样才能做到公正、公平,实现实体正义,《办理死刑案件证据规定》结合我国的情况,总结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实际经验,要求办案人员从各个证据与待证事实的关联程度,各个证据之间的联系等方面进行审查判断,并规定了一个判断的标准,即合理排除矛盾,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还规定了法官对存疑证据的处理程序;“法庭对证据有疑问的,可以告知出庭检察人员、被告人及其辩护人补充证据或者作出说明;确有核实必要的,可以宣布休庭,对证据进行调查核实。法庭进行庭外调查,必要时可以通知出庭检察人员、辩护人到场。出庭检察人员、辩护人一方或者双方不到场的,法庭记录在案。”(见第三十八条)。
鉴于量刑程序改革的成果即将在全国各级人民法院推广,量刑证据的调查和运用是当前实务部门急需解决的一个问题。《办理死刑案件证据规定》的第三十九条对被告人有立功、自首情节的证据,如何调查和运用也作了具体规定:“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提出有自首的事实及理由,有关机关未予以认定的,应当要求有关机关提供证明材料或者要求相关人员作证,并结合其他证据判断自首是否成立。”

 U633687664
U633687664
 U582679646
U5826796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