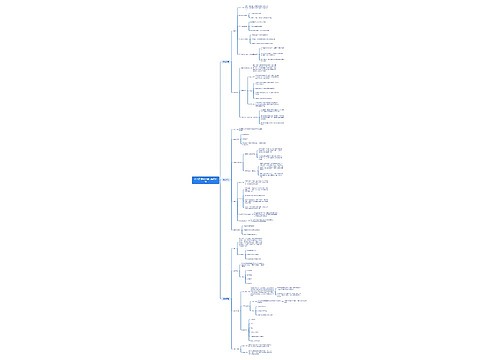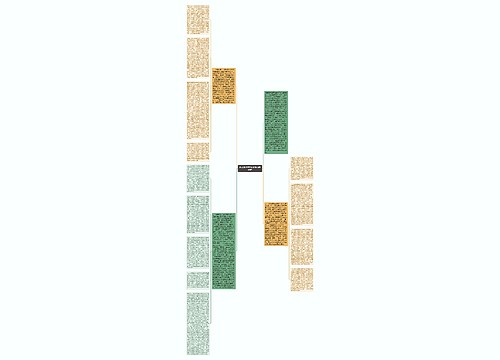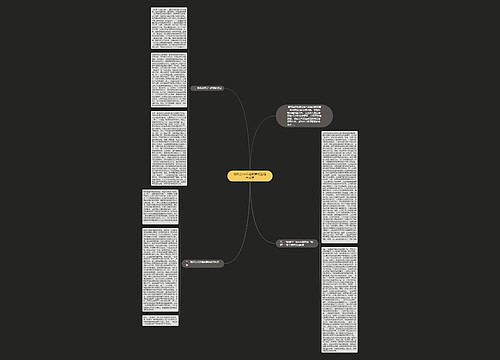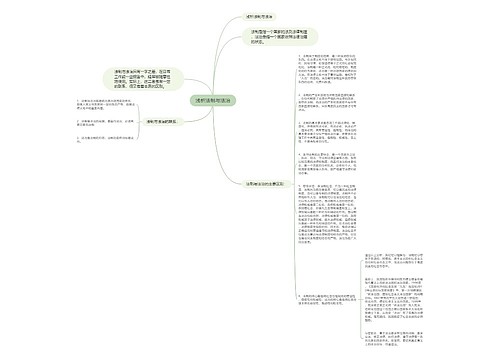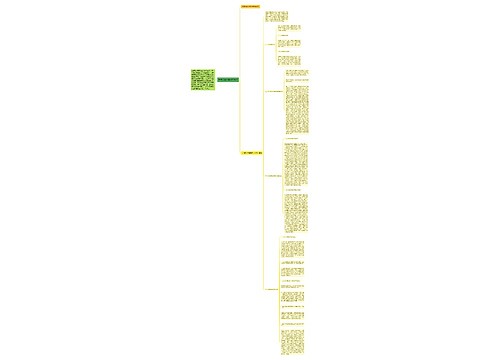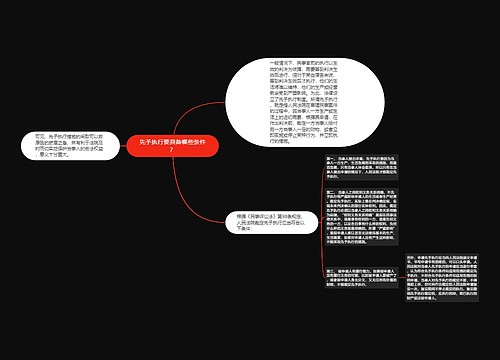(1)在立法基本理念上,重视环境刑法的生态本位、自然生态环境的极端重要性,强调环境刑法的基本价值追求应是通过对犯罪行为科处刑罚而实现一般预防的作用。
从现行规制环境犯罪行为的法条在刑法第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出现的事实,我们可以推断出现行环境保护规制制度在本质上是为了维护环境行政管理秩序,其思想根基是一种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的环境观和利益观。“现行环境刑法不过是人类控制自然驾驭自然地众多机器中的一部,机械化的线性思维方式贯穿其中,我们在工业文明的机器轰鸣声中依然能够感受它的滴答声。自然界自身的利益是被忽视的,正因为能够给人类带来经济效益,所以才被称为自然资源”。我们目前对环境犯罪的管制从起步阶段就存在巨大的局限,把环境问题仅仅视为一种经济核算问题,把环境质量看作是一种市场中的产品,可以由计算来决定。因此,只有摆脱了传统人类中心主义的环境观的局限,才能获得一种整体生态主义的视角,以期达到对环境犯罪的全面系统的通盘考虑,改变“头疼医头,脚疼医脚”、“防不胜防,治不胜治”的尴尬局面。
(2)法定刑的规定上,笔者强烈建议将现有环境刑法体系中的法定刑规定升格,加大对犯罪行为的惩治力度。笔者已在文中多次提到环境犯罪危害结果的极端性、不可逆性,反观现行的环境刑法对于环境犯罪行为的处罚却远远没有体现出与其犯罪结果的均衡性。
现行环境刑法的行政从属性直接导致了对环境犯罪的处理过分依赖行政处罚手段而忽视了刑法手段的运用的现实,由于环境犯罪长期被视为一种短期危险而迟迟没有得到司法机关应有的重视,以及片面追求经济效益而导致的地方保护主义、部门保护主义而产生的内部效应的干扰,相当数量的环境犯罪事件并没有受到刑法的追溯,而仅仅是被处以行政处罚。这种打击环境犯罪的现状根本无法引起犯罪分子的畏惧,反而助长了犯罪分子的嚣张的气焰。因此,笔者建议,立法机关应本着务实、高效的态度出台更加严格的刑事法律规定打击猖狂的环境犯罪,同时争取在短期内成功处理一到数个影响较大的案件以达到“敲山震虎”的效果,消除部分犯罪分子及潜在的“犯罪人”认为可以逃避刑事追究的侥幸心理,以期达到预防犯罪发生的环境刑法应然的价值追求。
(3)在犯罪既遂的规定上,增设危险犯与故意犯。在环境犯罪的各种罪名中,绝大多数是以结果犯作为科处刑罚的前提。但是环境污染特别是土地污染、水环境污染,造成严重后果的过程,往往是一个累积的过程,要经过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才能完全地显现,而且造成的严重后果是不可计量的,不可逆转的。在国际上,一些工业化国家的环境立法中早就有关于危险犯的规定。因此,笔者认为,我国刑法也应增加对环境犯罪危险犯的规定,以充分发挥刑法的预防作用。
此外,我国刑法学界目前普遍认为重大污染事故罪为过失犯罪。但在现实生活中,经常发生企业偷排有毒有害物质造成严重后果的案件,像这一类的案件,企业的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不可能不知道这些有毒有害物质的成分以及危害程度,而仅仅是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采取了恶劣的损害生态环境的行为。因此,笔者建议,在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中应增加故意犯罪的处罚,而且要从重处罚。
(4)改进污染损害举证规则,引入“过错推定”制度。在司法实践中,排污单位往往很容易利用其自身在行业、技术上的压倒性优势证明其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而绝大多数污染受害者个人没有技术能力和条件掌握排污单位内部的实际排污种类和浓度等证据,因而无力反证排污单位的所谓“证明”。因此,我们应改进环境犯罪的举证规则,引入“过错推定”制度,即推定排污者有过错并应承担责任,除非其能够反证。
环境刑法这个称谓,是在刑法这个属概念之前添加了“环境”这个限定词,一方面表明环境刑法与刑法之间存有种属关系,另一方面表明作为种概念的环境刑法已经与刑法属概念相剥离并区别于普通的刑法。作为一门新近的、相对独立的刑事法学科,其理论研究的新触点带给理论界和实务界一种迥异于传统的思辨方式,使传统的刑法理论受到多方位的冲击。理论工作者应勇敢的面对环境刑法对传统刑法理论的挑战,结合环境犯罪自身独有的特点,修正、改进现有的刑法理论,使理论与现实相契合,也只有这样环境刑法才能肩负起对抗环境犯罪的重任,才能实现更有效地打击、遏制环境犯罪。刑罚目的作为刑法理论中的核心部分,其重要性不言自明,在环境刑法的大语境之下,必须重视、端正对环境犯罪科处刑罚的目的是实现一般的预防犯罪的作用,而不是正义的报应,而后,进一步完善以一般预防为目的相配套的刑事法律规定。惟其如此,环境刑法的机能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各类法律主体在进行生产、生活活动时才能恪遵国家的相关规范,才能达致对人类生存极端依赖的自然生态环境以及行政环保制度有效的保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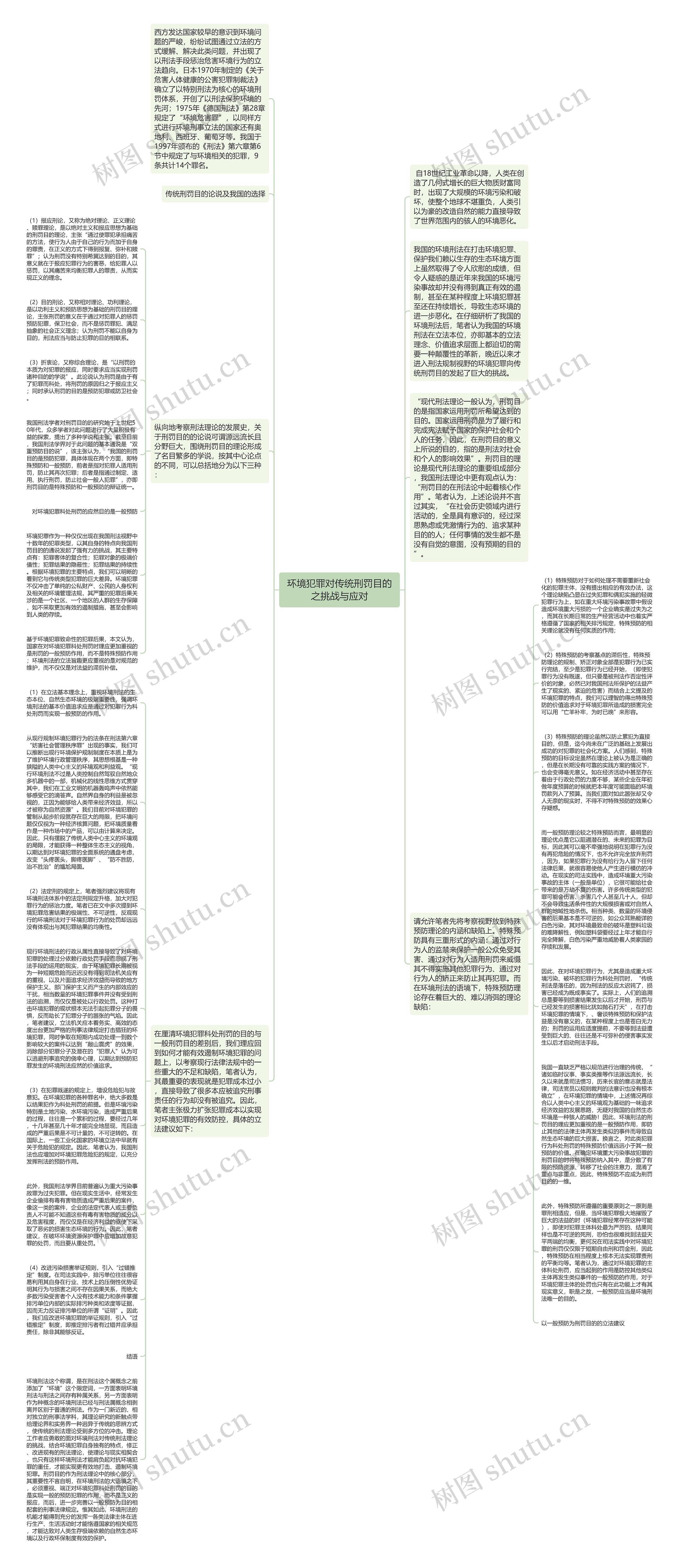
 U582679646
U582679646
 U882673919
U8826739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