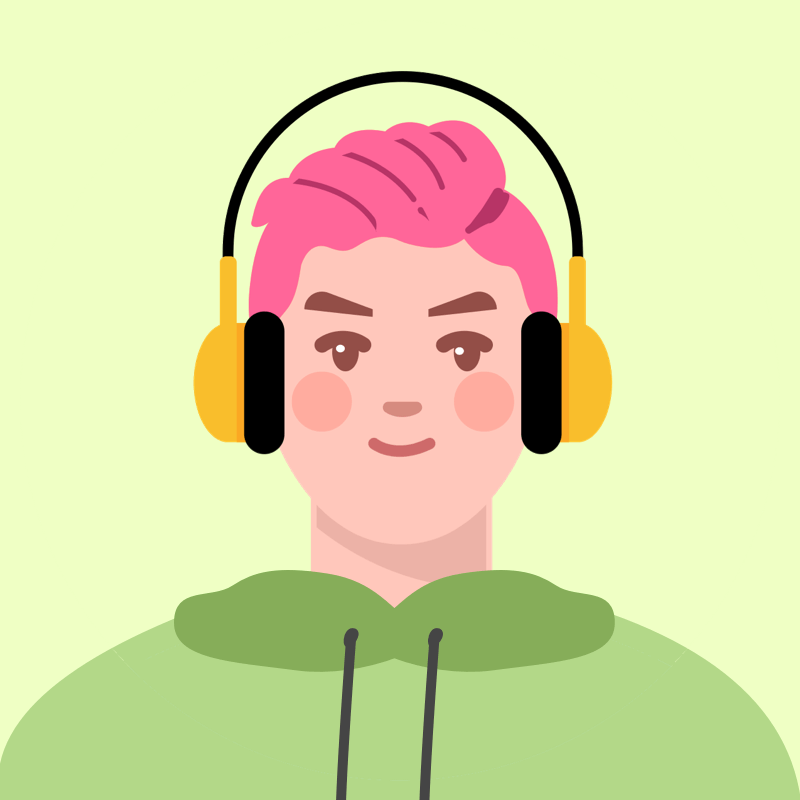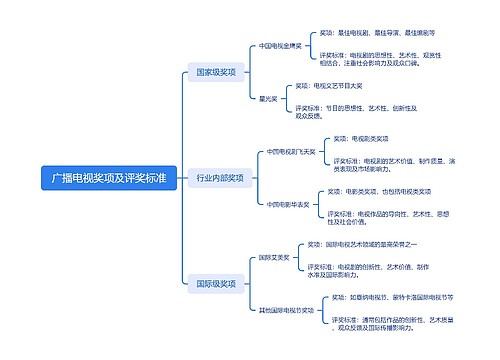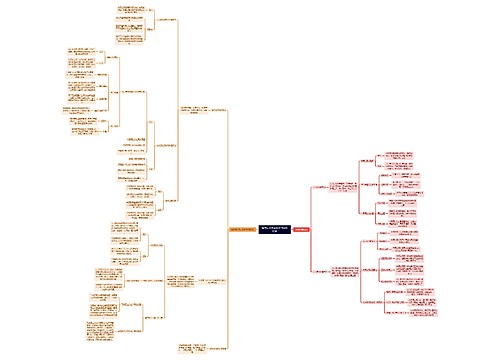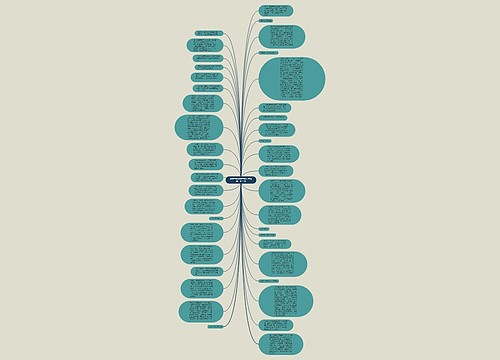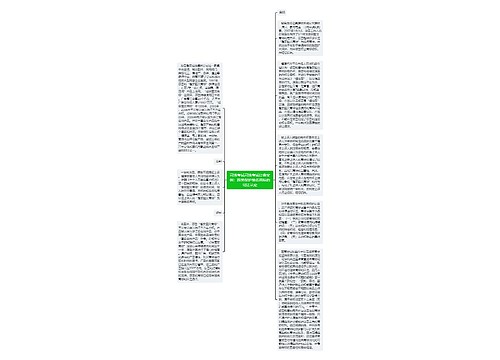在本案中,原告已经向房地产管理部门申请了过户登记,这时发现陆小峰实为无权处分,如果后来登记成功了,原告是否还符合善意的主观要件呢?认定受让人主观善意应以何时为准,对这一问题的不同认识将直接影响到对本案的判决,也是本案的主要分歧所在,具体而言存在三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应当以签订合同时为准,理由是不动产登记是以国家信用为保障的,如果要求不动产的受让人除了要了解登记薄的状况之外,还要去承担额外的审查义务,这不但对于受让人不公平,也不利于商品的自由流转。因此,只要受让人在签订合同时履行了注意义务就应推定其具有主观善意。本案中原告基于对房产证记载事项的信赖而与被告签定了房屋买卖合同,已经尽到了必要注意义务,且原告已经支付了合理对价并已实际入住,为维护我国房产登记制度的公示公信力、保护交易安全,应当认定原告基于“善意”而“取得”讼争房产,判决两被告继续履行合同,协助办理房产过户登记手续。周忠兰则可以通过诉讼,要求无权处分人陆小峰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
第二种观点认为应以登记完毕时为准,理由是我国《物权法》规定受让人在受让时应为善意,受让即为接受让予之意,一个完整的受让过程应当完成所有权的转移。动产所有权的转移以交付为准,不动产所有权的转移则应在登记后始为发生,因此只有在登记完毕时仍为善意者,才适用善意取得。更何况《物权法》对善意取得的要件明确作出了规定“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已经登记”,其中“已经登记”这一事实行为必须完成,否则无法发生善意取得的效力。本案中原告在过户登记完成之前发现陆小峰为无权处分人,主观上并非善意,又因过户登记客观上并未实际完成,因此不符合《物权法》关于不动产善意取得的主、客观要件。被告陆小峰擅自处分共有人周忠兰的财产,未经周忠兰追认该无权处分行为应属无效。对于因合同无效而导致的履行不能的问题,应建议原告另行要求被告承担违约责任。
第三种观点认为应当以申请登记时为准,理由是鉴于我国目前登记机关众多、混乱,而且登记过程非受让人所能左右,以申请时为准更能保护受让人的权益。即使在登记过程中知道让与人无处分权,也不妨碍善意取得的适用,只要受让人提出登记申请时为善意即可。例如,《德国民法典》第892条第2项便规定:“为取得权利而有必要进行登记的,对于取得人的知情,以提出申请的时间为准,或在依873条有必要成立的合同嗣后才成立时,以合意的时间为准”。本案中叶冰松与陆小峰已在房屋过户申请表上签字,应视该房产交易行为已经完成登记,叶冰松基于善意取得获得该讼争房屋的所有权,被告周忠兰可以通过另行起诉要求陆小峰承担侵权责任。
笔者认为上述第一种观点混淆了主观善意与善意取得之间的关系,误认为只要受让人主观“善意”便应当拥有“取得”转让物的权利,从而将善意取得简单地理解为一种债权债务关系。其实,主观善意仅是构成合同有效的条件之一,依法理“任何人不得处分不属于自己的财产”,当无权处分人处分他人财产又未得到原权利人追认时,即使受让人主观善意该合同亦是无效的。而存在无权处分行为却是善意取得制度得以发生的前提,善意受让人并没有一个合法的有权取得,才会发生所有权取得的例外规则。设立善意取得制度其目的并不在确认一种债权债务关系,善意取得是基于法律所确定的事实行为而取得物的所有权,是一种原始取得的方式。主观善意也并不必然地导致发生物权转移,只有当受让人主观上善意,支付对价并按照法律要求办理了登记,不动产善意取得始为发生。
对于第三种观点,将当事人申请登记视为登记完成,的确有助于更好地保护受让人的合法权益,存在相当的合理性。但除非有司法解释予以明确规定,否则如此理解《物权法》关于不动产善意取得的规定,尚缺乏法律依据。
因此,笔者同意第二种观点,根据我国《合同法》第51条规定,在未得到共同共有人追认的情况下,对于无权处分人陆小峰擅自处分周忠兰的共有财产的行为自然是无效的。并且,因为本案中因不动产登记尚未完成,物权变动这一事实行为并未发生,原告不能根据不动产善意取得制度取得讼争房屋的所有权。
当无权处分人擅自处分原权利人的财产时,原权利人和善意受让人的合法权利都有可能受到侵害,保护了其中一方的物权,另一方就只能通过提起侵权或违约之诉实现救济,然而债权的保护毕竟不如物权的保护直接有力。换言之,取得争议不动产物权的一方得到了最大程度的保护,善意取得是国家立法在衡量原权利人和受让人的利益保护力度后进行的一种制度安排。我国《物权法》规定不动产善意取得必须在完成登记后才能实现,在最大程度上为原权利人保留了发现权利被侵害的时间,可见对原权利人的保护力度还是较大的。在对不动产善意取得制度的具体司法适用中,我们应充分理解《物权法》平衡这两种保护关系的立法原意,充分考查原权利人和善意受让人是否尽到了必要的注意义务,根据各自的过错程度,确定物权的最终归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