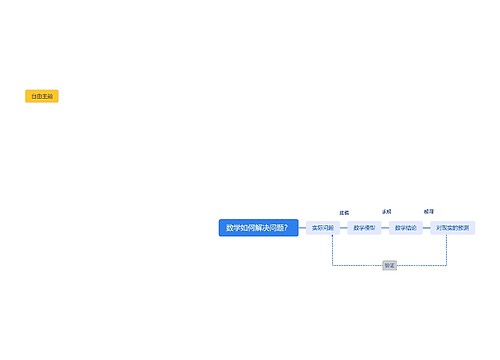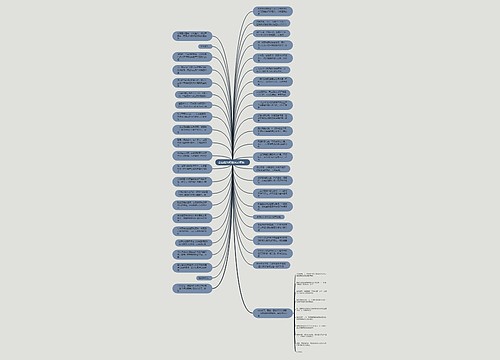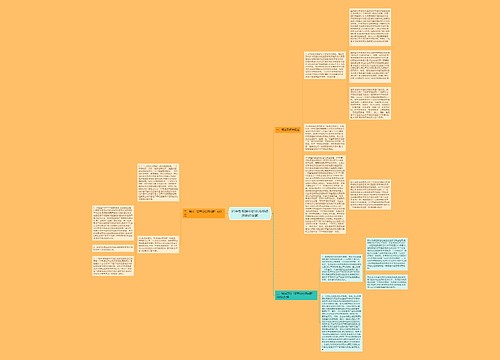在大陆法系国家,特别是我国,尤为强调司法解释作为一种权力的单独存在,而且通过法律明确限定了司法解释权的主体。这导致了对一个实际情况的忽略,即法官在适用法律过程中事实上不可避免的需要法律解释,也就是说实现法律适用离不开司法解释这一重要手段;而在英美法系国家,法院是行使司法权的当然主体,因而法官在履行司法职责时,解释法律成为他们扮演裁判者角色不可或缺的一种重要手段。正如美国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法学理论家之一,本杰明·内森·卡多佐所言:“对于各个案件,由制定法提供的一般框架应当通过解释——即贯彻制定法的一些原则——的方法来填满。毫无例外,在每个案件中,法院的事务都是为制定法提供其所省略的东西,但又总是通过一种解释的职能来完成的。” 可见,在英美法系,司法解释更多的体现为一种完成职能的手段,也就是说,不把司法解释单独列为一种权力,它是司法权的组成部分或自然延伸,如果说一定要把它解读成一种权力,那也是附着在司法裁判过程中不可剥离的一种权力。
从上文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制度的不同,法律环境的差异,对司法解释的理解也会存在分歧。WTO法律制度是现代国际法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也是近代发展最快、最新、最富活力的门类,它不仅对传统国际法有不少突破,而且其法律规则从实体内容到程序规范都具有自己的特色,可称作是现代国际法的一个全新的领域。 因此WTO领域的法律制度可谓自成一体,“司法解释”在其环境中同样也有特殊的含义,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WTO中的司法解释是行使司法权的一种职能手段
在WTO组织中,DSB负责整个WTO的“争端解决程序”的运作,行使司法机构的职能;而部长会议和总理事会负责“决策制定程序”,行使立法机构的职能。按照学者约翰·H·杰克逊教授的说法,这实际上是在WTO体系内部进行了横向分配(horizontal distribution),把立法、决策权赋予了部长会议和总理事会,把司法权赋予了DSB。 DSB通过设置专家小组和上诉机构具体执行其司法裁判权。
著名学者Trachtman提出了“契约不完善”(incomplete contract)理论,认为人类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是不断发展的,人们对未来出现的事物常常难以精确预见,因此人们在一个特定的时点上对社会各方面的认识不一定很准确,所以在立法时应保持一定的应变因素,由实际司法机关按照具体情况做出解释予以处理。WTO一揽子协议作为国际“约定”是国际上主权国家之间的“契约”,根据“契约不完善”理论,它亦需要司法解释予以弥补。WTO《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谅解》(Understanding on Rules and Procedures Governing the Settlement of Disputes,以下简称DSU)第3.2条规定:“WTO的争端解决机制是为这个多边贸易体制提供保障和可预见性的中心环节。各成员方认识到,它可用来保持成员方在各涵盖协议中的权利与义务,并可用来按国际公法解释的习惯规则阐明这些协议中的现有规定”,以及第17.6条:“上诉限于专家小组报告中包括的法律问题,以及专家小组所做的法律解释”,这些都是专家小组和上诉机构进行司法解释的正当性依据,而且专家小组和上诉机构在实际的争端案件中做出了许多典型性、具有说服力的解释。因此,专家小组和上诉机构承担着WTO中司法解释的职能是不容置疑的事实。
WTO的法律制度为DSB、专家小组、上诉机构设定了管理争端解决的职责,为了实现这个职责,上述主体就必须正确的适用WTO法律,而实现正确适用WTO法律的重要手段就是司法解释。因此,综合以上种种, WTO中的司法解释可以定位为:裁判者为实现法律适用而运用的职能手段。

 U182637395
U182637395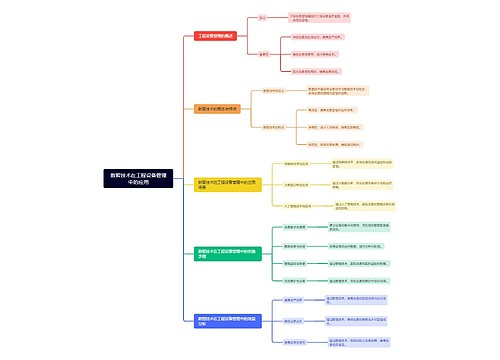
 U575789758
U5757897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