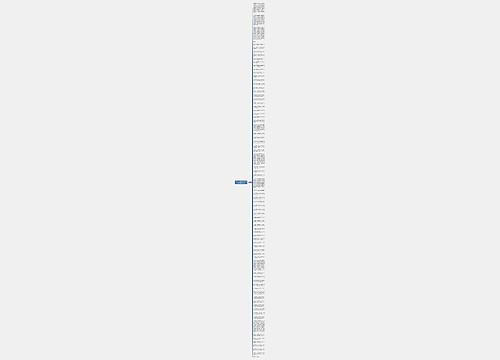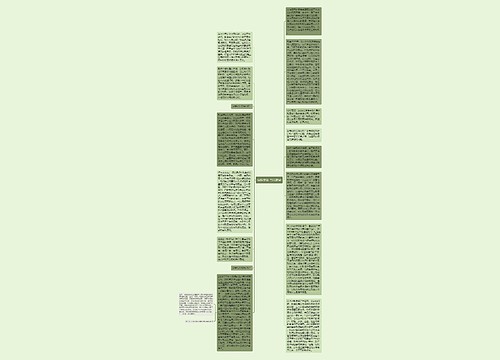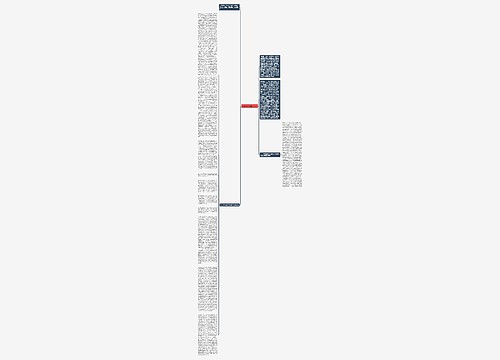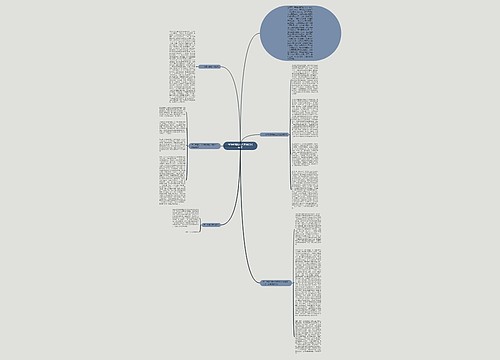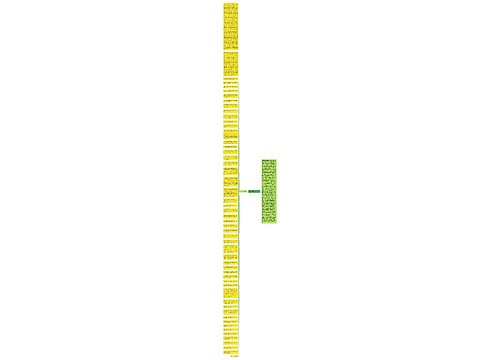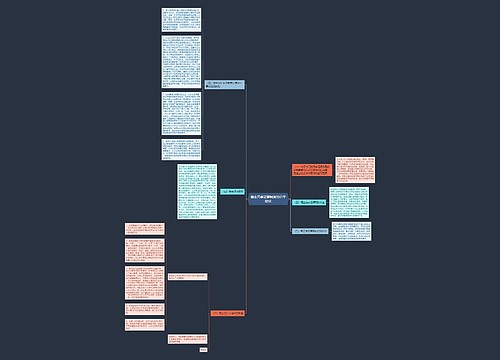第一,法官适用公序良俗条款的作业契合了我国传统的非科学的思维方式。“在中国文化中,理性思维的独立性一直未受充分的重视,人们往往将一些应分、可分的观念混为一谈,或以自信之理充当必然法则,以强烈的价值态度去处理实际事务。”[5] 中国的职业法律人大都患有“情绪化”的毛病,不注重进行严格的建立在对相关事实的细致分析和严密的法律规则运用之上的法律推理。我国法院判决书中经常使用“手段残忍”、“罪大恶极”、“民愤极大”、“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等用语,以打动听众情感,并为判决寻求道义根据[6]. 关涉公序良俗要件的规定并既未能为当事人提供明确的行为模式,也未能为法官提供可操作的裁判依据,因此,在私法中的适用,极易助长法官在此种传统思维惯性的主导下进行不慎重裁判的倾向。
第二,公序良俗条款体现了私法中的非理性因素。包括公序良俗在内的道德标准是私法中的非理性因素。不管我们是否承认道德判断中是否存在理性判断的成分[7], 但其内涵着价值判断的因素却是无法否认的。作为价值判断,道德纯粹是每个人发自内心的感受和选择,是一种“非常个人化的实践”,人们对自己行为的欣慰和不安,即是道德力量之所在。[8]由于公序良俗要件的存在,使得当事人所实施的法律行为虽然尚未违背法律明定的某一强制性规范,但其也有可能被裁判者确认为无效,也就是说,“法无禁止皆自由”规则在此处的适用受到限制,亦即即使尚无法之禁令,行为人也不得随心所欲的实施行为,这肯定会影响到行为的安全性。公序良俗条款的适用,“不能透过传统的逻辑三段论,将具体法律行为或契约,直接认定为违背公共秩序善良风俗,而导出无效的法律效果,”[9]反而是需要法官在个案中进行价值补充,这就使得当事人难以获得稳定的预期。此种非理性因素的存在极易导致法官关于法律行为有效与否的判决的恣意性。
第三,公序良俗的内涵与外延难以界定。法官要运用公序良俗条款去判断法律行为的效力,首要的问题是确定公序良俗的内涵。虽然“一个概念必定具有无争议的意义的核心,因为要不然,就没有理由认为许多解释针对的是同一事物。”[10]很早以前亚里士多德就指出,“陈述应该满足于粗略大致地表明真理,对每一类事物的精确性的追求,只求达到该学科本性所认可的地步,这才是明智之士的标志。”[11]意大利学者布鲁诺?莱奥尼也指出,“某词的含义的共同底线是存在的”[12]. 但是,“当人们着手使某一术语更加精确时,结果发现,他用来消除所论及的模糊性的那个术语本身又是模糊的,因此,消除一个给定术语的所有模糊性,这是一个不切实际的目标。我们所希望做到的,至多渐渐地接近于消除模糊性。”[13]公共政策一词,本身并没有十分确定的含义,“有时候它所包含的内容,完全就是法律演变过程中,立法或司法功能上,最根本的伦理、政治和社会等诸原则和概念;而某些时候,它本身就只是一法律名词,而意味着'公共利益的好处',意即任何合法行为,若有侵害大众或违反公共利益之虞时,即应加禁止。”[14]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各国的法官们也不遗余力地努力着,将善良风俗或者公共政策的概念尽可能清晰地演化为法律的原则,将各种不同的案件分门别类并发展出具体的界限和标准,以便于在将此原则当成合同的一般条款时避免错误的理解。[15]然而,虽然“长期以来,许多学者就试图清晰地界定公共秩序的范围(内涵和外延),但是界定公共秩序的尝试却从未成功过。”[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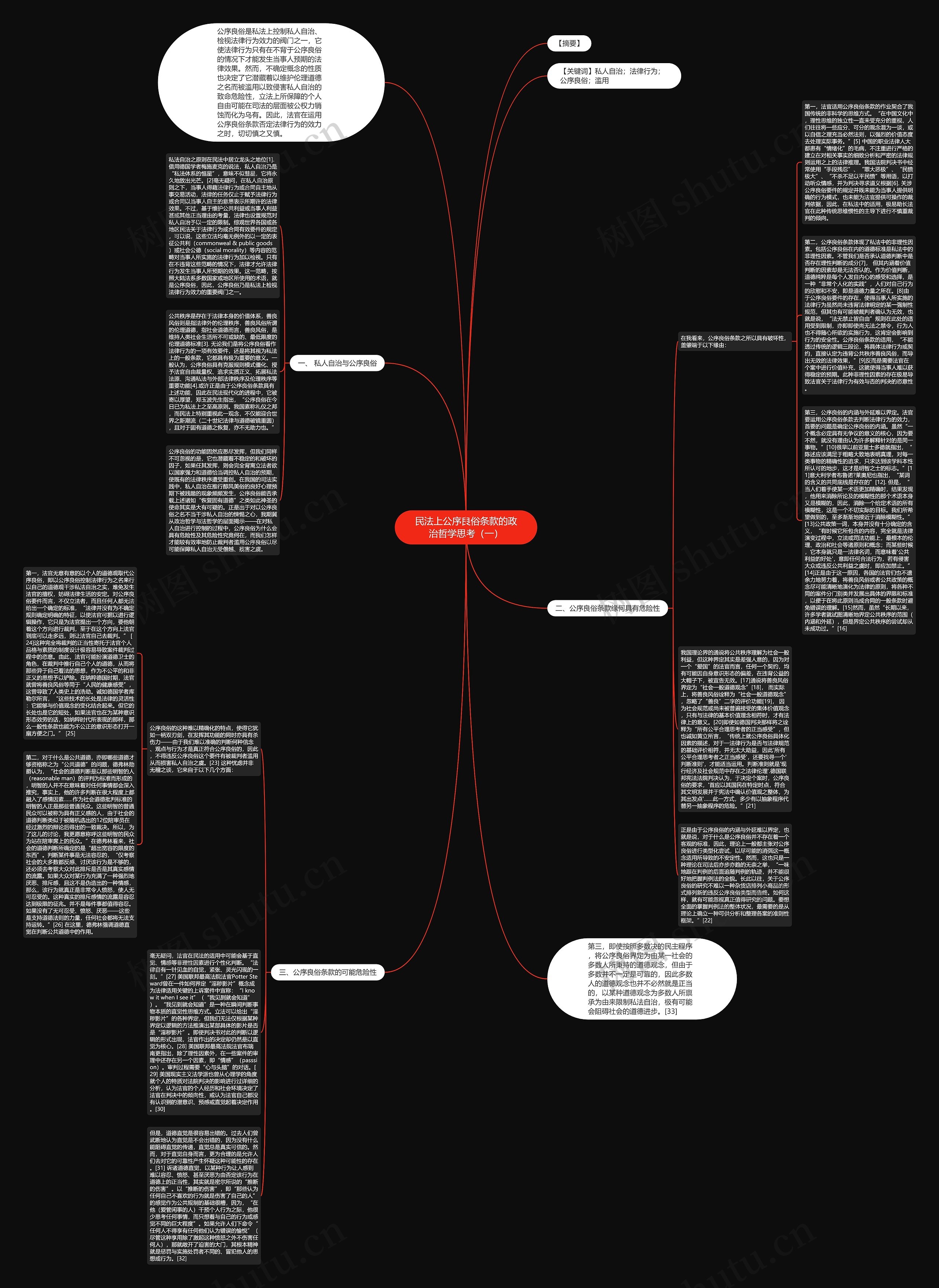
 U682687144
U682687144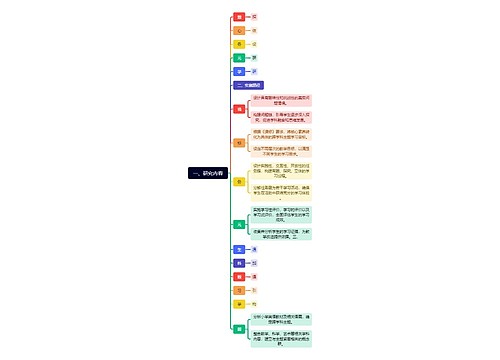
 U633687664
U6336876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