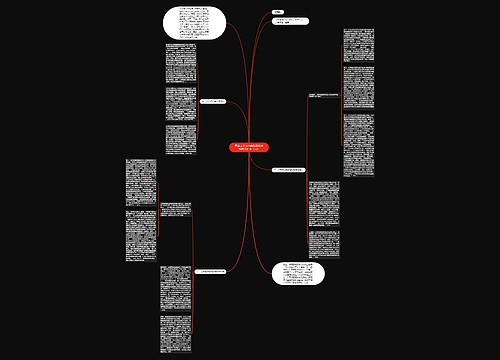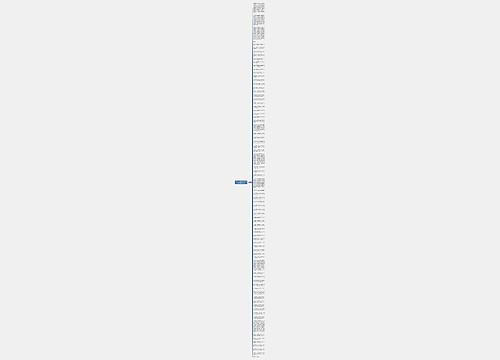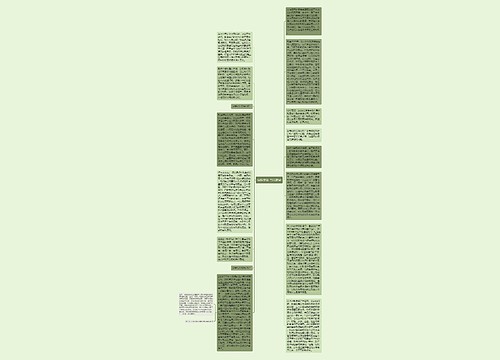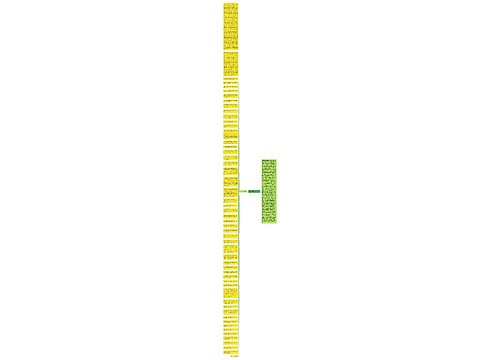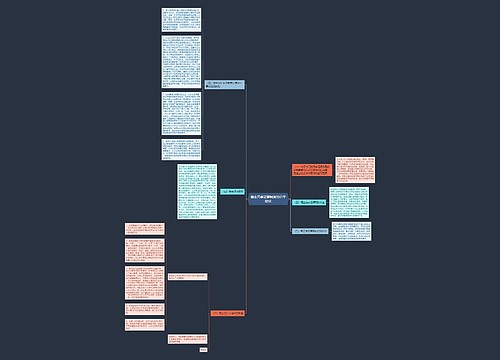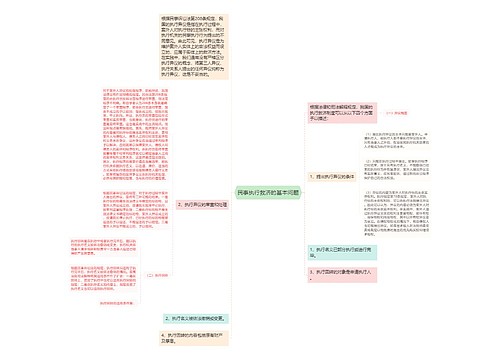我国近三十年的变革历程,使法律这种社会关系的调整机制越来越受人们垂注。尽管法律人不断抱怨法律的不力,其他公民抱怨“法律顶个球”,但和法律相关的权利意识、追责理念、义务关注等等,在公民交往中,明显增强。在公民尚不甚满意的政府行为中,公务员们行为中的法律自觉也在明显增加,而不是减少。十多年前,鄙人给司法局的大人们讲法律,不少观念让他们瞠目结舌。但年前本埠某市司法局长率领其要员亲临陋室,谈及该市今年依法行政建设之规划,令我大为震惊:他们对相关行政法律的熟悉、对依法行政理念的理解,对依法行政之具体技术方法的设计……已经远远超出了往往自命不凡、指手画脚的法学者(不仅指别人,也指笔者自己)的见识。尽管在行政实践中,他们的知识和见识未必能贯彻到底,但这种法律知识和见识的增长,确实让人为之动容!
但这是否意味着我国实在法已然艳若桃花,美妙绝伦?倘若联系到我在前文中申明的基本前提和姿态,则至少可以检讨者有二:其一是我国作为一个幅员辽阔、文化多样、习俗纷繁的国度,在立法上,尽管有个别的法律草案实现了公开发布、公开或半公开地讨论的机制(尚未形成程序),但法律的起草,几乎是一个书房里的作业。本人的一些个友人,也不时参加一些法律文献的起草。但他/她们究竟对我们这个国家国民的日常交往方式了解多少?很令人生疑。动辄德国立法例如何如何,法国立法例如何如何,日本立法例如何如何……就不见中国国民日常交往生活如何如何,这样起草的法律,你说它究竟是专断的还是民主的?在这样一个大国,实行自上而下的单一制体制模式,其法律究竟是民意之表达,还是官意之贯彻?当这种法律的贯彻在实践中遇到障碍时,反思遇到障碍的民间法的落后性,固然是一个思路。但与此同时,能否留出另一条反思的路线:消蚀了地方自治性、自主性、能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的自上而下的法律体制,凭什么要求人人遵守?就因为它的强制力?如果是这样,这种法律不就变成了刺刀的全方位伸展了吗?
其二是迄今为止,在吾国法律体制外,仍有不受法律制约,但能够对法律进行全方位干预的组织存在。早在两千多年前,吾国先人们就强调“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呢,古人讲特权还强调“法定化”呢,但时至如今,在吾国法律体制中,法外特权组织之特权来源——如所谓“双轨”,究竟国家通过什么法律授权了?作为法学者,不知其然,更不知其所以然。这样的法律体制,能否得到公民的接受?会得到哪些公民的接受?即便公民接受,是因为其自觉参与的接受,还是被迫无奈的接受?是通过公民对话的接受,还是通过“先进组织”训话、教化的接受?我想对这些问题,建议特别关注、青睐权利的兄台多加关注。
职是之故,鄙人以为,吾国当下实在法尽管多如牛毛,但在实在法合法性之根本问题尚存在严重缺陷时,就急吼吼地以实在法消灭我们的生活事实,催生的只能是危险的实在法,而不是民间法的危险。兄以为西方法学家关注实在法之外的社会生活等等,乃是因为其法律完善的缘故。我以为恰恰相反,是法律实证主义的兴起,才真正表明一种相对完备之法律体系在西方呈现的事实。吾国尚不存在这一事实,法律合法性的确认、博弈正在进行中,在此过程中,过分强调实在法和法律实证主义,不过是对“生米做成熟饭”的一种无可奈何的体认。因之,尽管我关注法律实证主义,但之于当代中国法律,更切要的关注,乃是对吾国法律合法性的讨论。我关注到兄的文章中对权利本位的阐发,这是个老话题,尽管我不太赞同在义务比较意义上谈论权利本位的话题,但只要你主张权利本位,就意味着你本身进入到对法律合法性问题的执著中。在此意义上,我们之间似乎又多了一重共识——因为强调国家法律体制对民间法的关注,其实就是强调区域主体、“自治”地方(不仅是民族自治地方)的权利。

 U633687664
U633687664
 U582679646
U5826796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