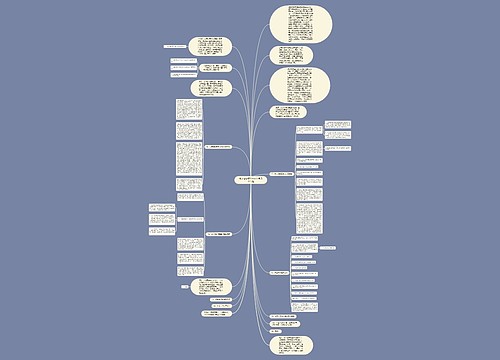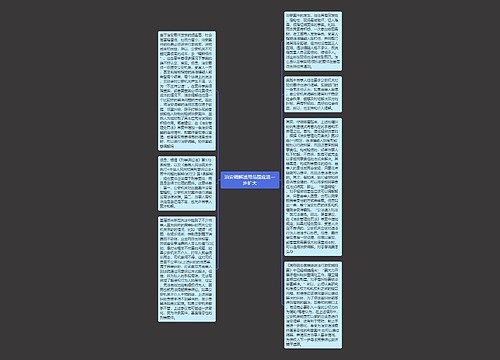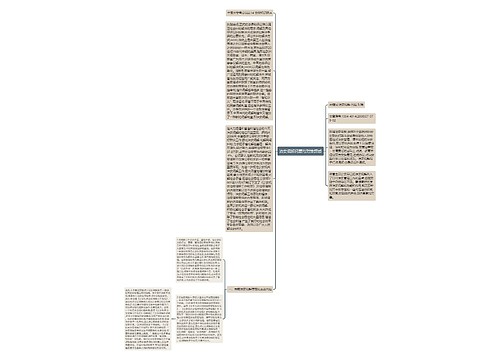(一)对调解的适用范围、条件把握不准,处罚与调解之间的界限模糊。由于民间纠纷概念本身的模糊性,民警对治安案件是否因民间纠纷引起掌握不准,对可以调解的治安案件具体包括哪些行为类型亦不明确;有的民警甚至认为只要是民间纠纷引起的治安案件均需进行调解,认为调解是这类案件的必经程序,将“可以调解”错误理解为“必须调解”。
(二)滥用调解权,以调解代替行政处罚。很多民警办理治安案件有一种强烈的调解偏好,任意扩大调解范围,滥用调解权,如将寻衅滋事,非因纠纷引起的聚众打架斗殴等不符合调解范围的案件也进行调解处理。
(三)重调解,轻取证。实践中存在一种“重调解,轻取证”的错误倾向,有的民警认为,既然是可以适用调解的治安案件,到时候组织双方当事人调解即可,没有必要花时间、费力去做调查取证工作。结果一旦调解不成,事过境迁,该取的证据无法取到,不仅导致难以认定是哪一方的过错,造成案件调解不下去,而且等到需要作出处罚决定时,也因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而处罚不了。这不仅不利于化解矛盾,解决纠纷,而且影响法律的尊严和公安机关的威信。
(四)调解的程序任意性过大。民警对调解处理的治安案件,普遍存在不立案、不组卷的现象,待调解不成需转入治安处罚程序,才办理受案手续。调解的具体方式步骤都没有一套完整规范的统一程序,基本上是各行其是。
(五)久调不结,案件积压。这是治安调解实践中最为突出的问题之一,其形成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有:一是治安调解没有明确的期限限制,民警头脑里没有形成调解的时效意识,抱着能调则调,不能调便拖的办法,奢望当事人不会长时间消耗精力而最终能达成和解,使有些案件一拖再拖,甚至长达一年也没有结果;二是有的民警热衷于治安调解,忽视案件的调查取证,在事实未查清,过错和是非责任未分清的情况下即仓促调解,无原则地“和稀泥”,当事人之间达成调解协议的难度无形中增大,导致久调难结;三是治安调解协议缺乏应有的法律约束力,当事人不能慎重对待自己在调解中的意思表示和主张,稍有不满意就有可能撕毁调解协议或反悔不履行,使得案件的调解出现反复,拖延了调解的时间;四是有的民警对经多次调解不成的,该及时进行治安处罚裁决的不及时裁决,担心处罚可能更加激化当事人之间的矛盾不利于纠纷的解决,对民事损害赔偿部分则告知当事人向法院起诉,但当事人对法院诉讼的迟延和高昂的成本望而生畏,大多不愿去法院起诉,又重新回到公安机关要求继续调解,而此时公安机关对调解能否成功则无能为力,案件长期积压在公安机关得不到消化,从而引发大量的疑难信访案件甚至可能酿成刑事案件。
(六)治安调解功能的扩张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公安机关破案打击职能的发挥。当前基层公安机关在处理民间纠纷工作中遇到了越来越多的困境。调解工作量逐年增大,民警不仅要进行治安调解,还调处着大量的一般民事纠纷。公安机关“110”报警台的设立,为群众联系民警提供了方便快捷的渠道,加之公安机关调解不收取任何费用,因而一般民事纠纷发生后,群众首先想到的是找公安机关解决。公安机关为此耗费大量的警力,基层派出所有60%以上的警力要用于应付各类民事纠纷,其投入侦查破案、打击违法犯罪的精力有多大是可想而知的,这必然严重影响到刑事打击和治安管理效能。而且调解工作难度大,社会矛盾纠纷的内容和形式日趋复杂,往往涉及到民事的、经济的、行政的等多种法律关系,而多数调解民警由于没有受过严格而系统的培训,缺乏相关法律知识和调解技巧,往往调解效果不佳,使有些纠纷久调难结,警力陷入其中,难以解脱。再则公安机关对一般民事纠纷并无实质的管辖权,调解缺乏法律支持和效力,派出所调解中“一锅烩”的做法也难免有逾越权限,执法不规范之嫌。另一方面,随着大量的民事纠纷涌入公安机关,使得人民调解委员会、基层司法所等民事纠纷调解组织的功能日益弱化,群众有了纠纷不愿找这些组织而愿找公安机关解决,这又必然导致国家有限调解资源的浪费。

 U633687664
U633687664
 U582679646
U5826796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