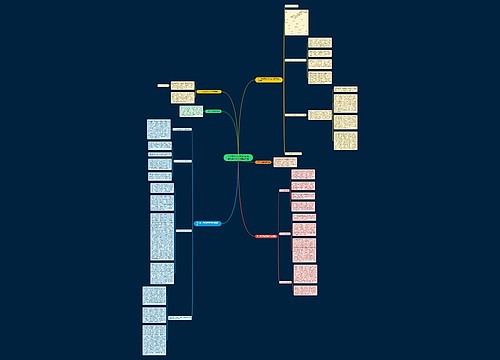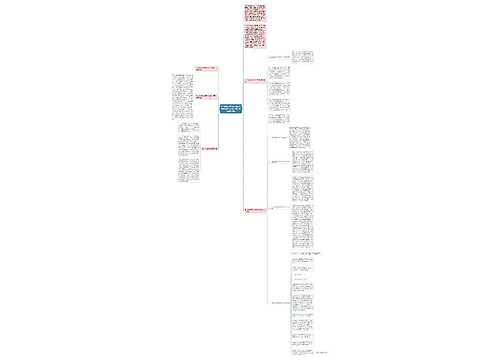近年来,“三农”问题倍受社会广泛关注,其中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我国农村土地纠纷一直呈上升趋势,农民合法权益受到侵犯而引发的冲突、械斗、上访、围攻政府及有关部门的事件也明显增多。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大国,土地与广大农民的生存、就业、发展、保障紧密相连。农民的土地权利如果不能得到有效救济,特别是群体性纠纷不能得到很好的解决,不仅事关广大农民的切身利益,而且事关农村社会的稳定。
从涉农群体性纠纷产生的背景、原因来看,首先,多年来我国农村土地政策不太稳定,几经变化,而土地变动缓慢,因此产生矛盾。例如,我国在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后,曾经推广过“两田制”,即实行口粮田和责任田两种土地使用制度,而在这种制度被国家认定不利于土地的长期利用之后,很多地区却还在积极地继续施行,导致现实与国家政策和法律脱节。2003年新的《土地承包法》颁布,扩大了农民的土地处分权,土地承包最低30年不变。但是因为历史原因形成的土地现状的混乱,良好的法律政策无法实际良性运行。我国法律、政策的多变性,与历史原因形成的农村土地状况混乱,以及我们没有根据国家法律、政策的改变对土地政策及时调整所产生的矛盾,导致农村土地纠纷的大量产生,并且群体性特征明显。
其次,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国家和政府在逐步加大对农业的各项投资建设,涉及农村和农业的政策也逐渐向着农民利益倾斜,农村土地的增值成为必然,然而我国人地矛盾十分突出,因此纠纷产生就有其不可避免的结构性因素。这几年土地承包价格上涨很明显,前几年一亩地承包价格是几十元甚至十几元、几元,现在涨到了每亩300元、500元,土地发包初期没有提出异议或进行荒地开发时没有提出异议,后来经开发土地状况变好或种植的农产品价格上涨,土地承包者获得了较大利益,土地所有者村集体组织成员,因利益驱动导致心理不平衡而产生纠纷。
再次,有些农村基层组织行为不规范,对农民的自主经营权干预过多,时有越权处理农村的具体承包合同,对荒碱地、池塘水库等承包合同的干涉尤为突出,甚至违法行政侵害农民的土地利益。与此同时,基层组织社会控制力在弱化,有些乡村基层组织自律不严,民主法制意识淡薄,对群众的号召力、凝聚力和说服力大大减弱。从调查的情况看,所有土地使用权流转、农地征用、农村集体经济收益分配等纠纷,很多都是由于村基层组织实施的重大决策没有按照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运作,没有召开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大会方式进行民主决议,损害了农民民主权利和财产权利而引起。群众的利益一旦受到损害,在本地区本组织内难以解决或无法解决后,通过法律途径解决已成为人们的普遍性选择。
最后,近年来,随着社会进步和普法工作的开展,农民的自我意识、土地主人翁意识、法律意识明显加强,对土地收益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为了更好的维权,他们往往联合起来,因而形成群体性纠纷。
1.所有权纠纷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9条、第10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下简称《民法通则》)第73条、74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以下简称《物权法》)第46条至52条、58条至60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2条、第8条、第10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2条等明确了我国土地的所有权主体,即土地所有权由国家和集体所有,且做了详细的划分。通过上述立法,我国确立了国家和集体两级土地所有权,但由于长期受土地所有制姓“公”或姓“私”观念影响,“我们无法回避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在法律上有名无实的状况。权利主体虚位,是集体土地所有权弱化的原因与表现。”[1]从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实际运行来看,其“不仅范围较窄,其所有权权能除占有、使用、收益权外,农村集体对土地之处分权受到国家所有权的严格限制,一定程度而言,农村集体所有权仅仅是国家所有权之补充或附庸,其产生并非是国家平均地权的结果,而是国家进行社会控制的一种手段。”[2]于是出现了国家所有权至上,集体所有权受限的尴尬局面。从现有立法结构看,其着重保护者为土地的所有者———国家利益,而非对土地做出投入并使其产生实际效益的利用者即用益权人,致使国家随意以各种行政手段侵害集体土地所有权,农村土地所有权仅具形式而缺乏实际权利内涵。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国家与集体土地所有权权属纠纷、不同集体经济组织间集体土地所有权权属纠纷、“四荒”土地使用权纠纷比较突出。
2.收益分配权纠纷
在农村土地纠纷案件中,争议比较大、问题比较多,也较难处理的是收益分配权纠纷。由于在如何确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等问题上各地认定标准不一,从而导致执法不统一。农村土地纠纷主体与其他民事案件主体相比,其特殊性在于,主体只有取得成员的身份资格后才能享有征地款分配权和土地承包经营权等村民待遇。实践中比较普遍的做法是或以当事人的居住地为依据,或以其户籍为依据,以此认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资格。但其极有可能“两头”否定诸如“外嫁女”、离婚、丧偶女性、大中专在校生、服刑人员等特殊群体的成员资格,以此剥夺他们的收益分配权,造成两头权利都悬空的状况。据我们调查,上述特殊群体由于身份上的不稳定性,致使其收益分配权极易丧失。以大中专学生为例,过去只要其一经录取,其身份即发生变化,毕业后由国家统一分配工作,与所在乡、村存在经济联系的可能性不大。而随着国家取消统分工作和就业形势的严峻,许多毕业生不能保证其在城市工作,相反有相当一部分毕业生待业滞留家中,在未正式参加工作前,其理应享有收益分配权。正是社会对上述特殊群体权利的漠视、法律和政策等原因致使许多人无法享受土地上的诸项权利。于是,以争取收益分配等引发的农村土地纠纷也日渐增多。
4.土地征用纠纷
依据《物权法》第42条的规定,征收集体所有的土地,应当依法足额支付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等费用,安排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费用,保障被征地农民的生活,维护被征地农民的合法权益。征收单位、个人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应当依法给予拆迁补偿,维护被征收人的合法权益;征收个人住宅的,还应当保障被征收人的居住条件。从理论上讲,依契约而成立的承包经营权可以对抗集体的发包权。但实践中比较普遍的做法是:当国家对农业土地进行征收时,发包人可以凭借所有权人的优势干预承包人之自主经营权,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人不能以平等身份与国家达成补偿协议,难以适用物权效力保护自己的权利。[4]结果土地承包经营权人的权利完全由享有所有权优势的集体替代,后者通过自己在农地上的优势和话语权,迎合权力主体的需要,往往以各种手段压低,甚至贪污、挪用、私分、截留、拖欠征收补偿费。安排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费用,保障被征地农民的生活,维护被征地农民的合法权益等法律规定更是难以执行。当权利主体的利益明显受到侵犯或不能满足其利益需求时,因土地征用费引起的纠纷自然成为农村土地纠纷之一种,且在实践中比较常见。同样,城市与农村土地征用补偿问题也很突出。一方面,同样的土地和房屋在土地征用补偿中此地与彼地的差距太大;另一方面,征用农牧民土地后的社会保障机制滞后。尽管《物权法》有明确规定,但社会保障理论、意识还很滞后,需要从根本上予以解决。

 U633687664
U633687664
 U582679646
U5826796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