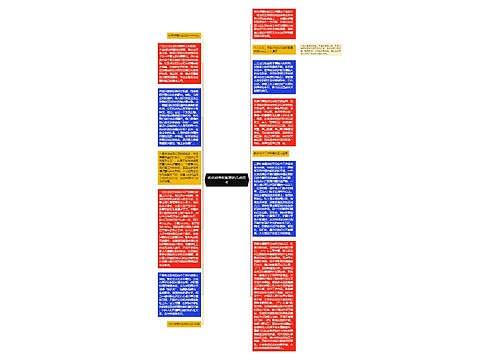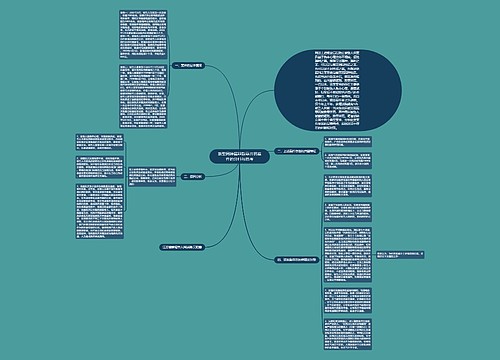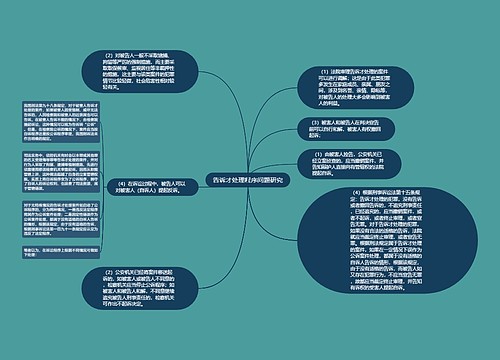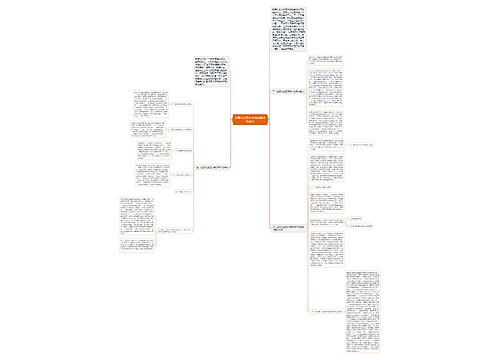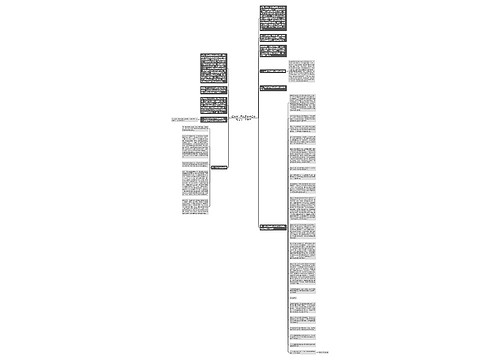事实上,从司法改革的层面来看,制度本身的公正性才是建设公正的司法制度的本源问题,不解决好这个本源性的问题,公正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就会成为镜中花、水中月。没有制度公正,遑论政策上的公正、实践中的公正。建设公正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最为根本也是最为关键的还是制度本身的公正性;而制度本身的公正性,则在于制度的设计是否符合社会大众对公正的期许,制度的正当性是否得到了全社会最广泛的认同。这就要求新阶段的司法改革仍要对我们的各项法律制度——无论是实体法还是程序法——继续前阶段司法改革最常使用的“修法”措施,保证制度的“与时俱进”以维护其公正性。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坚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1](P31)“科学”、“民主”的立法,就是为了保障法律制度的公正性、正当性,建立公正、科学、合理、符合司法规律的制度体系。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由于中国社会的变动频繁且剧烈,本来就常被推崇习惯法的学者们所诟病的成文法的滞后性被无限地放大,司法制度不合理、不能与时俱进,使得一些制度未能体现出公正的价值。在此种制度框架下,无论之后的政策如何调整,实践运行中如何规范,都无法真正顺畅地实现法律制度对公正价值的追求。特别是随着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发展,法律思想层面发生的巨大变化并未在法律制度中得以及时充分地展现。当社会中广大民众对制度公正的期许逐渐与现有的制度构建发生偏离时,人们对现有法律制度的“接受、认同、信赖和支持”必然也会开始逐渐弱化,对制度的公正性产生质疑。因此,新一阶段的司法改革仍需通过不断的修法、立法、完善整个法律制度,以先进的法律思想推动制度的变革,维护法律制度的公正性,以达到正本清源的目的,从根本上为公正的实现打下坚实的基础。
当下,从制度层面建构公正的司法制度、确保制度公正的核心问题,在于如何将人权保障的理念融合到制度建构当中,使已获得宪法确认的“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在司法制度中得以体现。应当说,在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的第一阶段的司法改革中,人权理念得到了初步的确立,但在司法制度的建构上,并未能形成科学、系统的体系。随着人权理念逐步深入人心、逐步成为社会大众的集体共识,司法制度能否体现并有效地保障人权已成为衡量其是否公正的重要标准。司法制度能否被社会大众所接受、认同、信赖和支持,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制度建构能否有效地保障人权。因此,如何在新一阶段的司法改革中完善司法制度,构建一个充分体现人权保障理念的制度体系,就成为建设公正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关键。
新出台的《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09—2010年)》就体现了这样一种制度建构的方向。该计划明确了“未来两年中国政府在促进和保护人权方面的工作目标和具体措施”。[2]在与司法制度改革相关的第二部分“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保障”中,该计划明确提出要“完善预防和救济措施……依法保障人身权利”、“完善监管立法,采取有效措施,保障被羁押者的权利与人道待遇”[3],并随之提出了一系列的具体措施。这些措施将帮助我们建立起一套完善的、科学的、蕴涵了人权保障理念的司法制度,使制度本身能够获得接受、认同、信赖和支持,在制度建构的层面为建设公正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打下坚实的基础。
司法制度——政策高效提高诉讼效率一直是司法改革的重要目标之一,效率一度被提高到与公正同样的高度进行讨论,成为司法制度改革中不可或缺的推动力之一。在前一阶段的改革中,提高诉讼效率成为改革的重点,在1996年的《刑事诉讼法》修改过程中,确定证据不足作无罪处理的规则、增设简易审判程序、取消收容审查、规定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期限等几项改革措施,都是围绕或者涉及司法效率问题而展开的;在民事、行政司法制度中,更是通过完善民事、行政诉讼简易程序,制定简易程序审理规则,建立健全多元纠纷解决机制,有效地提高了人民法院的司法能力,缩小了其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司法需求之间的差距。
不难发现,在前一阶段的改革过程中,提高诉讼效率的目标是通过修改、补充、完善现有法律制度来实现的。我们可以将之前的提高诉讼效率的方式视为一种追求“制度高效”的方式:通过司法制度本身的调整,尽可能地缩减各类案件在司法程序中对有限的司法资源的消耗,以期容纳更多诉讼案件。应当说,这种制度高效的路径选择在前一阶段的改革中,确实起到了一定的节约司法资源、提高诉讼效率的作用,有效地缩减了一些不必要的诉讼程序,使得整个司法制度更加经济、高效,有效地缓解了整个司法体系所承担的案件压力。
然而,在笔者看来,在新一阶段的司法改革中,若仍仅以制度高效为改革的唯一路径,是难以达成建设高效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改革目标的。
一方面,随着第一阶段司法改革的完成,各种节约司法资源、提高诉讼效率的制度已逐步建立,通过制度本身的进一步调整所能带来的司法效率的提升空间已十分有限。在司法制度改革中,涉及效率的制度改革并非完全遵循经济原则,完全以节约资源、提高效率为目标,而是要受到公正原则的限制,即制度高效必须建立在制度公正的基础之上,不能一味地追求高效而贬损制度的公正性。如辩诉交易制度虽然在理论上能够极大地提高诉讼效率,但由于其在正当性上难以获得社会大众的广泛认同,对制度的公正性会带来极大的损害,因而在当下的中国无法建立起来。因此,在社会大众对司法制度的公正性的认识未发生较大变化的情况下,司法制度在完成初次的制度高效的调整后,通过同样的方式所能提高的诉讼效率就十分有限了。对于我国的司法体制改革而言,虽然仍有许多有助于提高诉讼效率且无损于公正的制度尚未建立起来,但相对于整个司法制度,这些制度上的小修小补并不能真正大幅度地提高诉讼效率。
政策高效最为典型的表现是“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的提出。坚持宽严相济的司法政策被认为“是我国刑事审判工作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符合司法规律和特点”。政策的制定“以增强群众安全感、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为出发点”。[6]同时对于检察机关而言,“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就是要根据社会治安形势和犯罪分子的不同情况,在依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能中实行区别对待……对严重犯罪依法从严打击,对轻微犯罪依法从宽处理……全面把握、区别对待、严格依法、注重效果”。[7]不难发现,社会效果是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所着力追求的目标。依靠政策的灵活性,通过不断地调整司法工作的重心,达到宽与严的动态平衡,将司法资源合理地配置到司法程序当中,以获取更多、更好的社会效益是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的根本目的。因此,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可以被视为我们追求政策高效的一项原则性规定,在此原则性规定的指导下,“根据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犯罪与社会治安的形势,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依法予以从宽或者从严处理”。[8]通过更为具体的刑事司法政策,及时地调整司法资源在不同案件类型中的分配,可以达到优化资源配置的目的。
在当前的社会形势下,我们所采取的刑事司法政策就是坚定不移地贯彻宽严相济的形势政策,依法严厉打击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和严重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等犯罪,依法严肃查处贪污贿赂、渎职侵权等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坚决遏制刑事犯罪高发势头。同时,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依法从宽处理,对因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轻微刑事案件依法从宽处理,对轻微犯罪中的初犯、偶犯依法从宽处理。[9]围绕构建和谐社会理念推行刑事和解的政策,以平和的方式解决诉讼纠纷,在诉讼的任何环节都创造案结事了的可能性,并最大限度地节约诉讼资源,减少涉诉信访上访。从过去重视审判效率转向重视审判前的诉讼效率,有所侧重地对有限的司法资源进行科学、合理的分配。这种资源分配的司法政策,将随着社会形势、犯罪控制形势的变化而变化,从而使司法资源得到更为有效的配置,提高整个司法体系所获取的社会效益,在政策调整层面为建设高效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提供保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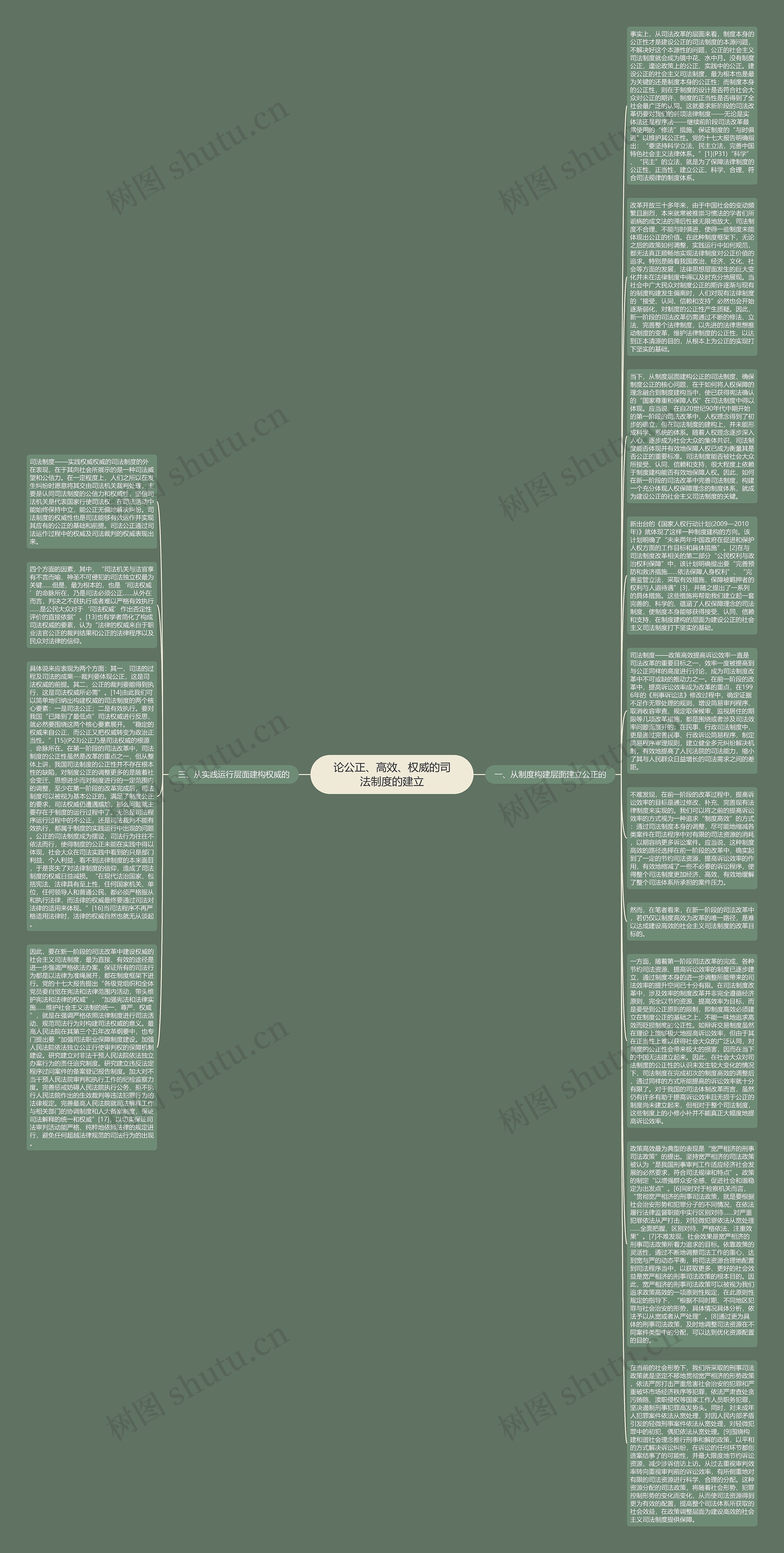
 U633687664
U633687664
 U582679646
U5826796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