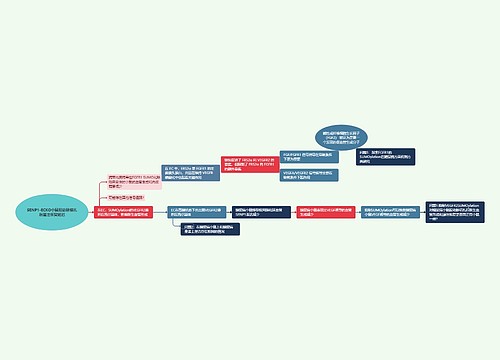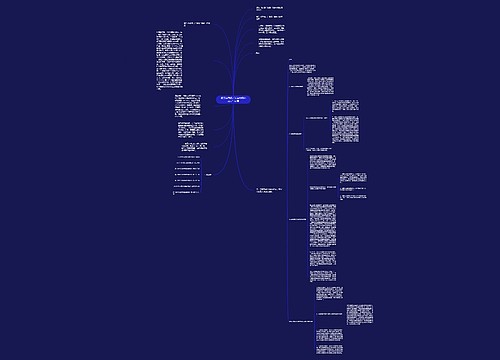经过审理,法院查明,电视大学在寄发通知书时,所写的邮政编码为张某联系人涟水县某中学的,而邮寄的地址为张某的家庭地址。邮政编码与地址不符。淮阴邮政局在分发信件时,又将信件误分到涟水方渡邮包内,致使信件邮寄耗费了10天时间。法院据此判决淮阴市电大和淮阴市邮政局对录取通知书的延迟送达负有直接责任。
现在的问题是,邮政局应当承担多大的责任?作为本案被告的邮政局认为,我国有《邮政法》,也有《民法通则》。《邮政法》是《民法通则》的特别法,根据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原则,本案的审理与判决应当适用《邮政法》的规定。而《邮政法》又规定,对平常邮件的损失,邮政企业不负赔偿责任。所以,邮政局对张某的录取通知书延迟送达不应当承担责任。
专家说:《邮政法》属于行政法,它不能排除民事责任。
有法律专家认为,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原则仅在同种性质的法律规范之间才有意义。也就是说,民法规范与民法规范之间发生规范竞合时,才会有所谓的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原则适用,民法与行政法之间,民法与刑法之间绝对不发生所谓的竞合问题。如果一个行为既符合民法关于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又符合行政法关于行政违法行为的规定,甚至符合刑法关于犯罪的规定时,适用民法规范追究行为人的民事责任并不妨碍适用行政法追究行为人的行政责任或适用刑法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因为民法规范、行政法规范和刑法规范之间不发生竞合的问题,本案中所涉及的邮政法属于行政法,所以邮政法与民法不发生竞合。
尽管法院与学者的结论都是适用《民法通则》而不适用《邮政法》,但是其逻辑依据却明显地不同。一个是从法的效力层次上看问题,一个是从法的部门性质上来判断。那么哪一个推理更为准确呢?
我们认为,无论是学者的逻辑推理还是法院的判决理由都有可供商榷之处。
学者将《邮政法》视为行政法而将《民法通则》看成是民法,从而得出两者不发生竞合的结论,在逻辑上不能成立。因为《邮政法》作为一个法律文件不仅仅包含行政法规范,它还包含有民事规范的内容。具体到本案而言,关于邮件延迟送达的赔偿责任就是民事赔偿的内容。不能在论述问题时将法律文件与法律规范混淆在一起。规范平等主体之间行为的法律规范都应当是民事法律规范,不管它出现在《民法通则》中还是《邮政法》中。邮政企业在为顾客提供邮递服务时,产生了邮递服务关系,在这一法律关系中,彼此的地位是平等的。他们之间的关系应当遵循民事法律规范的要求。
法院的判决理由虽然解决了法律适用的冲突问题,但缺乏根据。从法律效力的层次上来说,宪法高于法律是没有疑问的。法律的效力高于行政法规也是没有疑问的。但同样是国家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为什么《民法通则》效力高于《邮政法》的效力?从立法机关来看,《民法通则》与《邮政法》是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如果最高立法机关所制定的法律再分出效力的高与低,在立法理论上是无法解释的。
在法律适用上,《民法通则》是关于民事损害赔偿的一般规定,而《邮政法》中关于延迟送达的损害赔偿是关于损害赔偿的特别规定,按照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原则,在延迟送达的损害赔偿方面当然应当优先适用《邮政法》的规定。
问题就在于,《邮政法》规定,延迟送达邮政企业不承担责任。这一规定本身有问题。为什么当事人一方不按时履行自己的义务可以免除责任?合同主体的权利与义务如何实现平衡?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如何得到维护?所有这些,都没有体现。
我们从邮政法的法律适用论及我国的立法体制问题,看似离题甚远,实际上是想找出造成我国法律冲突的根本原因。我们的结论是:作为特别法的《邮政法》应当得到尊重。法院应当适用《邮政法》的规定处理类似的案件。但是《邮政法》的规定又明显地违背了公平的原则,背离了保护消费者权益的精神,所以必须修改。
我们的意见或许是被动的、消极的和无奈的,但又是法治精神所要求的。法院的判决虽然求得一个公平的结果,但在法律上站不住也是不行的。

 U277740458
U277740458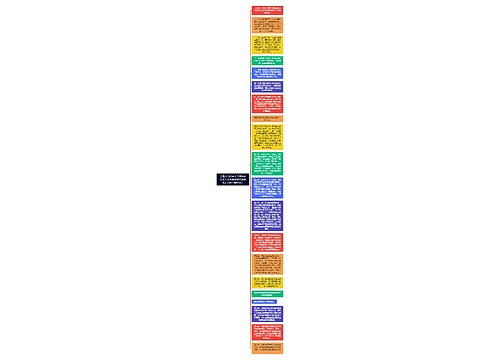
 U561649057
U5616490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