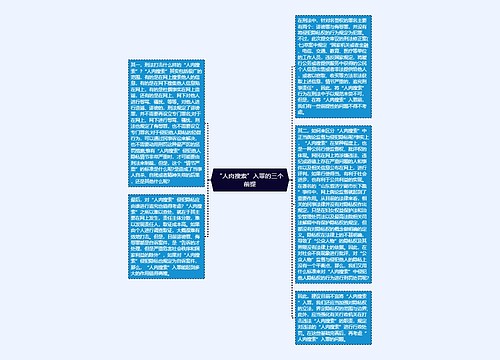笔者认为,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和刑事违法性是犯罪的基本特征,判断一个行为是否属于犯罪更离不开这两个条件,脱离它们谈犯罪是没有意义的。
首先,社会危害性大小是判断犯罪与否的根本标准。在大家对婚内强行性行为究竟是否属于犯罪讨论得如火如荼的时候,似乎人们都忘记了犯罪的本质特征,即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在现代的文明社会,在任何情况下,违背妇女的本意而强行与之发生性关系都应该受到道德上的否定评价,都应该受到社会的谴责,这一点是不应该存有争议的。然而,在道德上应该受到否定评价、在道义上受到谴责的行为并非都适宜上升为“犯罪”,例如随地吐痰、乱说脏话等等。犯罪有着自己的特征,其中,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是重中之重。强迫妻子与自己发生性关系与强奸其她妇女是否具有同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呢?这是决定这一行为是否属于犯罪的决定性因素。
有学者认为,我国刑法在规定强奸罪的时候并未将丈夫排除在外,即丈夫并不因自己的侵害对象具有特殊性(即是自己的妻子)而不能成为犯罪主体。然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解释,盗窃或抢劫自已家的财物或者近亲属的财物,一般可不按犯罪处理。因为那些人不会在社会上随机选择家庭成员以外的人作为自己的行动目标,这就决定了他们的行为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只局限在自己的亲人范围内,由此也就决定了他们的行为具有较小的社会危害性,他们本人的人身危险性也要远远小于其他实施盗窃或抢劫的人。
由此,我们得出结论,犯罪对象的不同会影响到该行为的定性,即是否属于犯罪。那些只是强迫妻子与自己发生性关系的人,无论是其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还是人身危险性都不可能与“强奸犯”相提并论,因此,一般情况下不宜定为犯罪。
不考虑社会危害性的大小,只是谈论作为女人有拒绝性行为的权利或是作为妻子有发生性行为的义务,都只能作为对婚内强行性行为做否定或是肯定评价的论据,而不能决定该行为是否属于犯罪。单纯的强调权利或者义务,都会使我们陷入迷乱,不能正确认识犯罪及其本质,不能使自己的观点立的稳固,也不能将对立观点驳的彻底,这就好象争论斑马究竟是黑斑白马还是白斑黑马一样,很难令人心悦诚服。
其次,从刑事违法性看婚内强行性行为。刑事违法性,是指犯罪行为违反了刑法条文中包含的刑法规范。[5]
强奸罪,是指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违背妇女意志,强行与妇女发生性交或者以各种手段与幼女发生性交的行为。其中,“意志”是一个涉及了立场、信念的概念,被强奸的妇女在心理上是绝对排斥与强奸者发生性关系的,强奸者与被强奸者在立场上是绝对对立的。绝对的排斥与一时的不情愿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境界。妻子对于丈夫发生性关系的要求不应该是绝对排斥的,通常仅是一时的不愿意或没心情,也就是说,丈夫违背的不是妻子的“意志”,而是“意愿”。妻子只是不“愿意”在当时当刻与自己的丈夫发生性关系,这还未上升到涉及立场、信念的层次。引入这个概念之后,我们就可以很容易的判断某些特殊的婚内强行性行为是否属于犯罪。对于王卫明强奸其妻案,他们的事实婚姻已经结束(双方长期分居并且一审法院已判离婚),而法律婚姻尚存(一审判决尚未生效),在这种情况下,女方事实上已对男方发生性关系的要求持绝对排斥的心理态度,而不同于一般的夫妻吵架后的“不愿意”,男方也在明知事实婚姻已经结束的情况下强行与其妻发生性关系,其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明显提高,因此,应当将其行为定为犯罪。
至于有学者认为婚内“有强无奸”,我认为值得商榷。其中,“强”顾名思义即为以暴力强行为之,而“奸”的解释是“不正当的性行为”[6].在妇女地位日益提高的今天,“正当的性行为”不应该按照传统的观念仅仅理解为有婚姻的“允许”,它应该是两情相悦的,是双方都同意的。因此,婚内是可能出现强奸行为的,只是这种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还没有达到需要刑法对之加以干预的地步,这种行为应该得到社会的否定评价。
再次,程序上不具有可操作性。将婚内强奸规定为犯罪,不仅在理论上难以自圆其说,而且在程序上也不具有可操作性。进行性行为通常是只有夫妻双方在场,不会有其他见证人,因此,若将婚内强奸规定为犯罪,在取证上存在着巨大的困难,而取证过程本身,又不可避免的会造成对他人隐私权的侵害。

 U633687664
U633687664
 U678146910
U678146910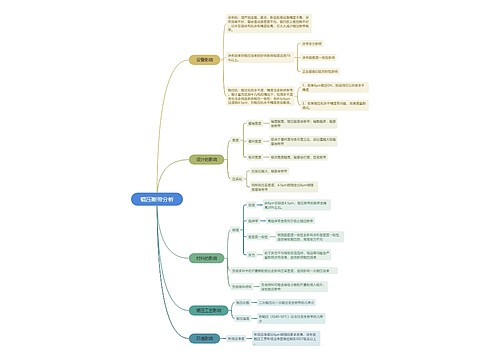








![[摘要]:家庭暴力,特别是针对妇女的暴力,自古以来不论地域 [摘要]:家庭暴力,特别是针对妇女的暴力,自古以来不论地域](https://pic.shutu.cn/shutu/static/2023/03/05/f92b6c/f92b6ce292c81f5c2d6e8ecb3abf4cf1.jpeg!w500?v=370577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