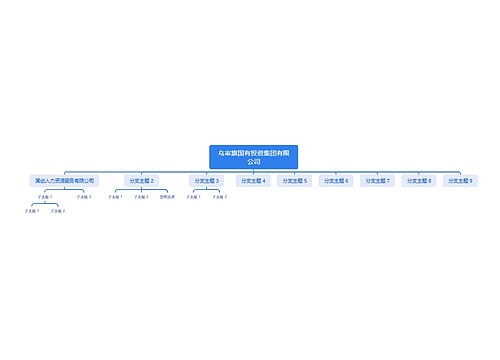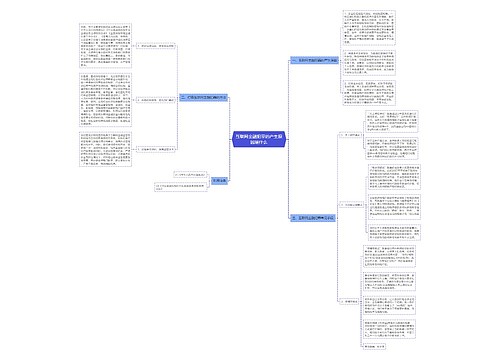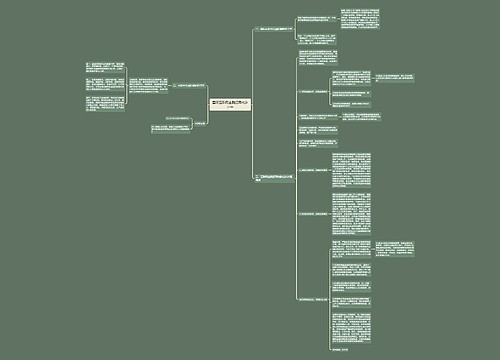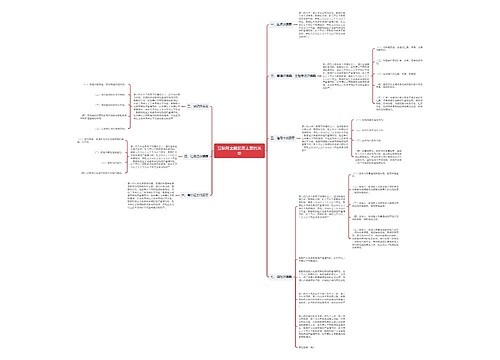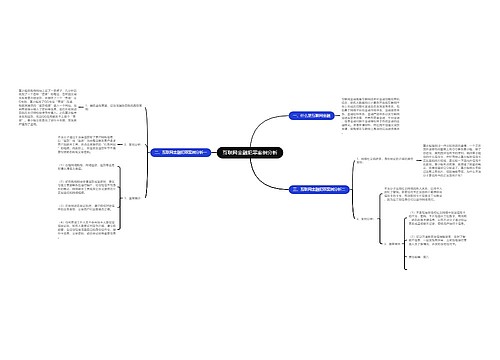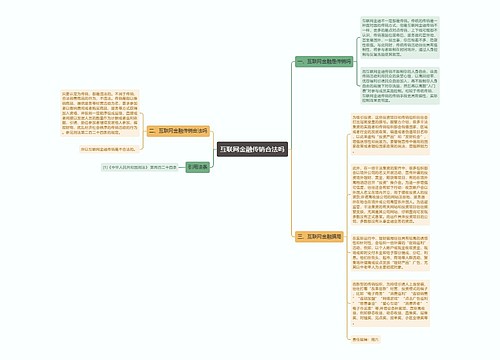一是加强对互联网金融的规制。检讨互联网金融犯罪在一段时间里高发的成因,能够明显看出对互联网金融进行强规制的必要性。比如,从“P2P”网络平台的异化过程,就能够看到这种必要性。前两年一度乱象丛生的“校园贷”,也存在规制不力的问题。诚然,与传统金融行业相比,互联网金融有其特殊之处,但这种新型金融产业仍具有金融企业的基本性质,因而应当对互联网金融企业给予和传统金融产业相同的监管。互联网具有“放大”功能,即任何活动及其影响,无论利弊,都可能被快速放大,因而互联网在为金融企业提供便利的放大功能同时,也会同时为这些企业带来风险的放大效果。从这个角度讲,对互联网金融进行强规制意义更为重要。当然,“强”规制并不意味着限制、束缚,而是要围绕风险防控进行全方位的制度规范,而政府主管部门不仅要提高对互联网金融风险的认知,更要努力“开发”新型的监管工具和措施。从某种意义上说,应当考虑以互联网之“道”来降服互联网之“魔”,这个“道”就是要形成适应互联网规律的监管体制。一想到“规制”,就采取“堵”“压”“封”的方式,是不符合互联网规律的。同时,互联网金融相关企业应当在刑事合规方面加强自身建设,即充分了解从事互联网金融可能带来的犯罪风险和刑事法律风险,并将其作为内部合规管理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
二是有关互联网金融犯罪的刑事法律应当继续完善。客观地讲,我国现行刑事法律还存在不适应互联网金融快速发展的“短板”。在刑事实体法方面,对于现行金融犯罪(刑法典分则第三章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和金融诈骗罪)中的一些规定,有必要考虑,应否结合网络空间的变化进行调整,或者增设新的犯罪类型。现在有的网络平台提供高利贷业务,这本身就是为法律所不容许的,对于从事高利贷业务、情节恶劣的行为就应考虑予以犯罪化。例如,猖獗一时的“裸条贷”行为,就应该考虑予以犯罪化,仅仅以敲诈勒索罪处理,不能评价这种高利贷行为的危害性。比较而言,在刑事程序和证据法方面,更应当考虑如何适应互联网金融犯罪的“涉众性”问题。例如,对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类案件,应当考虑采取刑事、民事程序相对分离的方式解决,这样更有利于化解由此引发的社会矛盾。在证据法方面,对于包括互联网金融犯罪在内的所有网络犯罪认定,应当考虑调整事实认定思维和证据规则,换言之,不宜固守线下犯罪的证据规则,应当根据互联网行为的特点进行因应性的调整。
三是关注隐性的互联网金融犯罪问题。网络“非吸”类刑事案件属于显性的,相对容易被发现,司法机关认定事实也比较容易,对于隐性的互联网金融犯罪,则不仅不易发现,而且即便进入司法程序,也会出现定罪难的问题。最典型的隐性互联网金融犯罪就是洗钱罪。可以说,利用互联网平台、网络工具进行洗钱,是常见多发的互联网金融犯罪,但在司法实践中,实际进入司法程序的案件却极少。例如,利用特定数字货币进行洗钱就是典型的例子,而以这种方式进行洗钱比以往洗钱方式更为巧妙,而且很难查处痕迹。所以说,对于这种隐性的互联网金融犯罪,政府有关职能部门应加大与公安部门、金融机构的合作,同时也要加强该领域的国际合作和区际合作,要在能发现、能控制、能追踪、能锁定、能追回方面下功夫。当然,这个任务肯定是刑事法制中最难的一部分,但如果考虑到这种犯罪的现实危害性,下功夫破解这个难题,应当被看作是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
四是建立互联网金融犯罪的预警机制。以目前的网络技术手段而言,发现并及时制止互联网金融犯罪并非难事,但迄今为止,全国范围内尚没有建立起统一的互联网金融犯罪的预警机制。建立这一机制,主要应考虑四个问题:谁来建立?谁来管?如何管?如何协调不同机构?从目前管理体制看,有必要整合公安部门、金融主管部门和互联网管理部门的力量,合力构建这一机制。对于显性的互联网金融犯罪而言,这种机制的建立,可以及时发现犯罪线索,并防止犯罪危害的扩大和蔓延;对于隐性的互联网金融犯罪而言,建立这一机制则更为重要,因为这一机制可以同时充当证据收集和固定的机制。当然,这一机制的建立,离开相关互联网企业也难以运转。目前一些提供即时通讯服务、网络社交平台、网络搜索服务的互联网公司拥有天量的数据,从实践看,互联网金融犯罪也是通过这些平台、利用这些工具来实施的。所以,在建立预警机制方面,就需要互联网企业的大力支持,当然,互联网企业也负有参与社会治理的功能和职责。值得注意的是,建立这类预警机制应当依循法治原则,不能因此不当干涉公民的通讯自由以及其他受宪法所保护的权利。

 U482242448
U482242448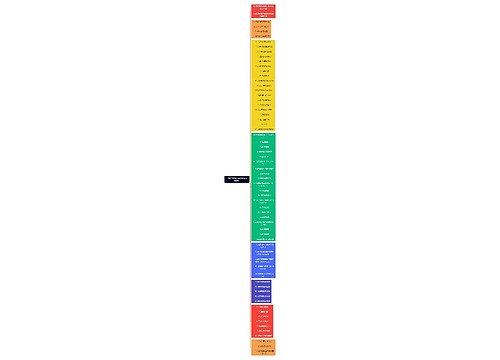
 U682198976
U6821989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