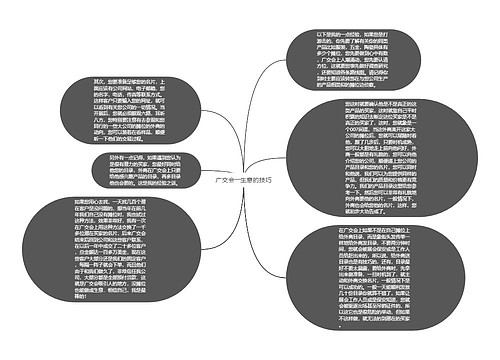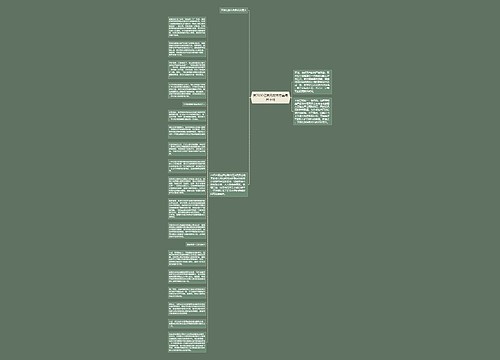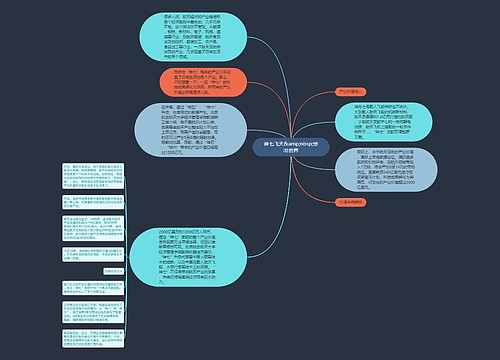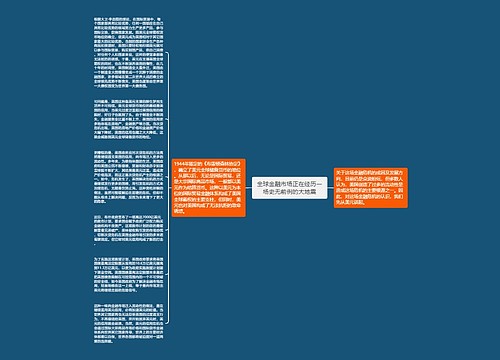夏业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公共政策研究所副所长)
-改革开放初,我们党讲农民对土地的承包三十年不变,三十年的期限即将到来,怎么办?这一问题不仅农民很关心,也涉及到中国农村改革发展方向。
-农民在自己的土地上不仅可以种粮食,还可以“种”工厂,“种”城市。
-决策层应该考虑到改革的动力正在衰减,要想推动改革的车轮继续前进,需要新的动力,而新的动力不是空想的,而是看国民最需要什么。
辛鸣:改革开放初,我们党讲农民对土地的承包三十年不变,三十年的期限即将到来,怎么办?这一问题不仅农民很关心,也涉及到中国农村改革发展方向。胡锦涛总书记前一段时间在安徽考察,其实已经指出,“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党的农村政策的基石,不仅现有土地承包关系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还要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这次全会将对此进一步明确。那么不变究竟有多长,五十年还是七十年,还是更长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讲的一百年,这都是政治意义的说法,我们政策的目标是给农民一个定心丸,“长期”二字足矣。
农民对土地的经营承包权得到保障之后,紧接着就是农民能用土地做什么。三十年前,我们给了农民在自己土地上种粮食的自主权,种什么粮食农民说了算,国家不管,这一举措既解决了国家粮食增收的问题,又解决了农民增收的问题。三十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土地越来越成为稀缺的要素,土地功能也越来越拓展,不仅可以种粮食,还是发展工业、进行城市化的重要支持,而这都是财富增值的巨大空间。过去农民一直未能参与进来分享成果。今后,只要在国家规划范围内,符合法律法规,农民在自己的土地上不仅可以种粮食,还可以“种”工厂,“种”城市,使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徐小青:中央的政策目标这三十年来越来越明确,就是要长期稳定农民和土地的关系,从过去的承包期15年,到30年,到现在非常明确的指出长久不变。至于是否会延长到70年,这个文件不一定能讲出来,但是提出长久不变是没有问题的,这是已经决定的事情。
接下来就是土地流转问题,实际上从1993年开始,在土地问题上中央是鼓励流转的,不过1990年代中期之后,一些大型企业长期包租农民的土地,也产生了一些问题。
农民家庭承包的土地还是比较稳定的,流转的幅度不大,就我们前几个月去调查的情况,传统的农业大省,农民自愿流转的比例也就十分之一,农民虽然进城打工但是不愿意放弃自己的土地。现在有一些流转比较多的是沿海地区,江苏,浙江,广东,流转的比列高一点,但是大体上也基本固定下来了。
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探索建立土地经营权的流转市场,总书记这次在小岗村的讲话也明确提出来了。要促进土地的流转,发展适度的规模经营,这是随着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和农业产业化发展的需要把土地逐渐有条件的集中。
于建嵘:现行的农村土地政策中,“集体”是所有者,但法律并未明确它的构成要素和运行原则,作为个体的农民与“集体”的利益关系也不明确。
而在现实中,“集体”往往只是有限的所有权人,国家才是农村土地的终极所有者——它垄断了土地的一级市场,所有土地转让往往先由国家低价征用变为国有,再按市场价出售,而农民则被排斥在土地增值收益分配的体系之外。农民既不能决定土地卖与不卖,也不能与买方平等谈判价格,而国家和强势集团则可以不受约束地占有农民的土地权益,而造成大量的农民沦为无地、无业和无社会保障的“三无”人员。
对农民而言,土地不应仅仅是一种生产资料,而应真正成为他们的财产。一方面,这有利于土地相对集中,实现规模化经营,另一方面,从土地转让中获得财产性收入,可促进农民向城市流动。
这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还是一个农民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问题。如果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就不可能真正解决中国的农民问题。
夏业良:“三农问题”的核心突破点就是土地问题,无恒产者无恒心,目前农民无法对土地做长久的投资和利用。土地作为资产要带有广泛的传导意义,如果这个要素放开了,它会影响到多个流通领域。如果土地市场具有真正的个人私有产权,买卖自由的话,它能盘活资产,使得交易量提高,使得单位面积的价值成倍的增长。比如一亩土地放三十年不动,它的市场价值肯定不高,而相反流通次数越高价值就越大。
于建嵘:农地改革的底线,可参照林权改革,由于农村土地关系到13亿人温饱问题,其改革必然要更加谨慎,它的安全线,肯定在林地改革的范围内,不可能超出。一是不太可能突破土地的集体所有制,只是允许某些非农用地实现流转,从操作上解决抵押、继承、转让的功能,进而实现农民对土地的财产权利。
第二条不太可能突破的是土地二级市场制度,也就是说,国家征地这个环节仍然必不可少,目前的分税制,使得一些地方政府财政严重依靠土地出让,这在短时间内难以改变,也不是地方政府可以改变的。但是,在征用的细节上,应该进行相应的改革。
辛鸣:农村改革的一个根本问题,就是打破统筹城乡发展,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体化新格局。统筹城乡的工作其实一直在做,之前中央也布置了很多试点,比如在重庆和成都启动“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又比如,此前很多地方已经开始放开户籍制度,还有,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问题,要进一步发展农村的公共事业,包括教育、文化、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由于目前农村的现状和形成一体化新格局的需要,今后国家财政应该会进一步向农村倾斜,当然采取什么样的办法保证倾斜还需要进一步的探索。
于建嵘:短时间内,改变中国户籍制度不现实,意义也不大,最重要的是附着在户口背后的各种权利,如何与城市居民实现对等。在市场经济中,应当对处于弱势的农民进行保护,这是一种制度性的保护,在财政安排上和社会保障方面予以倾斜,更重要的是,要让农民有利益表达和自我维护的能力。
周天勇:对于经济形势的判断和宏观调控政策的制定,一般是在每年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但毫无疑问,作为当下最重要的问题,即中国与全球的宏观经济形势,将会进入三中全会的视野。
同时,农业经济在中国经济中仍起基础性作用,农产品价格是基础性价格,是稳定物价水平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叶笃初:虽然没有说有新的议程出现,但是对现在的经济形势,在党内要有基本的认识和判断,这在各级官员中是非常急切的,最近官媒在这方面的声音都是逐渐的加强,我相信这次三中全会会适应这个变化和党内外的期待做出反应。
夏业良:中国经济目前整体上来讲,实体经济是向好的,前景是好的,前半年通货膨胀比较严重,下半年采取比较有力的措施以后,水平明显地下降了。现在担心的是经济增长速度下滑较快,因为要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确保消费能力以及就业能力。虚拟经济即股市潜伏着危机,如果解决得好可以消除隐患。
农村问题其实影响到房地产问题,最近几年一方面房价涨得很厉害,一方面土地供给又存在很多问题。中国房地产市场跟其他国家的特殊性在于有土地的制约,以及拥有房产的时间很短,从1995年起私人才能拥有房产,短短的13年,所以需求很旺盛,而供给很有限,国家支配土地,从而产生了供给矛盾,房屋供给矛盾根源于土地供求矛盾。
目前三中全会背景下对中国经济有个较为清晰的判断是,虽然有外部经济的影响和压力,但是我们本身还没有到一个糟糕的状态,目前经济还是良性的,最近两年内中国经济自身不会有问题,有些小的问题需要调整,但是基本面是好的。而最大的压力是来自进一步发展的压力,通货膨胀的压力和通货紧缩的压力其实都是有的,以及就业的压力,但是这些都是长期的矛盾。
这次三中全会,如果政府在一批人的要求下出台一些类似于救市的措施,我觉得这样做可能是错误的,我是反对救房地产市场这类说法的。房地产不是靠救市的措施,而是靠解决生产要素全面流通的问题,这才是根本出路,而且从根本上也解决了“三农问题”。
辛鸣:全球范围的粮食危机给中国敲响了警钟。而且这一段时间来中国在国际市场采购铁矿石和原油的教训告诉我们,不能指望将来靠国际市场来养活中国人。但是低水平的、传统农业生产模式已经很难使得农村经济大发展,加之我们的耕地客观在减少。如何在耕地面积减少的情况下保证粮食的增产,这次十七届三中全会将会重点推动发展现代农业,通过发展现代农业,保证粮食安全。
夏业良:前三十年改革是政府推动的,政府顺应了民意,但是今后三十年改革的主题应该体现为公民社会的成长和壮大,由公民社会主导改革。
我们期望三中全会出台一些影响中国未来几十年的重大政策,决策层应该考虑到改革的动力正在衰减,要想推动改革的车轮继续前进,需要新的动力,而新的动力不是空想的,而是看国民最需要什么,需要什么放开就是最英明的决策。

 U682687144
U682687144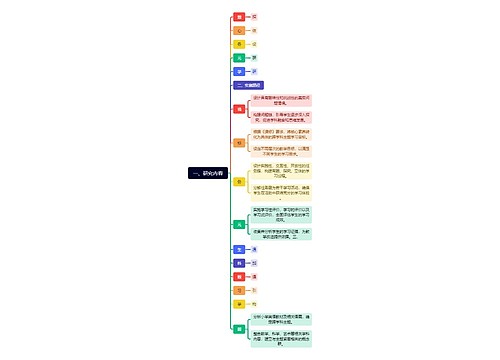
 U633687664
U6336876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