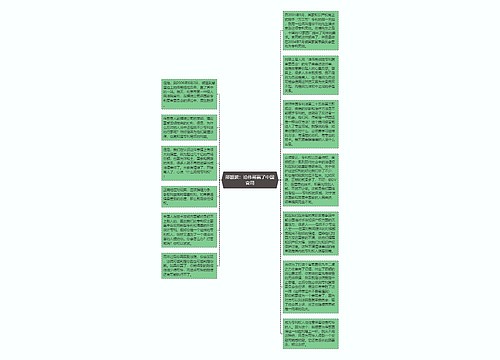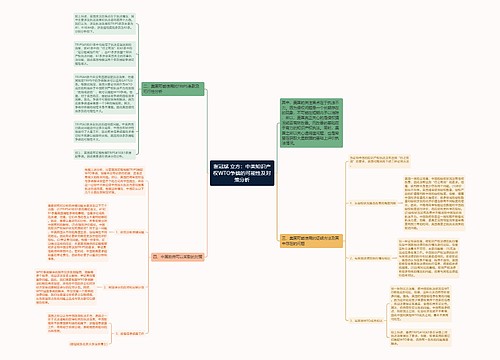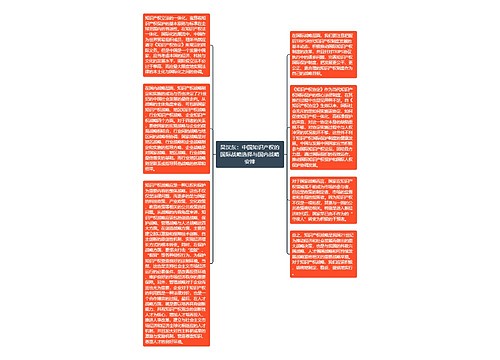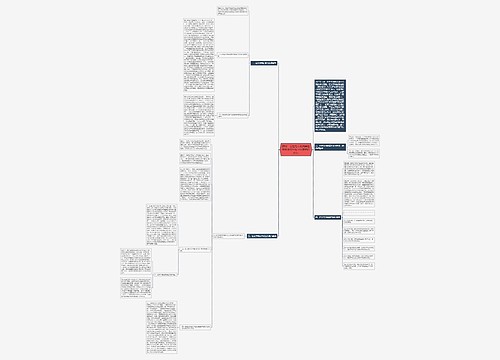这是传统理论中有关知识产权客体的通说。持该观点的学者将关于精神财富所享有的权利称之为“智力成果权”,因而相应将这种权利客体归结为“智力成果”,并且强调其价值不能用货币衡量。应该指出,关于智力成果的传统说法,偏重于这类客体的精神属性,而未能突出其商品属性和财产价值,因此未能反映出知识产权客体的本质特征。
持此观点的学者认为,“知识产权的对象”和“知识产权的客体”是两个不同概念。“有关智力成果和工商业标记”只是“知识产权的对象”,而“知识产权的客体,即知识产权法律关系的客体”,“绝不是智力成果或工商业标记本身,而是依法对智力成果或工商业标记进行控制、利用和支配之行为。
这种观点似乎在力图改革传统法理的客体理论,即认为权利客体不是权利义务所指向的共同对象,而是对共同对象的控制、利用、支配行为。依这种观点的逻辑,我们可以推出在民法领域财产法的客体,也不再是“物”,而是所有人对物的支配行为、转让行为、继承行为等等。这种观点的错误在于它混淆了“权利的实现方式”与“权利客体”。事实上,这种控制、利用和支配行为正是权利内容的实现方式。
持此观点的学者认为,知识产权的客体是指基于对知识产权对象的控制、利用和支配行为而产生的利益关系或社会关系。这种观点混淆了法律关系的客体(也即权利客体)与法律所调整的社会关系的客体。说法律关系的客体是社会关系,等于说社会关系的客体是社会关系,这无论是从哲学意义上的客体来理解,还是从法律意义上的客体来理解,都是难以成立的。
持此观点的学者认为,知识产权的客体是信息。这种观点是把问题处理得过于简单化。仅“知识产权的客体就是信息”这个论断本身也是值得质疑的。因为我们可以说,知识产权的客体含有大量的信息,而不能说知识产权的客体本身就是信息。这正如日月星辰、江河湖海、花鸟虫鱼都含有信息,但并非他们本身就是信息一样。
持此观点的学者认为,知识产权的客体是无形财产。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知识产权尚未成为国际上广泛使用的法律概念,人们一般将基于创造性智力成果所获取的民事权利称为“无形财产权”(intangible property),因此许多学者将其客体视为“无形财产”。但是,无形财产在不同国家有着不同的理解,或指智力创造性成果(如日本),或指特定财产权利(如法国),或泛指一切具有财产意义之抽象物(如英国)。因此,将无形财产概括为知识产权的客体,尚未在世界范围内形成共识。
持此观点的学者认为,知识产权的客体是知识财产及其相关精神权益。这种观点没有弄清楚知识产权兼具人身性和财产性的真正含义。首先并非所有知识产权都具有人身权和财产权双重属性。其实,只有在版权领域(更确切些讲,在作者权中),才谈得上人身权。应当清楚的是,版权双重性中所说的人身权与民法人身权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著作人身权的特殊性在于它是依附在著作财产权之上,不能单独存在的。而且,单就精神权益中的 “权益”一词来说,也是有问题的。“权益”,严格来说是权利与利益的缩写,这就又犯了将权利本体与权利客体混同的逻辑错误。
持此观点的学者认为:知识产权的客体是知识产品或曰知识财产,是人们在精神生产过程中创造出来的,它没有外在形体,但具有内在的价值与使用价值。知识产品表现了客体的非物质性,也突出了其为人类创造的兼具商品和财产特点产物的属性。但是知识产品与知识财产两个概念相比较,知识财产的范围和其拥有的主体范围更广泛,就象用英文INTELLECTUAL PROPERTY 来描述,比用 INTELLECTUAL PRODUCTS 更为普遍、更易为人们所接受一样。此外知识产品的表述还易使人们对其与知识产权物质载体相混淆。
在笔者看来,在现阶段,试图将知识产权范围内各项具体权利的客体抽象为一类,在目前而言是无法做到的,这是由知识产权本身的复杂性决定的。这也许正是为什么“在十八世纪产生出‘知识产权’这一术语的德国,从本世纪初开始,反倒不大使用‘知识产权’了。”正是基于此,吴汉东教授才发出感叹“以知识产权名义统领下的各项权利,并非都是来自知识领域,并非都是基于智力成果而产生,‘知识’一词似乎是名不副实。”唐广良教授则提出“知识产权是一个‘开放’的领域,是一个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的领域,是一个永远无法限定的领域。只要人类社会还在进步,还会有新的、不能为其他法律规范加以调整的社会现象出现,知识产权的范围必然会不断扩大。”所以笔者认为,知识产权范围的不确定性决定了我们对于知识产权应采用模糊论的认识方法,知识产权的开放性决定了知识产权的客体必将是一个开放的体系,所以对于知识产权的客体应采用发展的观点,具体权利具体分析。

 U633687664
U633687664
 U582679646
U5826796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