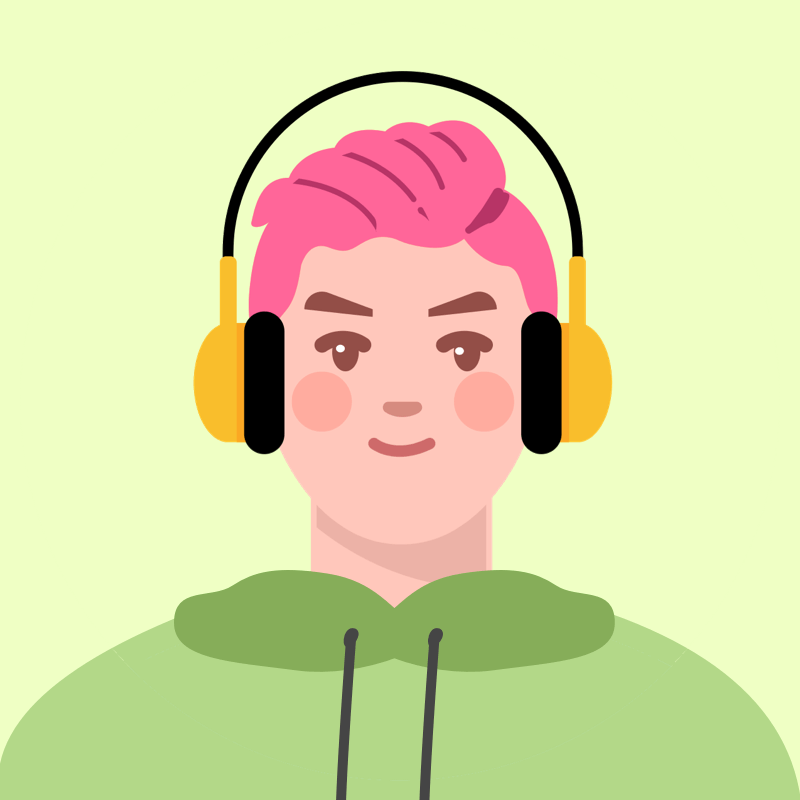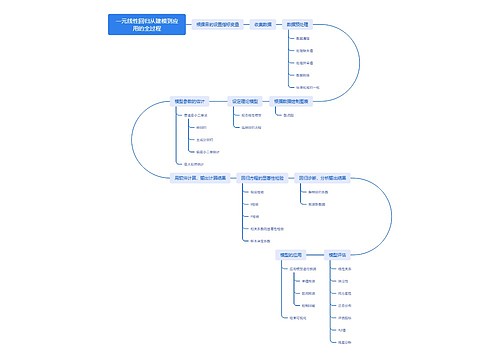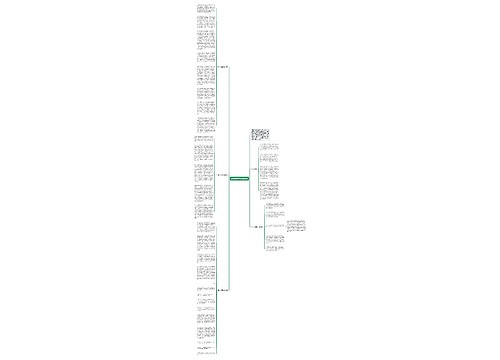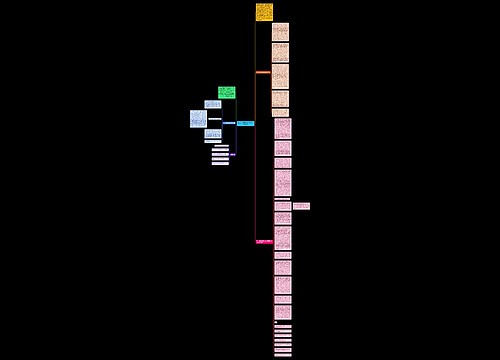民法基本原则适用的规则思维导图
感情愚钝
2023-02-22

规则
基本原则
民法
法律
遗嘱
规定
具体
没有
社会
民法
民法知识
民法基本原则
四川省泸州市那桩闻名全国的遗赠案早已尘埃落定,但其中涉及到的法律问题并没有就此画上句号,至少没有形成一个相对统一的观点。该案不仅受到媒体的广泛关注,学术界亦引发诸多讨论,人民法院出版社出版的《判解研究》还专门约请专家对此案进行了探讨。从获得的信息看,各方对此案的分歧仍然明显。如果没有形成一个相对统一的意见,那么,普通百姓甚至司法人员都将产生一种模糊认识。这种现象反映在具体案件上,很可能会出现“同样的事实,却得出不同、甚至相反的判决结果”这样适用法律不统一的严重后果。这种后果会使人们对自己的行为得不出合理的
树图思维导图提供《民法基本原则适用的规则》在线思维导图免费制作,点击“编辑”按钮,可对《民法基本原则适用的规则》进行在线思维导图编辑,本思维导图属于思维导图模板主题,文件编号是:c726647659221589f3d316d40773d45c
思维导图大纲
相关思维导图模版
民法基本原则适用的规则思维导图模板大纲
该案争论的焦点是法院的判决依据,即遗嘱的内容是否违反了《民法通则》第7条有关“民事活动应当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规定。审理法院认为:遗嘱人黄某将自己的财产遗赠给与之同居的本案原告张某,其遗嘱违反了该条的规定,因此,根据《民法通则》第58条“有关民事行为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的无效”的规定,认定遗嘱无效。可见,该案是直接引用法律规范中的基本原则进行判决的。那么,民法的基本原则能否作为审判规则?适用民法基本原则作为审判规则的条件是什么?“遗赠纠纷案”的判决存在什么问题?本文试就这些问题阐述以下观点。
一、民法基本原则的理论
民法的基本原则,是指其效力贯彻民法始终的民法根本性规则,是在民事立法、司法中必须遵守的规则。除在法律体系中所具有的功能外,基本原则的重要功能还在于它是法律解释的依据,是克服成文法局限性和弥补法律规范漏洞、解决具体法律规范矛盾的工具,同时基本原则也是授权司法者自由裁量的基础。
从法律规范的关系角度讲,各种具体的民事法律规范是在民法基本原则的精神指导下制定的。在法典化国家,民事法律规范的上千个条文中,包括民法基本原则,但更多的是民事具体规范。基本原则反映立法精神和立法目标,其具体表现具有抽象性、不确定性,但是作为行为规范和裁判规范的法律,必须具有可把握性和操作性才有意义,所以,法典中需要把基本原则在特定的民事关系领域的表现形式确定下来,使之具体化,便于人们理解,也便于司法者操作。数目众多的具体民事规范是民法基本原则的具体化,所以,通常情况下,依据具体规范所进行的民事行为也是符合基本原则精神的。
基于上述理论,民法的基本原则当然具有审判准则的功能,但是,审判准则功能的表现是在法律对案件缺乏具体规定时反映的,司法机关在处理具体案件时,首先应适用具体法律规范,在有具体规范可供适用的情况下,不得直接引用基本原则审理案件。这主要是缘于两方面的原因:其一,各基本原则的内容是极为概括和抽象的,依杨仁寿先生的说法,乃属一白纸规定。各基本原则的词语从规范意义上看也是模糊的,如诚实信用原则,其具体含义究竟是什么,法学界一直有争论;公平原则的内容也是不确定的,对同一事实,根据不同的标准,可以有多种公平;社会公共利益原则,在不同国家或同一国家的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解释,甚至在特定的情况下,多数人的利益不一定就是社会公共利益。所以,直接以基本原则为依据判决具体案件容易造成法官自由裁量权范围的扩大,裁判结果也易使人产生异议。其二,根据民法学一般原理,各种具体民事法律关系的成立,都以各种具体的法律规范为依据,没有单独的以基本原则为依据成立的法律关系。如:买卖合同关系的成立,其依据是有关买卖合同的法律规范,而仅仅依据平等原则或意思自治原则是不可能在当事人之间成立买卖关系的。所以,对具体案件也应以法律关系成立时所依据的规范进行裁判。当然,这样说并非否定基本原则的价值,基本原则在各项民事活动中应当被普遍遵守,但直接作为具体案件的裁判依据则是有一定限制的。
根据民法学的一般原理,对基本原则的规定,只有在以下情况才得直接引用:一是在案件的事实没有具体法律规范可资适用时,适用基本原则的规定。基本原则的功能之一即是弥补法律漏洞,但在没有具体法律规范时,才能称之为有法律漏洞,基本原则才有补充漏洞的适用余地;二是在对案件的事实有两种以上的具体法律规范都可适用,而两种规范的适用又有矛盾时,适用基本原则的规定来解决具体规范之间的冲突,即在选择案件适用的具体法律时,法官必须以民法基本原则为准则,考虑案件处理结果是否符合法律的最高价值——公平和正义。如:在由于监护人的原因,以及动物饲养人的疏于管理,使动物伤及被监护人的案件中,对被监护人的损害,根据法律对监护人职责的规定,监护人应承担责任;而根据法律对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规定,动物的饲养人应承担责任。到底应由谁承担责任呢?这种情况下,法院就可以依据公平原则,运用自由裁量权来处理具体案件,因为,没有办法仅适用一个具体的法律规范来裁判该案。除以上两种情况外,严格来讲,法院不得直接以基本原则作为裁判规范。换句话说,在有具体法律规定的情况下,法院没有理由,也没有必要直接适用基本原则。否则,立法时就没有必要规定那么多具体条文,而直接规定几项基本原则就足够了。不直接适用基本原则,并不等于在司法实践中,就可以不遵守基本原则。事实上,由于具体法律规范都是以基本原则为指导思想制定的,所以,适用具体规范,也是在贯彻基本原则的精神。
法律规范不仅是裁判规则,同时也是行为规则,具体法律行为的实施、法律关系的成立,都是根据具体的法律规范进行的。因此,通常情况下,法律行为是否有效,应以具体法律规范来检验:不符合具体法律规范的无效,符合具体法律规范的就有效。只有在具体法律规范本身被认为违反基本原则精神时,根据该具体规范而成立的行为才可以被认定为无效。这种规则,在法解释学上被称为“禁止向一般条款的逃避”。“向一般条款的逃避”,指关于某一案型,法律本有具体规定,而适用该具体规定与适用基本原则,均能获得同一结论时,不适用该具体规定而适用基本原则。这种现象应予禁止。其理由即是:(1)具体规定是基本原则的具体化,个别制度是在基本原则的指导下设计的,因此,法院在处理民事案件时,应严谨地遵守如下原则:先以低层次之个别制度作为出发点,须穷尽其解释及类推适用上之能事仍不足解决时,始诉诸基本原则;(2)如果此情形允许直接适用基本原则,而不适用法律的具体规定,必将导致法律权威降低;(3)在适用法律具体规定的情形,法官之价值判断过程清楚,依立法者意思探究,判断其结论当否容易。而适用基本原则的情形,其价值判断过程暧昧不明,其结论当否不易判断。
具体规定是否违反基本原则,以及具体规定违背基本原则规定精神时应如何处理的问题,应看适用具体的法律规定所获得的结果是否违反社会公正,如果适用具体规定的结果违反社会公正,法院可以不适用具体规定而直接适用基本原则。但这种情况必须进行限制,否则极易造成法官滥用基本原则、任意解释法律的不良后果。鉴于我国最高人民法院有司法解释的权力,所以,在遇到适用具体规定违背基本原则的情况时,应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批准后,才能直接适用基本原则处理具体案件。其他各级法院不得自行决定直接适用基本原则而不适用已有的具体规定裁判案件。
二、“泸州遗赠纠纷案”中的遗嘱是否违反了“社会公共利益”和“社会公德”
我国《民法通则》第7条的规定在性质和作用上相当于其他国家规定的“公序良俗”原则,即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原则。也就是说“社会公共利益”相当于“公共秩序”,“社会公德”相当于“善良风俗”。“社会公共利益”一般指不特定的第三人的私人利益和与基本法律价值相联系的私人利益,如人的生命、健康和自由利益等。“善良风俗”一般指被当时社会多数人接受并被当时法律认可的良好习惯。
本案中,黄某用遗嘱方式将其财产遗赠给同居的张某,是否会损害不特定的社会一般人的利益,导致其处分财产的自由与社会公德之间产生冲突呢?我认为是否违反社会公德,必须探究遗嘱人立遗嘱时主观的真实意思。另外,还须探究其将遗产遗赠给“同居者”的原因,以及不给其配偶的原因。从社会一般道德观念看,如果遗嘱人以遗嘱方式把遗产给“同居者”,目的是为了能继续维持他们的不正当关系,或者是为了报答“同居者”过去曾给予他的快乐的生活,那其遗嘱就是违反社会公德的。而如果遗嘱人是因为“同居者”生活困难,或者是为报答“同居者”在其病重期间对他的照顾而立遗嘱把财产遗赠给她,那又怎能说其遗嘱违反社会公德呢?
本案中,从遗嘱订立的时间以及张某对遗嘱人照顾的实际情况分析,黄某用遗嘱方式处分自己的财产的行为,是其行使财产权的表现。其遗嘱是严格按照法律规定条件和程序订立的:遗嘱的主体合格,即遗嘱人具有遗嘱能力;遗嘱人的意思表示真实,即遗嘱人没有被胁迫或被欺诈,遗嘱的内容没有被伪造、篡改;遗嘱的内容合法,即遗嘱处分的财产是遗嘱人个人的合法财产,没有违反法律的限制性规定;遗嘱的形式合法,即遗嘱的形式符合法律规定的五种形式的要求。本案被继承人订立遗嘱时系完全行为能力人;将遗产遗赠给张某是其真实意思;没有处分别人的财产,也没有违反法律有关特留份等的规定;其遗嘱经过了公证。所以,黄某的遗嘱是符合法律有关遗嘱的有效条件的。符合法律规定的遗嘱当然无损“公共秩序”,他只是处分了自己的财产,没有损害他人的利益,当然也就不能认为侵害了“社会公共利益”。遗嘱本身也并不违反社会公德。在一般意义上讲,人们都认可:自己只能处分自己的财产,不能处分他人的财产这一习惯。至于张某作“二奶”的行为当然是违反善良风俗的,但是,这与黄某的遗赠行为是否违反善良风俗不是一个法律关系。退一步说,如果不能认定黄某立遗嘱的行为是为了继续维持他们的不正当关系,又怎能认定黄某不是对张某照顾他而用财产进行的报答呢?
从另外一个角度分析,法院的判决是因为黄某将遗产遗赠给了张某这个非法同居的“第三者”而认定遗嘱无效的呢?还是因为没有将遗产给其配偶而认定无效?亦或是二者兼而有之?
就第一种情况而言,如果因为张某是“非法同居者”身份而剥夺其受遗赠的权利,理由即应是“非法同居”在道德领域是受谴责、被非难的。但问题在于,假如张某不是“非法同居者”,而是黄某没有配偶而与之同居(未婚同居在我国的道德评判中,同样是受谴责和被非难的),那么,这种情况下,黄某将其遗产遗赠给张某,法院是不能以遗嘱违反社会公德而认定无效的。所以,受遗赠人的身份不能作为判断遗嘱是否有效的标准。
针对第二种情况,依据我国继承法的规定,除有关特留份的规定外,法律规范中都强调尊重当事人的意思,没有强调必须为配偶保留遗产。从本案给明的情况看,黄某的配偶并非法律规定的需要为其保留必要遗产份额的人,因此,不能以遗嘱没有为配偶保留遗产而认定无效。
而对于第三种情况,在前两种情况都不能作为依据时,从逻辑上讲也就没有了适用的基础。
有学者认为本案的问题是法律规定出现了漏洞。认为我国《继承法》第16条只规定:“公民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赠给国家、集体或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人”,没有对“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人”进行限制,致使本案没有适合的法律可以适用,导致法院直接以基本原则作为处理案件的依据。这种认识是值得商榷的,从立法角度看,任何一个法律条文的出现,都是要确立并维护一种秩序,而维护秩序的基础则是利益平衡的结果。某一个条文的出现,都有其立法理由,都有其立法所要达到的目标。《继承法》第16条的规定也不例外,它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尊重立遗嘱人的意思,尊重立遗嘱人的财产权的体现,也就是意思自治原则的体现。这种权利的行使只要不违反继承法对遗嘱的限制,就应认定有效。随着社会的发展,继承法的有些规定确实需要修改和补充,但法律规定在此没有出现所谓的漏洞。不能因为憎恨“二奶”,就认定她没有获得受遗赠财产的权利,如同不能因为憎恨盗窃犯,就认定他不能获得受遗赠权利一样。
如前所述,遗嘱人是否将遗产遗赠给其配偶,在法律层面上是遗嘱人财产处分权利的体现,对这一权利的限制法律上有明确的规定。如果其配偶有固定的收入,或有生活来源,法律并不强求遗嘱人将财产必须留给其配偶。甚至在其配偶对其尽了扶养照顾义务的情况下,也不做此强求,更不用说,配偶没有尽照顾义务的情况。《继承法》甚至在有关法定继承的规定中认为:有扶养能力和扶养条件的继承人,不尽扶养义务的,在分配遗产时应当不分或少分。所以,本案中遗嘱是否违背社会公德问题,也可以从其配偶处找寻原因,遗嘱人为什么没有列其配偶为遗嘱继承人?依此才能确定争议的遗嘱是否违反社会公德,进而确定遗嘱是否有效,而不能将遗赠人与受遗赠人之间的关系是否合法作为判断依据,尤其不能以受遗赠人的行为是否违反社会公德为依据来决定遗嘱人的遗嘱是否有效。正象有专家指出的:如果张某的身份不是“第三者”,而是黄某的同事,或者是与黄某不认识的陌生人,法院肯定不会判决遗嘱无效;进一步说,如果黄某通过遗嘱将其财产遗赠给他的开赌场的朋友或嫖娼的朋友,法院是否就认定遗嘱无效呢?显然不会。因为,这与遗赠不是一个法律关系。张某的行为破坏了他人的家庭,是不道德的,但这与其接受遗赠是两种法律关系,受不同的法律调整。这如同不能剥夺罪犯的受遗赠权一样。同样,承认黄某的遗嘱效力,以及承认张某的受遗赠的权利;并不等于肯定他们的非法同居的行为。从法律利益平衡角度分析,在事实上,承认张某的受遗赠权,并不会影响人们的道德评判标准。因为,她在周围群众中,仍然会被认为是不能被接受的“第三者”,这种道德谴责对她并不轻松。实际上,《继承法》没有必要“管得过宽”,作为民事法律的一种制度,《继承法》没有能力将人们所有的行为都予以规范。
从另一方面讲,继承法之所以规定法定继承,将继承人限定在包括配偶在内的近亲属范围内,是自然法延续的结果,其主要的理由是法律推定被继承人具有要将其遗产留给其近亲属的意思。法定继承适用的前提是被继承人没有遗嘱。如果被继承人有遗嘱,那就没有必要再由法律进行“推定”,而应直接依照被继承人的真实意思处理其遗产。这在《继承法》上表现为:遗嘱继承和遗赠的效力高于法定继承,这也正是民法意思自治原则的体现。实际上,该讨论也涉及另一重要问题,即在继承法中,继承人的所谓继承权是根据什么来取得的,也就是说在继承制度中,究竟应以死亡人的意思自治为着眼点,还是以继承人的利益为着眼点。这当然是一个立法选择问题,从现代各国法律的规定看,对被继承人意思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在遗产问题上,继承人的利益与被继承人的利益(处分财产的权利)相比,被继承人的意思更应得到尊重。
从法律体系角度讲,法律对民事主体处分自己财产的行为应是统一的。即在物权法、债权法以及继承法中,除了因权利客体本身的特点不同而法律规定有所不同外,法律对主体处分财产的规定应是一致的。如果主体对自己的某项财产的处分,在物权法中是符合基本原则精神的,那么在债权法以及在继承法中针对该项财产的处分也应是符合基本原则精神的。本案中,我们假设黄某将遗嘱中涉及的财产抛弃或者毁损,法律能否认定这种财产处分行为无效呢?恐怕不能,我们再假设黄某生前将遗嘱中所涉及的财产赠与给张某,法律恐怕也不能认定这种处分行为无效,那么为什么黄某用遗赠的方式处分其财产就被认定为无效呢?
三、法院应维护人们对法律的信任
在法制社会中,如果一个人依据法律的规定实施了某种行为,通常他相信该行为会获得预期的法律效果。民事法律的规定是要通过法律规范,建立一个模型体系,引导人们进行正常的行为,作为“人法”,民法规范设计了一个“完整的法律人”,鼓励人们向这个“完人”努力。如果一个人按照法律的规定行事,却又被认定为无效,那么,人们就会失去对法律的信任,实际生活中,善良的人就会无所适从,而邪恶的人就会我行我素,社会就会变得无序。所以,真正实现法制社会目标,法院就应保证那些依照法律规定实施行为的法律效果能够实现。
直接适用法律的基本原则裁判案件,必须遵守法律适用的基本规则。一个判决的正确与否,不在于人们欢呼与否,而在于是否依法裁决,包括是否遵守法律的适用规则。对私人权利的尊重,就是尊重法律。如果对遵守法律的人的利益不保护,法律就变成了一纸空文。目前,我国的法制还相对不健全,人们的法制观念也十分欠缺,因此,培养和保护人们对法律的信心就显得格外重要。相信没有人希望《威尼斯商人》中夏洛克对威尼斯城邦法律效力的大声质问出现在今天的中国。
【作者介绍】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副教授。
注释与参考文献
案件的基本事实是:黄某与蒋某系夫妻,后黄某又与张某租房公开同居。在黄某知道自己是肝癌晚期后,即订立公证遗嘱:将自己的财产遗赠给张某。后黄某死亡。从二人同居到黄某死亡期间,一直是张某照顾黄某。由于蒋某拒绝执行遗嘱,张某诉之法院。法院以遗嘱违反《民法通则》第7条“民事活动应当尊重社会公德”为由,驳回起诉。
《南方周末》2001年11月15日的“‘第三者’继承遗产案一石激浪”;《北京青年报》2001年11月20日的“第三者是否有权接受遗赠”;《法律与生活》2002年第2期的“‘二奶’与情人的遗产”;中央电视台《今日说法》2001年11月27日“遗嘱算不算数”;《中国青年报》2002年1月18日的“二奶持遗嘱要分遗产引用道德断案的界限在哪里?”等等。
杭州也曾发生老画师以遗嘱的方式将自己仅百万的遗产逾赠给小保姆,而画师的两个女儿从小保姆处取走部分财产后,被小保姆告之法院。法院判决老画师的遗嘱合法有效。该案中,小保姆在七、八年的时间中一直住在老画师家里。
同样是四川省的案件,在一居民区,一居民因反对在其接下开设麻将室而告至居委会,居委会组织小区的近200户人家对是否在小区内设置麻将室进行投票。结果,只有一家反对。最后,该居民诉至法院,法院并没有以该居民是少数而驳回起诉。
我国《继承法》第13条第4款。
张俊浩.民法学原理[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
梁慧星.民法解释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
梁彗星.诚实信用原则与漏洞补充[A].民商法论丛(第2卷)[C].北京:法律出版社,1995.71.
许明月,曹明睿.沪州遗赠纠纷案的另一种解读[A].判解研究(第2辑)[C].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
引用法条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第七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
[3]《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
[4]《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第五十八条
查看更多
相似思维导图模版
首页
我的文件
我的团队
个人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