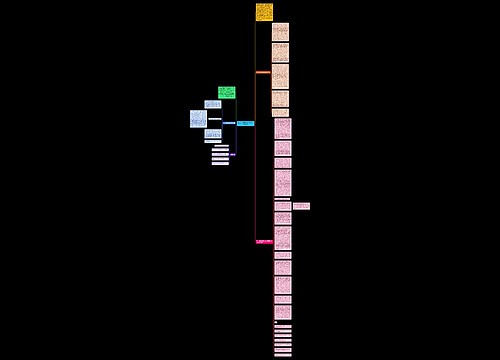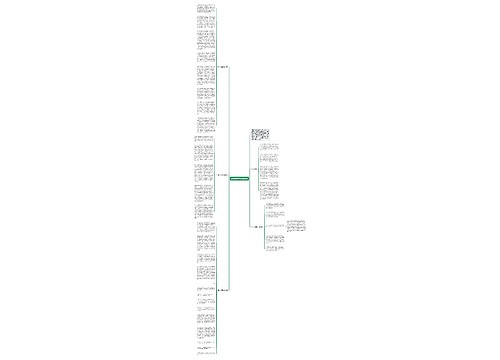试论禁止权利滥用原则的本质内涵思维导图
南归
2023-02-22

[内容摘要] 禁止权利滥用原则已在司法实践中得以广泛运用,然就该原则尚存在诸多认识不清的地方。禁止权利滥用原则历史起因,在于个体权利与社会利益矛盾激化,客观需要权利的限制。该原则为了权利而限制权利,其最终目标是保护和实现权利。但该原则授予法官自由裁量权,有导致权力滥用而减损权利之危险。为解决这一矛盾,使禁止权利滥用原则扬其利而避其弊,应强调其有限使用,立法上要限定在必需领域,司法中要合法、公正运用。
树图思维导图提供《试论禁止权利滥用原则的本质内涵》在线思维导图免费制作,点击“编辑”按钮,可对《试论禁止权利滥用原则的本质内涵》进行在线思维导图编辑,本思维导图属于思维导图模板主题,文件编号是:492b1f242904dfb242064a0fbde0ef19
思维导图大纲
相关思维导图模版
904名中国成年人第三磨牙相关知识、态度、行为和病史的横断面调查思维导图
 U633687664
U633687664树图思维导图提供《904名中国成年人第三磨牙相关知识、态度、行为和病史的横断面调查》在线思维导图免费制作,点击“编辑”按钮,可对《904名中国成年人第三磨牙相关知识、态度、行为和病史的横断面调查》进行在线思维导图编辑,本思维导图属于思维导图模板主题,文件编号是:10b9a8a2dd2fb4593f8130ef16c320fc

9.战斗的基督教思维导图
 U582679646
U582679646树图思维导图提供《9.战斗的基督教》在线思维导图免费制作,点击“编辑”按钮,可对《9.战斗的基督教》进行在线思维导图编辑,本思维导图属于思维导图模板主题,文件编号是:33d168acd0cd9f767f809c7a5df86e3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