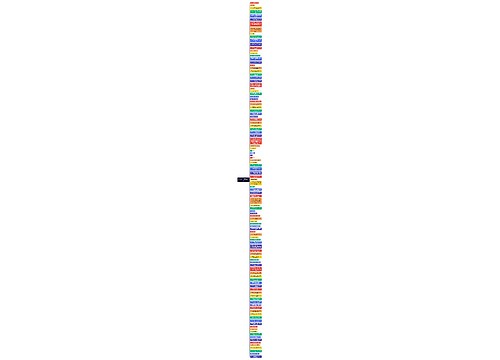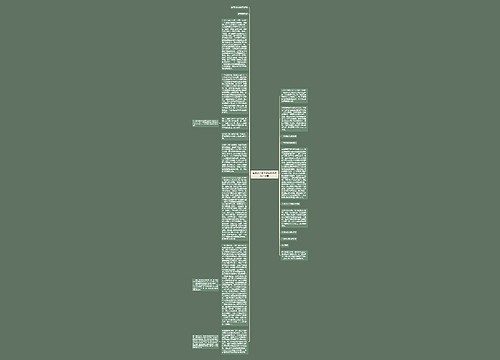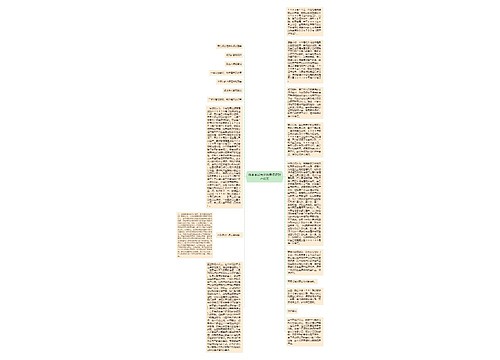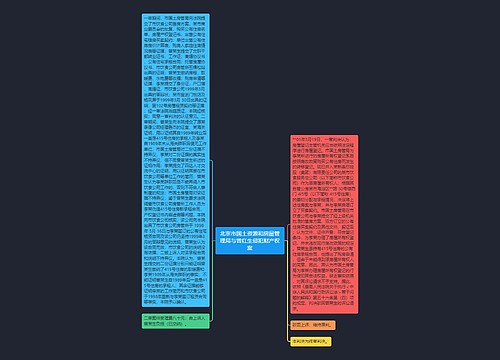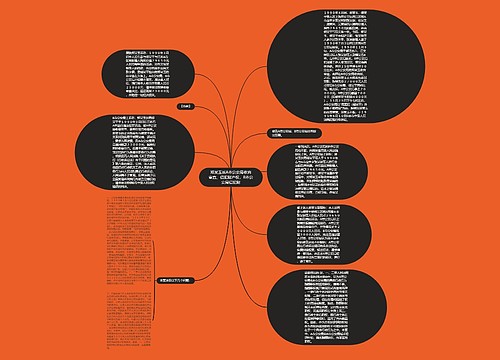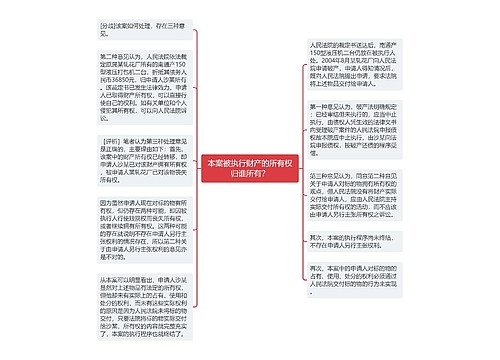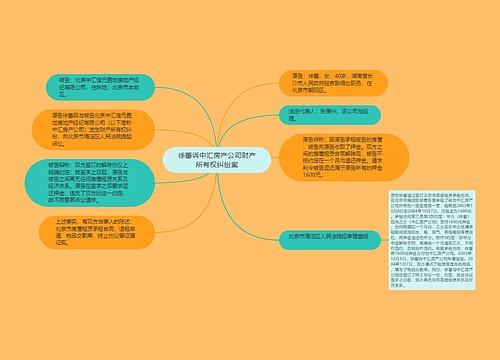原告自1984年至1998年期间,承包经营位于哈尔滨市南岗区**路30号南岗区跃进运输队(以下简称“运输队”)。始承包时,运输队有车辆一台,价值 17000元;办公室71平方米,三个库眼的车库309.6平方米,价值610478元。1987年3月份,A村村委会同张某鸣签订协议,双方约定,A村不再对车队进行投资,新增资产由车队自筹解决,新增财产的所有权同车队成员所有。1990年,车库毁于火灾,车队对火灾烧毁的车库进行重建,面积增加至475平方米,库高较原车库加高0.8 米,增加部分价值26924元。1992,原告购进KN150型汽车一台,价值58500元,1996年购进ZN150型汽车一台,价值58500元, 1996年购进EJ40型装载运输车一台,价值18万元。以上运输设备共计439680元。承包期间,原告先后投资购置加油泵、油罐、气罐等机器设备共 67921.5元。1997年,运输队进行产权制度改革,1998年4月,运输队同被告签订房屋租赁合同。1998年4月中旬,运输队解散。(1997— 1998年事实部分似不合逻辑,但此事实部分属对原被告辩词的整理,参见附录:庭审实录。)2000年8月,哈尔滨市科达小区安居工程启动,须征用南岗区学兴路30号的房屋及场地,被告同经济适用住房发展中心签订征地及拆迁协议,并获得征地及拆迁费用200万元。原告以被告非法财产权为由,诉至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要求确认其对上述机器设备、房屋及运输设备的所有权,判令被告停止侵害,赔偿损失。
原告辩称:1998年4月份运输队同被告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属在被告胁迫情况下签订的,请求法院撤销该合同。
A村向跃进乡所报的关于跃进运输队产权改制的分配方案(产权界定方案)在程序上违背法定程序,实体上违反产权界定“谁投资,谁所有,谁收益” 的原则,侵害原告的合法权益,应属无效。
被告辩称:原告签订房屋租赁合同证明原告在1998年已承认被告对房屋的产权。
《民事诉讼法》第四十条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由审判员、陪审员共同组成合议庭或者由审判员组成合议庭。合议庭的成员人数,必须是单数,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民事案件,由审判员一人独任审理。”而根据该法第一某四十二条的规定,只有在基层人民法院和它派出的法庭审理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的简单的民事案件,才适用简易程序。这就意味着,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任何民事案件,皆应依法由三人以上单数的审判员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
面对合议制如此普遍地被违反的现象,我们应该进一步地深入思考其内在的原因及相应的救济措施。按照“恶法非法”的法理,评议一种形式上违法行为的是否应受谴责性,首先应评议该违法行为(形式上)违反的法是否良法,违反良法的行为应受谴责和纠正,对于“恶法”则应及时修改“恶法”。与此相似,面对合议制的普遍被违反,我们首先应从整体上对合议制的良劣作一评价,如果合议制被认定为应该坚持,则应采取措施纠正违反合议制的行为。
在确认了合议制在理论上的合理性后,我们所需要做的是分析合议制普遍被违反的内在原因并寻找相应的救济方法。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导思想,儒家思想视“无讼”为理想境界,这我国古代法制史上漫长的重实体而轻程序的事实。程序法从诸法合体中独立出来还是晚清以后的事情。受长期传统法文化的影响,我国法学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坚持了“程序工具主义”,将“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这一功利主义的原则应用于法律裁判的分析中,认为“对于法的实体部分来说,惟一值得捍卫的对象或目的是社会最大多数成员的幸福的最大化。而对于法的附属部分,惟一值得担卫的对象或者说目的乃是最大限度地把实体法付诸实施。”这是我国法学重实体而轻程序的理论根源,而建国以来的法学实践一直把法律作为阶级统治的工具而忽视法律作为社会综合调整器的重大意义,这更加弱化了全民的程序意识。(关于程序法的价值问题,参看刘乃忠、张云鹏《论程序法的独立价值》,载《武汉大学学报》(哲学与社会科学版)2000年5月,及锁正杰《刑事程序价值论:程序正义与人权保障》,载《中国法学》2000年第5期。)
这种重实体而轻程序的法制思想形成了现阶段合议制被普遍违反的思想根源。在人权保护、司法公正的呼声来越高的今天,程序本位主义取代程序工具主义,从而更加重视程序法的内在价值成为法学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必然选择。(程序本位主义认为,评价法律程序的价值标准更在于其本身是否具有一些内在的优秀品质,而不仅在于程序作为实现实体法手段的有用性。见刘乃忠、张云鹏《论程序法的独立价值》,载《武汉大学学报》(哲学与社会科学版)2000年5月,第352页。)相信随着人们对程序法独立价值的进一步认识,合议制的施行情况会有很大改观。
在本案原告的诉讼主体是否适格的问题上,原被告双方存在着较大争议,同时原告自身也存在着对主体是否适格的模糊与前后矛盾。原告在起诉书中以张某鸣个人署名,即起诉书反映本案的原告是张某鸣个人,而原告在法庭质证阶段向法庭提供的第八份证据是运输队其他十名成员的授权书,原告自身在对被告提交的证据提出质疑时又强调本案中张某鸣仅以其名义代表着企业中的所有人员。本案在立案阶段,立案庭认为“应用张某鸣个人名义起诉,属于财产共有”。(据原告转述,参看附录:庭审实况,第4页。)这样,在本案中原告究竟应是谁的问题上就更显得模糊不清。张某鸣个人作为本案的原告是否适格?
1984年至1998年期间,运输队的承包人虽为张某鸣个人,但个人承包并不排斥也不能否认该承包经营期间车队其他成员对车队的投资。也就是说,在该承包经营期间,车队的新增投资所建设或购置的房屋、设备以及经营收益(除去应纳税款和依承包经营合同上缴集体的收益外)所建设或购置的房屋、设备,依照“孳息物的所有权除依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由产生孳息物时的合法占有人所有外应归原物所有人所有”,应属车队全体成员共同所有。并且,由于在共有关系存续期间(即共同投资始至依法分割共有财产时止),车队成员未划分出各自对该共有财产享有的份额,因而该部分财产属于车队全体成员共同共有。
依《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三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为《意见》)第五十六条和第五十七条关于共同诉讼的规定,共有财产权受到他人侵害,部分共有权人起诉的,其他共有权人应当列为共同诉讼人;必须共同进行诉讼而没有参加诉讼的,人民法院应依法追加当事人,即追加为共同原告。本案中,如果A村侵害财产权的事实存在,则侵害的是车队全体成员共同的共同财产权,立案庭认为由“张某鸣个人名义起诉”是错误的,如果庭审时仅有共同财产权中的一人参加诉讼,而其他共同财产权人均未参加诉讼,法庭进行事实调查时有可能遗漏或歪曲部分重要事实,在确认财产权属时也有可能侵害其他共同财产权人的合法利益。
综上所述,本案正确的原告应是共同原告,包括运输队曾参与车队共同投资的8个队员。而在本案实际审理过程中,法院仅将原告界定为张某鸣个人,这是不合适的。
依据我国农村基层目前实行的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相关规定散见于《民法通则》、各种单行法律法规及党的各种决议、通知、领导人讲话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权的主体是劳动群众集体组织,村是我国农村中劳动群众集体组织的重要形式。劳动群众集体组织有自己的财产,有自己的名称、组织机构和场所,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符合我国《民法通则》关于法人依法确立应当具备的基本条件和特征,应属于法人性质的组织,并具备企业法人的性质。因而,在法律上,“村”是具有法人资格的。以村为主体的劳动群众集体所有权,其客体主要是农村的土地,从事农业生产所各种农业基础设施、农用设备,以及服务于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的乡镇企业、文化教育设施等。
依据《宪法》及《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相关规定,农村的村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同时,村民委员会又是我国农村基层中“村”这一劳动群众集体组织的所有权代表,代表村行使对上述集体组织所有的土地、农业基础设施、农用设备和乡镇企业、文化教育设施的所有权,并进行组织和管理。在本案中,A村这一集体经济组织是运输队承包合同的发包方,又是同房屋开发中心签订拆迁协议的一方当事人,因而依法成为本案的被告。而作为A村集体所有权代表的A村村委会,则依法成为本案中被告的代表。
依据我国法律关于承包经营合同的有关规定,承包人享有对其承包经营的集体财产的经营权和在承包经营合同规定数额向集体组织缴纳相当收益后的收益权、对其在承包经营过程中的投资及投资所生法定孳息物享有所有权。本案中,对于该运输队的所有财产,应分为两部分:一是集体经济组织A村对运输队的前期投资,包括车辆、车库和办公室,集体经济组织A村对该部分财产享有所有权,且该所有权并不因承包经营的存在而改变。而承包经营人在承包经营期间依承包经营合同对该部分财产享有合法使用、依法经营和收益的权利。第二部分是车队所有成员在承包经营人张某鸣承包经营期间对车队的共同投资及其法定孳息。车队所有成员依法享有对该部分财产的共同所有权。
1998年承包经营人张某鸣和集体经济组织A村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由于原告举证足以证明该租赁合同属在胁迫情况下签订的,合同当事双方意思表示不真实,在当事人一方提出应予撤销并认定为无效时,法庭应依法认定该合同无效,该合同不对房屋的所有权造成影响。
对于本案中各部分资产的具体数值问题,本文不予讨论。

 U482242448
U482242448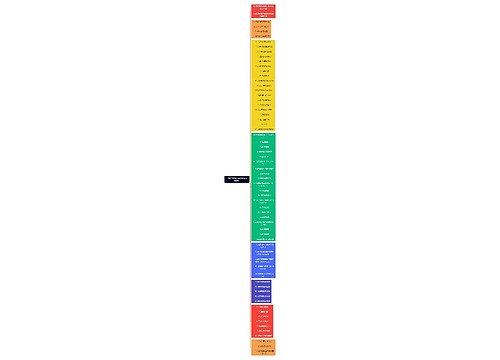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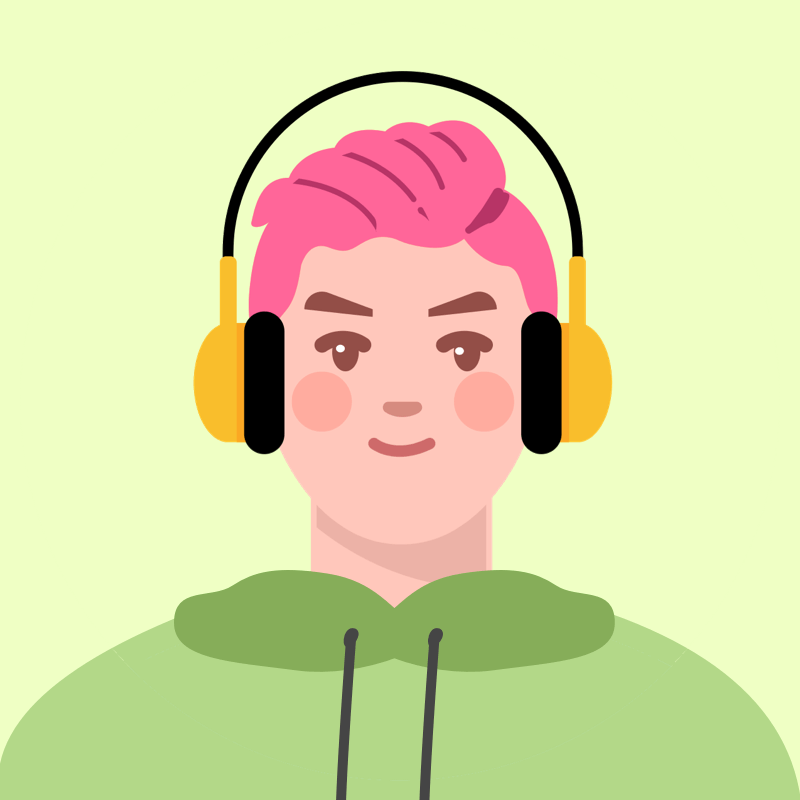 U982226919
U9822269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