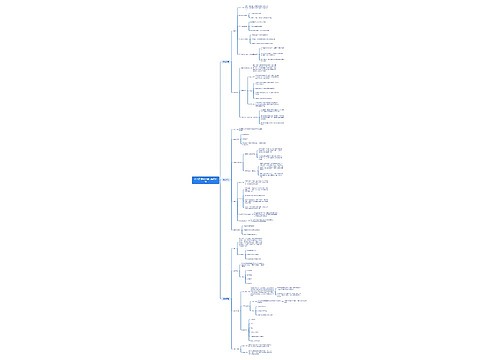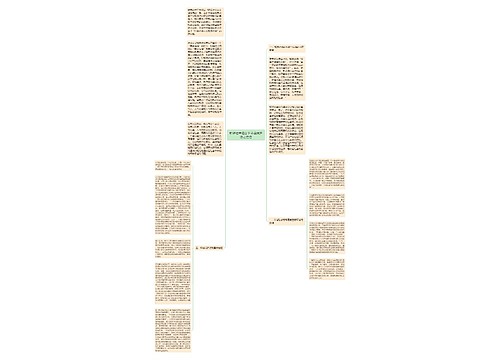无论“国家主权”还是“联合国主权”,都建立在自由主义立场上,将“国家”或“联合国”看作是人权保障的工具。在这个意义上,联合国原秘书长安南提出的这对概念,除了回应后冷战时期的人权保护,似乎了无新意。但事实上,这对概念的含义完全不同。前者强调是国家的自主决定不受外在的干涉,而后者则强调积极干预和主动建构。如果借用以赛亚・伯林的“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这对概念,那么安南提出的这对概念是否可以用“消极主权”和“积极主权”来理解呢?耶鲁大学法学院的保罗・卡汉教授正是从这个角度重新界定了主权概念。
“消极主权”植根于西方国际法的基督教―――自由主义传统之中,正如个体的求真德性存在于他面对上帝的内在灵魂活动,而国家的构成也源于人民的内在自我实现,而不是外部的强加。由此,消极主权使得国家享有了不受外来干涉的特权。二战后西方世界从外部给第三世界国家输出民主政体,就像拿破仑通过战争和政府给欧洲带来民主政体一样,都违背自由主义的消极主权传统。
“消极主权”实际上隐含了一种积极的观念,消极恰恰是为了创造一个自我积极实现的自由空间。消极主权为国家划定了外部边界,但这个国家之所以能够享有消极主权的特权,就在于它已透过主权人民构成了一个国家。正如消极自由强调“别管我”,积极自由回答“我是谁”一样,积极主权正是要确定“主权主体”。它涉及到领土、人口和制度的复杂建构过程,必然伴随着军事和意识形态的冲突和斗争。
消极主权以积极主权为前提。如果积极主权建构中把天主教会或者无产阶级革命作为国家自我认同的基础,那么消极主权就很难成为国际法秩序的基础。同样,如果一个民族没有能力实行自治,那么从外部干预其国内安排恰恰变成了一项道德和政治责任。如果说二战后的非殖民化运动是消极主权在发挥作用,那么冷战的争夺恰恰在展现积极主权:谁才有资格成为真正的主权者。而后冷战时期,恰恰可以看作是消极主权与积极主权之间的微妙平衡。
可见,主权国家之所以享有消极主权的特权,关键在于能否捍卫积极主权,能否将自我建构为一种独立的主权者。在西方历史上,积极主权的建构过程是通过美国革命、法国大革命以及反对拿破仑的欧洲反革命等这样的“革命行动”完成的。革命需要流血、牺牲和献身,它在摧毁旧秩序的同时也伴随着形成主权人民的创造性行动,正是这种形成主权人民的创生性使得这种流血牺牲具有祭献的神圣意义。国家要享有消极主权带来的自主性和独立性,就需要通过革命行动来展现积极主权的建构主权人民的能力,以及积极主权能够时刻准备流血牺牲来保卫主权的能力。
从欧洲的历史上,主权乃是胜利者的俱乐部,消极主权来源于经历了流血的战争和革命之后成长起来的主权人民以“国家”的形式获得了相互的认可和尊重。国际法的首要法则就是战争与和平的法则。国际法并不确保永久和平,但它给战争的胜利者赋予主权者的资格,并通过赋予其享有消极主权的特权来保证国际秩序的稳定。
从这个角度看,安南提出的“个体主权”或“联合国主权”如果要获得主权的性质,必须以积极主权的伸张为条件。按照卡汉的理论逻辑,个体如果要伸张其主权,必须做好流血和牺牲的准备,否则没有资格获得消极主权的特权,因为等待主权者庇护的个体不具有公民品格,自然也无法拥有“个体主权”。同样,无论是联合国主权,还是国家主权,要捍卫其消极主权的特权,也必须准备用战争、镇压和流血来展示其积极主权。二者结合在一起,恰恰构成了古希腊以来自由人结成自由城邦的西方传统。然而,当安南试图通过联合国的跨国管理为个人提供人权庇护,从而避免流血、牺牲和战争,是不是放弃了积极主权的内在要求呢?

 U582679646
U582679646
 U882673919
U8826739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