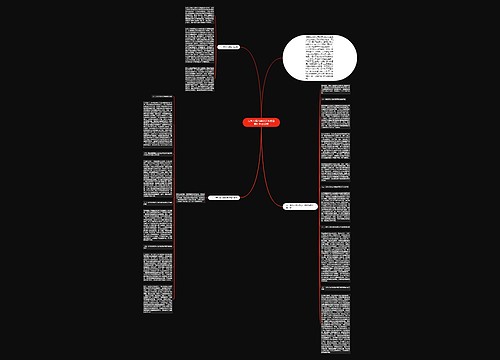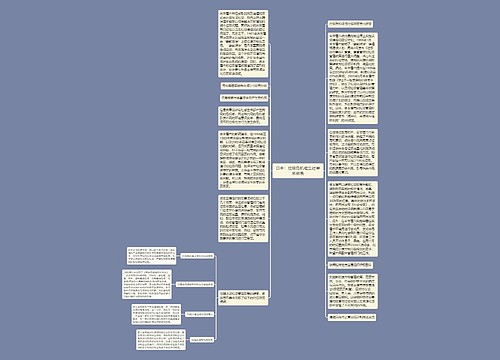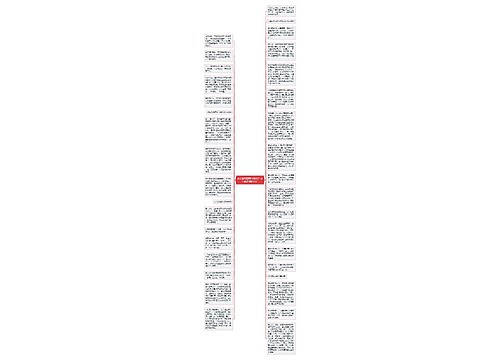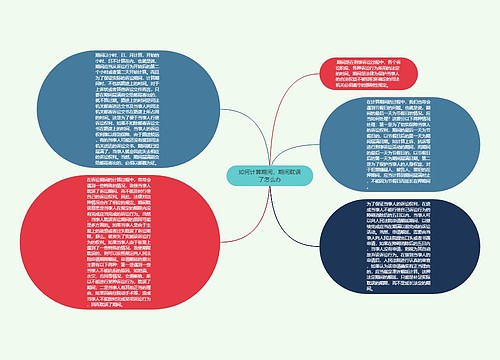我国制定《证券投资基金法》时,对私募基金的引进问题争议颇多,但最终还是未能对其作出明确规定。考虑到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以及资本市场国际化进程加速等各种社会经济及国际环境所发生的日新月异的变化,对私募基金问题一直采取回避态度并非明智之举。我国私募基金实务中存在的问题,既不利于保护投资者的利益,又不利于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同时,如前所述,私募基金是一种极具活力与创造力的金融理财的载体,从美国的实践来看,私募基金在推动金融创新方面极具积极作用,日本自引进私募基金制度之后,这项制度在促进资产运用方式及资本市场观念革新等方面也备受瞩目。
通过对美国、日本等国的私募基金制度的考察,笔者认为,我国在引进私募基金制度,构建私募基金法律规制体系时,为促使私募基金与我国投资基金业的制度整合,应当注意如下四个方面的问题。
(一)可以采用在一部投资基金法中同时规定公募基金与私募基金的规制方式
对于私募基金的规制方式,各国立法体例上存在着一定的差异。美国法中,私募基金被豁免于《1940年投资公司法》的管辖;德国法中一般认为年金基金及保险公司等机构投资者的资金广泛来自于年金参加者及保险参加者等投资者,因此其私募投资基金也广泛适用《投资公司法》的相关规定;日本采取德国的立法方式,私募基金受《关于投资信托及投资法人的法律》的规制,成为投信法下的特殊投资信托之一。从德国与日本的立法经验来看,在一部投资基金法中同时规制公募与私募两种形态的投资基金在实务操作中并无窒碍;同时,由于公募基金与私募基金之间的互为补充、相互促进的关系,在一部投资基金法中同时进行规定,对公募基金采取“高度管理”,对私募基金采“低度管理”的规制态度,从立法体例方面也显得较为完整且富于逻辑。因此,对私募基金单独立法,其成本较高也并非必要。
(二)在私募基金制度中,应当区分合格机构投资者私募及一般投资者私募
合格机构投资者私募的招募对象为符合法律规定的合格机构投资者,这在各国立法体例上基本相似。但就一般投资者私募而言,日本法仅采用了人数限定标准而未明确规定招募对象的资格要件,规定一般投资者私募的招募对象为“不满50人”;美国法中,私募基金的招募对象为“100人以下”,其对人数标准的要求低于日本法的规定,但对作为招募对象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严格规定。相较而言,美国法的规制方式更为科学。由于私募基金的投资者为特定对象,既有合格机构投资者,也有部分符合资格要件的一般投资者,他们通常拥有较高的投资知识、经验及资力,与私募基金管理人之间也多处于投资专家对投资专家的平等地位,因而其自我保护能力也较强。如不对参加私募一般投资者的资格进行相应限制,则难以防止并不具备自我保护能力的一般公众投资者为追逐暴利而参加私募,甚至可能出现一般投资者举债应募、集资应募或以来历不明的资金应募等现象,这部分投资者遭遇投资风险而引发的社会问题的覆盖面将更为广泛。目前,我国银监会于2007年1月23日颁布的《信托公司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管理办法》第6条已对合格投资者进行了界定,这在规定一般投资者私募参加者的资格要件时足可成为借鉴。
(三)对私募基金的规制重点在于防止其产生法律规避的情形
公募基金面向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其自我保护能力较弱,涉及面更为广泛,因此为保护社会公众投资者的利益,对公募基金的信息披露规制要求比较严格;私募基金面向机构投资者或资力雄厚的一般投资者等特定对象进行招募,他们通常自我保护能力及抗风险能力都较强,因此,私募基金的信息披露规制也较为宽松,各国一般不对其进行严密监管。鉴于私募基金的这个显著特征,必须要注意防止私募基金在利用私募形式完成招募行为之后,将基金份额转让给非合格机构投资者,或分割转让给更多人数的社会公众投资者,以这种形式发行的私募基金实为公募,其可以规避公募基金信息披露规制的严格要求,因此,必须对私募基金的份额转让问题进行明确限制。
如前所述,在我国私募基金发展历程中,大量资金流向了民间代客理财机构,目前,在非合法的民间协议型私募基金中,其双方当事人之间是典型的委托理财关系,其业务内容也极为隐蔽,合法性模糊,投资管理人既面临拖欠或抵赖业绩报酬的风险,又面临较高的道德风险,如引发问题则难以依靠法律手段来解决。这种现象一方面反映了私募基金业及委托理财业在我国具有极大的市场需求,另一方面又暴露了我国私募基金业及委托理财业所存在的混乱状况。目前,我国对私募基金及委托理财的概念的认识仍然存在许多混淆之处,厘清私募基金与委托理财的概念极为迫切。

 U633687664
U633687664
 U582679646
U5826796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