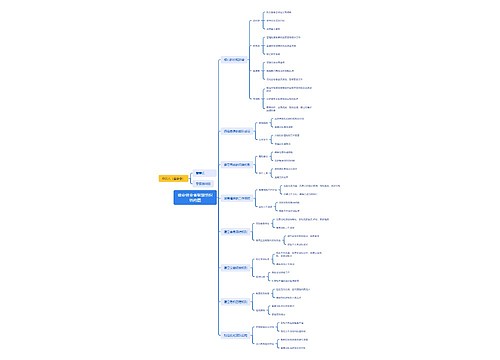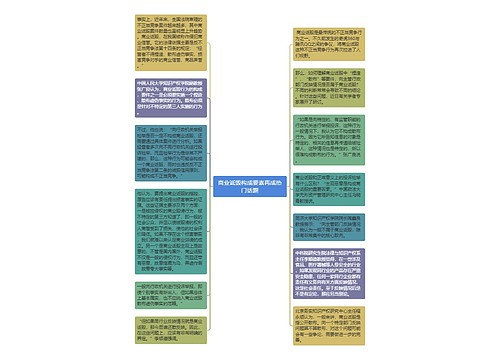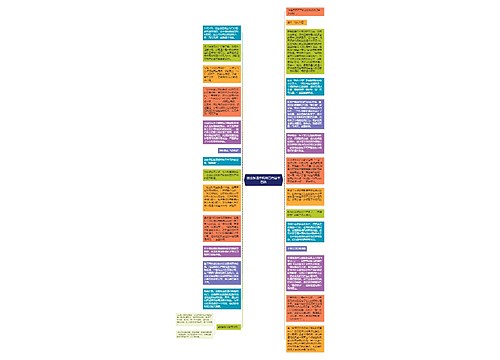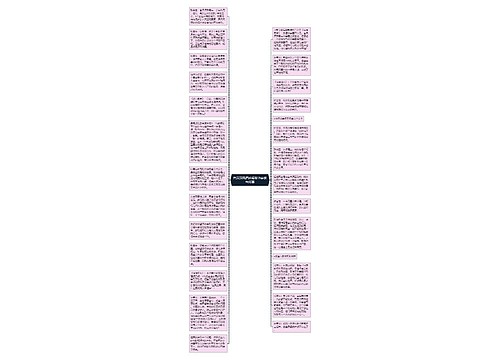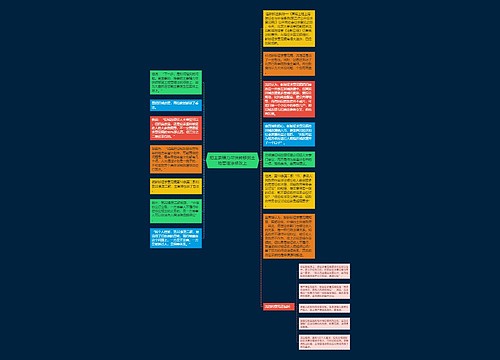近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联合下发《关于加强协调配合积极推进量刑规范化改革的通知》,明确对检察机关全面搜集证据提出要求―――“不但要注重收集各种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罪重的证据,而且要注重收集各种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的证据”。
学者分析认为,这与近年来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错案有关,赵作海、佘祥林等案件的高曝光率,冲击着社会对司法机关的信任底线。而包括对无罪证据在内的涉案证据的全面搜集,正是试图构筑起一道防止错案发生的法律防线。
在赵作海案中,当时对无名尸体进行DNA鉴定,并没有得出确定结果。死者身份不确定,本应作为对赵作海有利的证据,但在定罪时并没有被采纳。
“辩护一方提供的有利于嫌疑人的证据,被侦查机关有意无意地忽视了。”清华大学法学院刑事诉讼法学教授张建伟认为,这并非实务中取证的个例。
全面搜集证据,在我国刑事诉讼法、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中早有明确规定,这次下发的通知,“仅仅是对现行法律的一次重申”。中国人民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刘计划接受《法治周末》记者采访时说。
专家认为,令行禁不止,原因在于现行的考核机制存在缺陷。
曾有媒体报道,某地警方破获一起轮奸案时抓捕了5名嫌疑人,DNA鉴定结果显示这5人并非作案人,但办案警察却隐藏了这一重要证据。原因在于该地派出所每名警察都有指标任务,完成任务的奖励数千元,否则扣发奖金,还将被取消评先进的资格。
北京一名在检察院挂职的学者直言,检察机关中立的追诉角色在实践中很难实现,因为法院的一次无罪判决,在检察系统考评体系中会被记为一次“错案”,检察官及至检察院的“业绩”就会受到影响,因此检察院往往对无罪和罪轻证据不太追求,“甚至有意放过”。
将办案人员的业绩考核直接与破案率、有罪判决率挂钩,后果显而易见,“也是实践中刑讯逼供成为顽疾的重要原因。”张建伟接受《法治周末》记者采访时说。
当今世界各国,作为公诉人一方的检察院,都是代表国家以公共利益为诉求起诉犯罪,因此检察官“负有客观义务”,全面地搜集刑事案件证据即是义务的一项内容。“但检察机关作为控诉机关,自然地带有追诉犯罪的职业倾向,必须对其进行约束。”张建伟介绍。
广东省潮州市中级法院刑事审判庭的一名法官曾进行过调研,发现了同样的现象―――办案人重有罪证据搜集而轻无罪证据搜集。
他举例说,一起抢劫案的被告人按指控罪行可能被判处死刑,但案卷对被告人的身份、年龄均按照其自报处理,法官遍查案卷,也没有发现任何被告人的身份资料。后来庭审过程中发现被告人可能是未成年人,法庭经过调查,证实了该被告人未满18岁。
据了解,在死刑复核程序中,省高级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法院一直都将被告人的身份证据作为一个重点,不少审判人员就是因为发现身份证据存在问题避免错杀而立功。
实践中,其实不乏多搜集一个证据就救人一命的实例。今年6月,江苏省镇江市人民检察院就因为多作了一份司法鉴定避免了一起错案。
谭七一被以涉嫌故意杀人罪移送检察院,随卷移送的司法鉴定认定谭有刑事责任能力。但检察官调查发现,谭在案发前有大量反常举动,于是重新对其作精神病司法鉴定,得出结论:谭作案时处于癫痫精神运动发作期,无责任能力。这份鉴定结论与其他证据印证后被检察院采信,认定谭不负刑事责任,最终撤案。
在刑事案件中对涉案证据的全面搜集,不仅仅是侦查机关、检察机关的义务,“更是对人的生命起码的敬畏”。一位刑法学者如是感慨。
接受《法治周末》记者采访的学者均认为,办案人员的执法理念同样影响证据的搜集。虽然无罪推定、宁纵勿枉等理念屡被提及也深入教育,但学界甚至包括检察系统内部人士也都承认,“知道和做到不是一回事,这些理念并没有真正深入人心,办案过程中还是自觉不自觉地流露体现”。
学界对公检法3家处理刑事案件有一个经典的比喻:作为侦查机关的公安机关、公诉机关的检察机关和审判案件的法院,通过程序的设置,以证据为纽带,三者实质上均被赋予对一起案件审查并纠错的功能,这是一个“跨栏跑”的过程,任何一道“障碍”都有可能发现错误的存在,并最终防止错案的发生。
但实践中,有学者坦言,“这条司法路径已经变形”。在现行的业绩考核和错案追究体制下,形成了利益一盘棋,公检法形成了“立案就能捕,捕了就能诉,诉了就能判”的一场接力赛。
学者认为,如果只是单纯地重申全面搜集证据并不会比以往强调的更有效,“光喊口号没有用”,“应当将对现实冤案的反思反映到制度的改革上”。
这些改革,包括将长期以来呼吁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落到实处,包括对现行考评体系的改进,也包括对违法者的有力制裁……与全面搜集证据一样,都不是新提法,“但需要体现在行动上,需要相关方面下决心”。
全面搜集证据在通知中并不占据很大的篇幅,它也只是整个量刑规范化改革的一环,但没有人能够否认它的意义。
“塑造好的司法人格和形成好的司法传统需要时间,这个过程是不能够一蹴而就的。”张建伟认为。

 U882673919
U882673919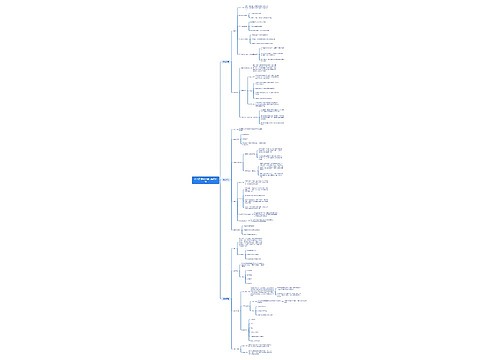
 U781785874
U7817858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