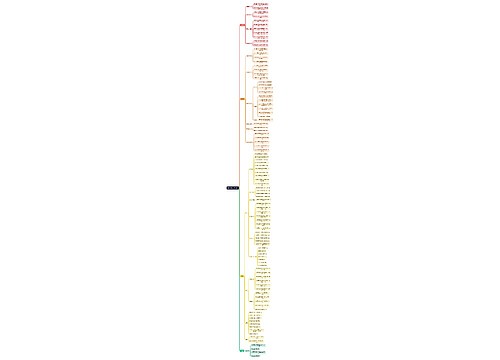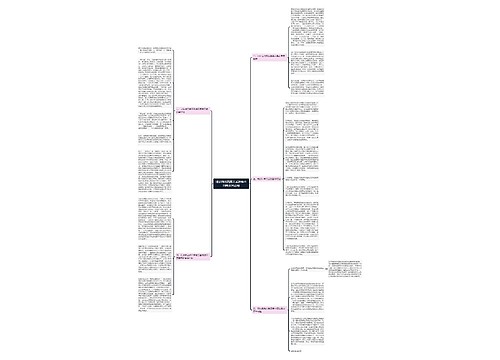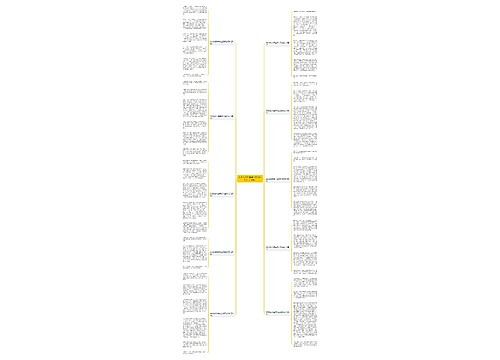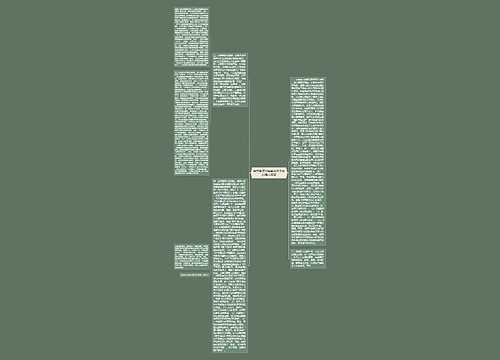犯罪客体属于犯罪性质的范畴,而犯罪客观方面是犯罪构成中物质性外化性的东西,是区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界限的标志和依据。通过比较诈骗罪与诉讼欺诈在行为结构方面的差异,能使我们进一步认清二者间的界限。
第一,行为人实施欺骗行为。诈骗罪的客观要件诸要素中,行为人的欺骗行为当属首要性因素。欺骗行为是使他人陷于错误的行为。在欺骗行为这一客观构成要素上,诈骗罪与诉讼欺诈的行为方式、欺骗程度,表现形式均有所不同。诈骗罪无论形式还是实质都表现为不法,是一种彻头彻尾的不法行为。而诉讼欺诈在表面上却是以合法的、符合民事诉讼的形式进行的,但在实质上却侵害了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和公私财产所有权。诉讼欺诈以合法的形式掩盖实质上的非法行为,更具隐蔽性。
第二,对方产生认识错误。诈骗罪中行为人实施欺骗行为是要让对方陷于错误然后交付财产。对方的错误与行为人的欺骗行为之间必须具有因果关系,同时,在欺骗行为与对方交付财产之间,对方的错误又是必不可少的中介环节,即必须是由于欺骗行为使对方产生错误从而交付财产,才成立诈骗罪。法院的判决基于错误认识而作出,这一命题并不适用于一切诉讼欺诈的场合。就诈骗罪而言,被欺骗者错误的重要意义在于确定欺骗行为和处分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既然在诉讼欺诈中,法院并非一概地陷于错误,那么欺骗行为和处分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也就并非存在于所有的诉讼欺诈场合。因此,将诉讼欺诈定性为诈骗罪的合理性难免会受到质疑。
第三,基于认识错误处分财产。诈骗罪的最突出特点,就是行为人设法使被骗人在认识上产生错误,以致其“自愿地”将自己所有或持有的财物处分给行为人,处分财产是诈骗罪成立的必备条件。处分意思是处分行为的主观要素,其内容是认识到自己的行为是把某种财产转移给他人占有,并根据自己的“自由”意思作出此种决定。在研究财产处分这一问题时,学界存在对“财产处分”和“财产交付”不加区分地交替使用的现象。而实际上“财产处分”和“财产交付”是两个不同的行为且具有不同的意义,二者应当予以区分。笔者认为,诉讼欺诈中的“财产处分”和“财产交付”有别于诈骗罪中的“财产处分”和“财产交付”。多数情况下诈骗罪中的财产处分人与财产交付人是同一的,处分行为与交付行为合二为一,处分意思与交付意思相同,均为“自愿”。少数情况下诈骗罪也存在财产处分人与财产交付人不同一的情形,此时财产交付人或对行为人的欺骗事实全然不知,或者虽知此事实但不知其意义。因此,在诈骗罪中,处分意思和处分行为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交付意思和交付行为不具有独立的意义,其依附于前者、受前者支配且能够被前者的内容所涵盖。因此,仅依被骗人的处分意思和处分行为来认定诈骗罪即可。而在诉讼欺诈中,被害人对行为人虚构事实,伪造证据的情况心知肚明,也明知法院作出的判决是错误的,其无论是基于法院判决而交付财物,还是基于强制执行而交付财物,主观心态必然是非自愿的,而且被害人在法院的错误判决面前并非无能为力,其还享有上诉、申请再审,中止执行等程序性救济权利。如果其能够提出新的证据,还能纠正法院的错误判决。因此,作为财产交付人的被害人,其意志和行为独立于法院的处分意思和处分行为。因而在诉讼欺诈中,我们不能只将目光专注于法院的“财产处分”,而忽视了被害人的“财产交付”。总之,由于在财产处分和财产交付问题上存在较大差异,诉讼欺诈不能构成诈骗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