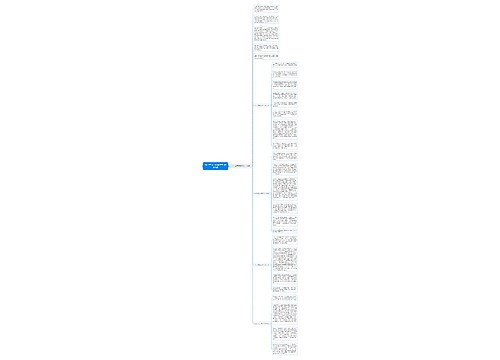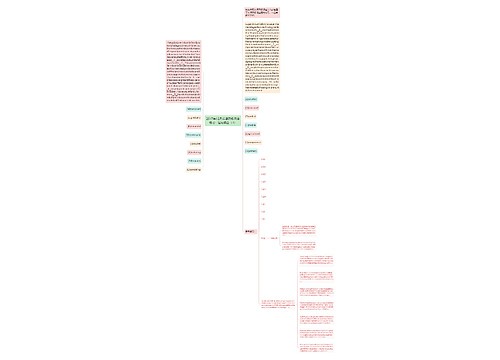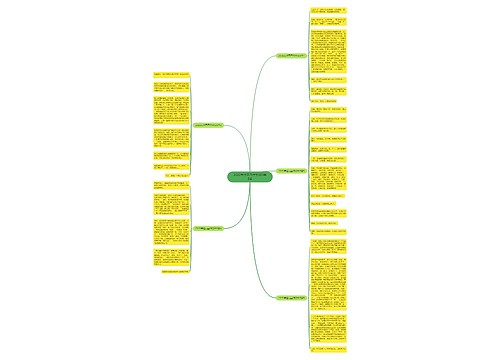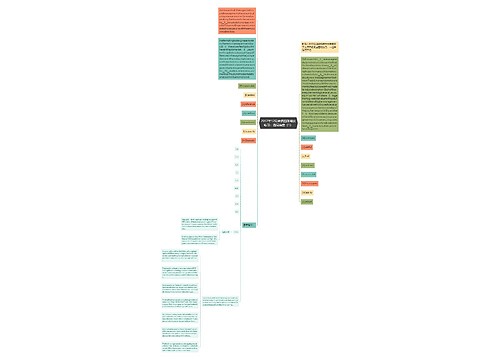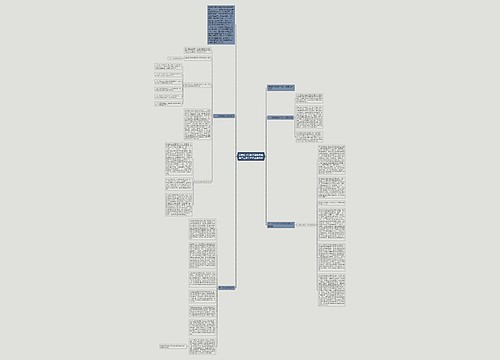比如,20年前的民法学著作将知识产权称为“智力成果权”。而在改称知识产权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大多数学者也都认为,知识产权是与智力成果相关联的权利。但近年来,许多学者对知识产权与智力成果的关联性提出质疑,认为知识产权的一部分领域所关注的并非智力成果,或与智力成果没有直接关系。甚至有人认为,那些将知识产权界定为智力成果权的人根本就不懂什么是知识产权。
再比如,知识产权的“专有性”曾被无可质疑地视为知识产权的特征,但自从民法学家们开始大谈物权之专有性后,知识产权有无专有性似乎都已经成了问题;一些学者虽然仍在讲知识产权的专有性,但从相关文字中或多或少地显示出了一些底气不足,好像占了别人的小便宜又被人发现了一样不好意思。我虽依然认为专有性是知识产权独有的特征,与民法学家们所讲的物权专有毫无关系,因为知识产权的专有性又称“排他性”,指的是相同的标的只允许一个人主张权利;而物权专有则指“一物一权”。但我发现,我的声音并没有引来多少共鸣,反倒像是我在为维护某种私人利益而甘冒天下之大不韪。这让人觉得非常无趣。
总之,作为知识产权学术圈儿里的一员,本人是越来越不敢在理论层面上说话了。在一些场合,我甚至曾明确表示同意一位学者的说法,即“知识产权无理论”。也正因为如此,近两年来,凡听说有谁在研究知识产权理论并撰写专著,我都会致以由衷的敬佩。
最近,上海大学知识产权学院的陶鑫良教授和他的得意弟子袁真富潜心撰写的《知识产权法总论》就要与广大的读者见面了;而在该书交由出版社出版之时,陶鑫良教授盛情邀我为这本凝聚了作者辛苦与智慧的著作作一个序。实话实说,虽然曾经为鼎鼎大名的程永顺法官及年轻有为的江苏省高级法院众法官们的著作写过序,但当2004年3月份接到陶鑫良教授邀我作序的电子邮件之时,我着实有些心里发虚,而且本应该在当月交稿的任务迟迟没有完成。虽然没完成任务的原因很多,但最主要的则是在认真拜读大作之前不敢枉下任何断言。半年多过后,对这部正文40万余字的著作有了一个基本的了解,因而在出版社即将向印刷厂发出付印通知之时,勉力拿出了这份并不十分漂亮的答卷。
首先,我非常佩服陶鑫良教授和袁真富敢于写这样一本书。在我所读过的关于知识产权的中外著作中,还没有哪一部在“总论”层面上下这样大的功夫,用这么大的篇幅。虽然也曾耳闻国内一些学者在尝试撰写知识产权法理学方面的专著,但真正面世的还没有见到。由此可知,陶鑫良教授和袁真富的这部著作无疑是开创性的。当然,我们也许会在不久的将来看到更多的同类著作问世。
其次,这部著作在结构的设计与安排上也与此前出版的知识产权法著作不同,包括绪论、本论与专论三部分,从对知识产权法的整体描述,到对知识产权法律制度中一些核心环节的阐释,再到关于知识产权法发展的几个热门话题的解析,下笔有轻有重,用墨浓淡相间,展现在读者面前的犹如一幅工笔与写意结合的现代水墨画。对于懂得欣赏它的人来说,肯定是值得收藏的。
再次,作者行文之审慎,用语之小心,也是理论性学术著作中少有的。任何一部理论性著作都少不了对他人学说的评头品足;而且通常的理解是,找出别人的漏洞与瑕疵并加以补救,方能显示出本人的聪慧与高明。与此同时,如果一本书中不对同行的观点加以评介,仅仅包含作者自己的表述,又难免学业不精、自说自话之嫌。然而在这部著作中,虽然同样包含了对其他学者观点的比较分析,并且最终给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但文中并没有针对任何个人的贬损性的批评与刻薄的嘲讽。这种绅士般的风范,着实值得吾辈学人推祟与效仿。
应当说,一本书承载及向读者传递之信息量的大小也是衡量其学术价值的重要指标之一。《知识产权法总论》一书无疑是作者在通览了国内现有的相关的知识产权法学专著及有影响的学术论文的基础上撰写完成的,读者可以从中找到国内各种学术观点及标注其来源的脚注。虽然从所占比例上看,本书的脚注量无法与英美法系国家的学术著作相比,但在中国大陆出版的学术著作中,这本书的引文注释及其提供给读者的信息量显然已经非常突出。另外,除了广泛参阅并收录国内外学者的学说外,该书还引述了大量的史料及案例,并对不同国别、不同领域、不同层次的相关法律规范作出了非常细致的评述。不论读者是否能够理解与接受书中反映的观点,其所提供的信息与信息源都是十分难得的。
上面的几段话看上去还是像书评。但这并不是我写这个序言的初衷,只是本人有感而发,信马由缰的写作风格使然。而当把思路拉回到写一个序言应有的轨道上来时,我却又不知道该写些什么啦。考虑到篇幅的限制,索性就此打住。就让这些出自真实感受的闲言碎语作为一段开场的锣鼓,引导读者尽情欣赏后面的好戏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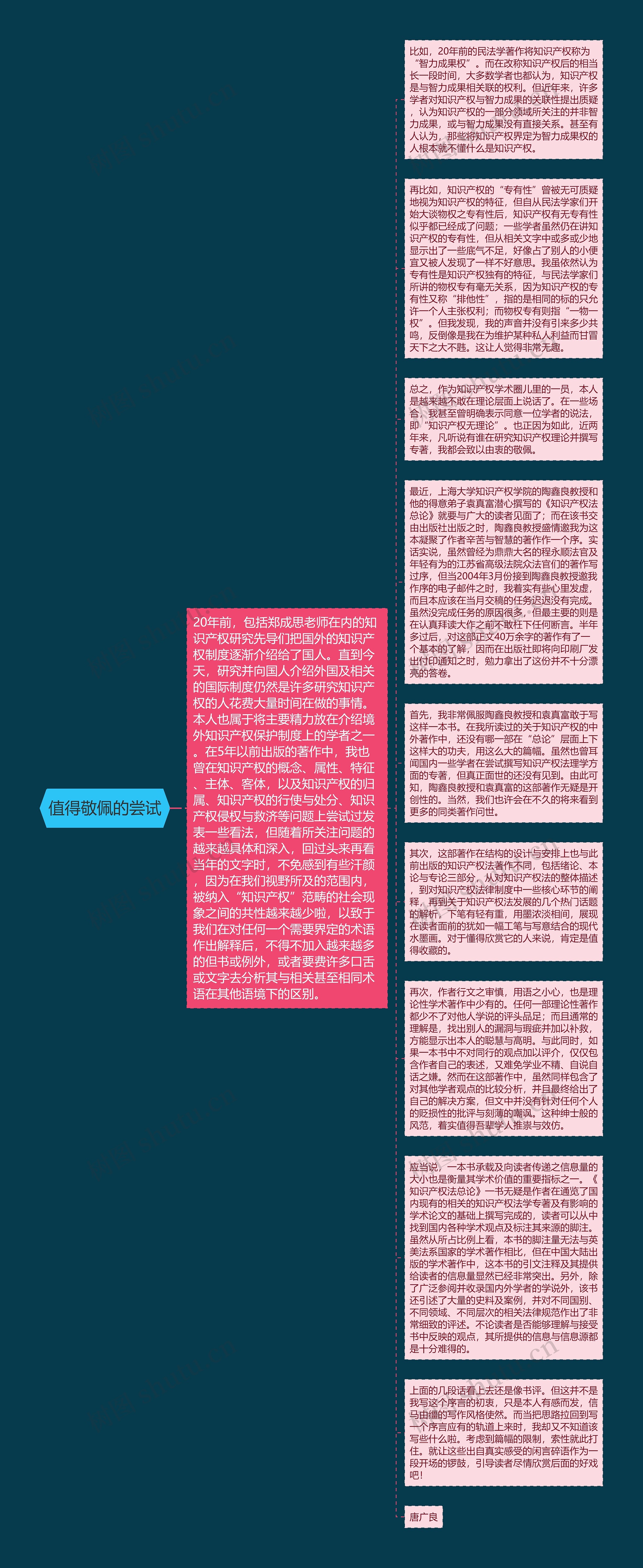
 U633687664
U633687664
 U582679646
U5826796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