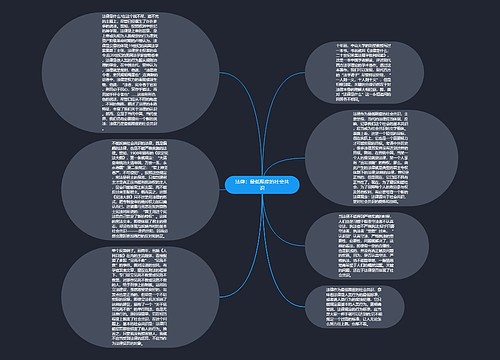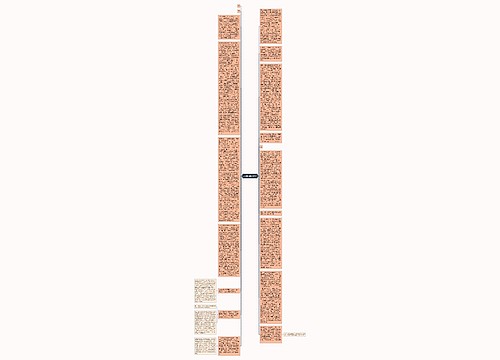媒体与司法关系的重构思维导图
所谓永远
2023-03-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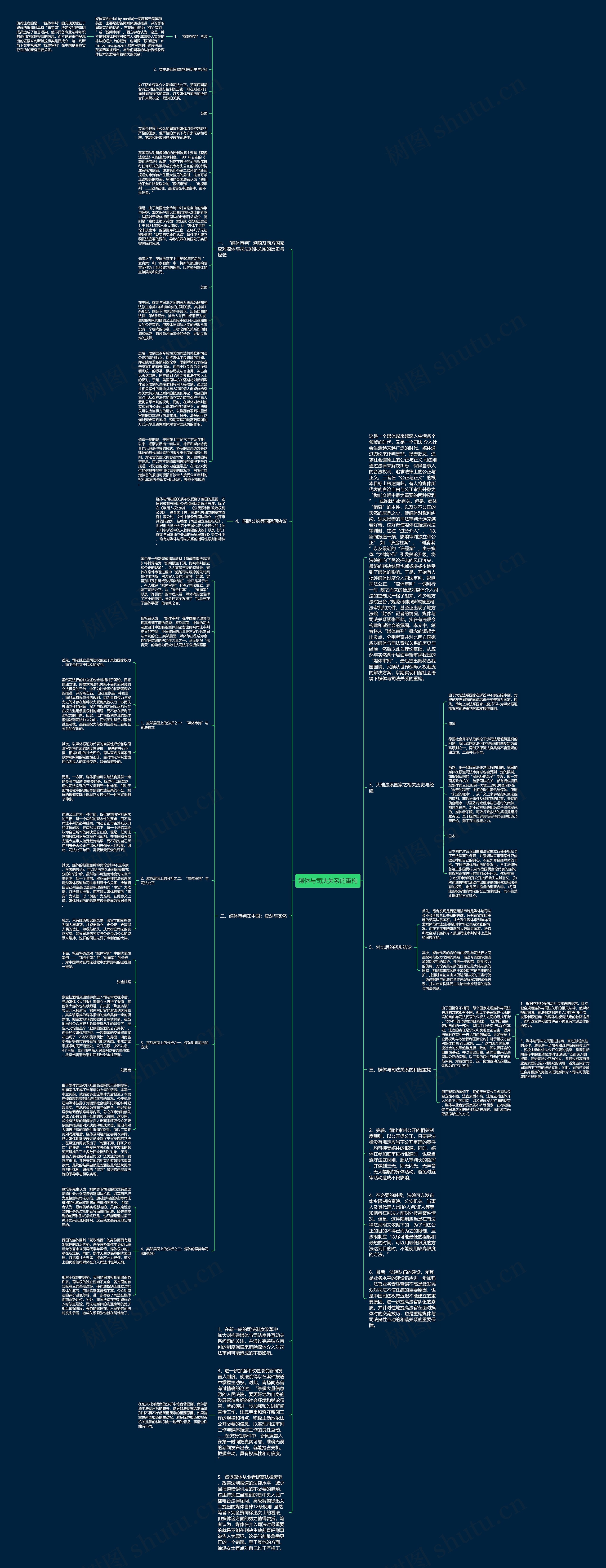
重构
关系
司法
媒体
审判
法官
影响
公正
报道
限制
法律论文
法理学论文
引言
树图思维导图提供《媒体与司法关系的重构》在线思维导图免费制作,点击“编辑”按钮,可对《媒体与司法关系的重构》进行在线思维导图编辑,本思维导图属于思维导图模板主题,文件编号是:c56f9b4e859286504918f99ff6fe2844
思维导图大纲
相关思维导图模版
媒体与司法关系的重构思维导图模板大纲
这是一个媒体越来越深入生活各个领域的时代,又是一个司法 介入社会生活越来越广泛的时代。媒体通过舆论来评判是非,扬善贬恶,追求社会道德上的公正与正义;司法则通过法律来解决纠纷,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利,追求法律上的公正与正义。二者在“公正与正义”的根本目标上殊途同归。有人将媒体所代表的言论自由与公正审判并称为“我们文明中最为重要的两种权利” ,或许就与此有关。但是,媒体“猎奇”的本性,以及对不公正的天然的厌恶之心,使媒体对裁判纠纷、惩恶扬善的司法审判永远充满着好奇。这好奇使媒体在报道司法审判时,往往“过分介入”,“以新闻报道干预、影响审判独立和公正” .如 “张金柱案”、“刘涌案”以及最近的“许霆案”,由于媒体“大肆炒作”引发舆论升级,将法院推向了舆论抨击的风口浪尖,最终的判决结果也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媒体的影响。于是,开始有人批评媒体过度介入司法审判,影响司法公正,“媒体审判”一词风行一时 .随之而来的便是对媒体介入司法的控制又严格了起来,不少地方法院出台了规范(限制)媒体报道司法审判的文件,甚至还出现了地方法院“封杀”记者的情况。媒体与司法关系紧张至此,实在有违现今构建和谐社会的氛围。本文中,笔者将从“媒体审判”概念的源起为出发点,分别考察并对比西方国家应对媒体与司法紧张关系的历史与经验,然后以此为理论基础,从应然与实然两个层面重新审视我国的“媒体审判”,最后提出既符合我国国情、又顺从世界保障人权潮流的解决方案,以期实现和谐社会语境下媒体与司法关系的重构。
一、“媒体审判”溯源及西方国家应对媒体与司法紧张关系的历史与经验
1、“媒体审判”溯源
媒体审判(trial by media)一词源起于美国和英国,主要是指新闻媒体通过报道、评论影响司法审判的现象 ,在我国也称为“媒介审判”或“新闻审判”。西方学者认为,这是一种不依据法律程序对被告人和犯罪嫌疑人实施的非法的道义上的裁判,也叫做“报刊裁判”(trial by newspaper) .媒体审判的问题率先在英美两国被提出,与他们国家的法治传统及媒体技术的发展有着极大的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媒体审判”的实现关键在于媒体的报道对具有“事实审”决定权的陪审团成员造成了信息污染,使不具备专业法律知识的他们以媒体报道的信息,而不是庭审中呈现出的证据来判断指控事实是否成立。这一判断与下文中笔者对“媒体审判”在中国是否真实存在的论断有重要关系。
2、英美法系国家的相关历史与经验
为了防止媒体介入影响司法公正,英美两国都曾有过对媒体进行控制的历史,现在则趋向于通过司法程序的完善,以及媒体与司法的协商合作来解决这一紧张的关系。
英国
英国是世界上公认的司法对媒体监督控制较为严格的国家,但严格的外表下有许多无奈和理解,宽容和开放同样浸透在司法中。
英国司法对新闻舆论的控制依据主要是《藐视法庭法》和报道禁令制度。1981年公布的《藐视法庭法》规定:对正在进行的司法程序进行任何形式的误导或发表有失公正的评论都构成藐视法庭罪。该法第四条第二款还定当新闻报道对审判有产生重大偏见的危时,法官可禁止该报道的发表。早期的英国法官认为“我们绝不允许法院以外的‘报纸审判’、‘电视审判’……必须记住,是法官在审理案件,而不是记者。”
但是,由于英国社会传统中对言论自由的推崇与保护,加之保护言论自由的国际潮流的影响,法院对于媒体报道司法的控制日益减少。特别是“泰晤士报诉英国”案促成《藐视法庭法》于1981年做出重大修改,让“媒体不得评论未决案件”的原则寿终正寝,还将几乎无法被证明的“现实的实质性危险”条件作为成立藐视法庭罪的要件,导致该罪在英国处于实质被废除的境遇。
无奈之下,英国法官在上世纪90年代后的“麦肯案”和“泰勒案”中,将新闻报道影响陪审团作为上诉和改判的理由,以代替对媒体的直接限制和处罚。
美国
在美国,媒体与司法之间的关系表现为联邦宪法修正案第1条和第6条的并列关系。其中第1条规定,国会不得制定剥夺言论、出版自由的法律。第6条规定,被告人有权由犯罪行为发生地的州和地区的公正的陪审团予以迅速和独立的公开审判。但媒体与司法之间的界限从来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二者之间的关系如何协调和规范,有过激烈而漫长的争论,经历过艰难的抉择。
之后,限制言论令成为美国司法机关维护司法公正和审判独立,对抗媒体不良影响的利器。即法院可发布限制议论令,限制媒体发表特定未决案件的有关情况。但由于限制议论令没有明确统一的标准,极容易被法官滥用,冲击言论表达自由,同样遭到了新闻界和法学界人士的反对。于是,美国司法机关逐渐将对新闻媒体议论限制从直接限制转向间接限制,通过禁止相关案件的诉讼参与人和知情人向媒体透露有关案情来阻止媒体的报道和评论,限制的侧重点也从保护法官的独立审判转向保护当事人受到公平审判的权利。同时,在媒体对审判独立和司法公正已经造成危害的情况下,司法机关可以应当事方的请求,以推翻有罪判决重新审理的方式进行司法救济。另外,法院还可以通过变更审判地点、延期审理和隔离陪审团的方式来尽量避免媒体对陪审团成员的影响。
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在上世纪70年代后半期以来,逐渐发展出一套法官、律师和媒体协商合作以解决冲突的模式,协商的结果通常是以建议的形式向法官和记者发出书面的指导性原则。对法官的建议内容通常是:关于案件的特定信息,可以在不影响审判进程的情况下予以报道。对记者的建议内容通常是:在向公众提供的信息并非有用和重要的情况下,对案件特定信息的报道可能损害被告人接受公正审判的权利;或者哪些细节可以报道,哪些不能报道。
3、大陆法系国家之相关历史与经验
由于大陆法系国家在诉讼中不实行陪审制,对舆论左右司法的顾虑远低于英美法系国家,因此,传统上该法系国家一般并不认为媒体报道能够对司法审判构成实质性影响。
德国
德国社会并不认为舆论干涉司法是值得重视的问题,所以德国宪法可以将新闻自由规定为最高原则之一,同时又保障法官具有不容置疑的独立性,二者并行不悖。
当然,出于保障司法正常运行的目的,德国的媒体在报道司法审判时也会受到一定的限制。如根据德国的“资讯拒绝给予”制度,即一方面各政府机关、包括司法机关,都有提供资讯给媒体的义务;但另一方面上述机关也可以在“未定的程序”中拒绝提供资讯给媒体。所谓“未定的程序”,从广义上来讲是指凡属法院的审判,非诉讼事件及检察官的侦查,警察的侦查程序,以至依行政程序法已进行的案件,都包含在内。对于政府机关拒绝给予媒体资讯的,媒体若不服,可依行政救济的渠道提起行政诉讼。至于媒体自辟蹊径获得的信息报道乃至评论,则不在此规定之内。
日本
日本同样对言论自由和法官独立行使职权赋予了宪法层面的保障,并强调法官审理案件只依据法律和自己的良心,不受外界包括媒体的干扰。在对待媒体与司法的关系上,日本法律界普遍主张国民(以及作为国民言论代表的媒体)有权对正在进行的审判公开评论,依据有三: (1)公开审判离开公开批评就失去其意义,(2)对司法机构的活动作出批评是国民依据宪法享有的权利,也是民主监督的重要内容, (3)司法的权威性靠司法的公正性来维持,而不靠禁止批评的方式建立。
4、国际公约等国际间协议
媒体与司法的关系不仅受到了各国的重视,还同时被有关国际公约和国际会议所关注。除了在《欧州人权公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联合国《关于司法机关独立的基本原则》等公约、文件中涉及到司法独立、公开审判的问题外,新德里《司法独立最低标准》、世界刑法学协会第十五届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刑事诉讼中的人权问题的决议》以及《关于媒体与司法独立关系的马德里准则》等文件中,均有对媒体与司法关系的指导性原则和精神。
5、对比后的初步结论
首先,笔者发现是否适用陪审制是媒体与司法会不会形成禁止关系的关键。只有在实施陪审制的英美法系国家,才会发生媒体审判这样引发媒体与司法(主要是刑事司法)关系紧张的情况。而在不实施陪审制的大陆法系国家,法官和社会对于媒体介入报道司法审判总体上是持赞同态度的。
其次,媒体代表的言论自由权利与司法权之间是权利与权力之间的关系,而当今的国际潮流加强对权利的保护,并进一步规范、限制权力的使用。无论英美法系的国家还是大陆法系的国家,都是越来越倾向于加强对言论自由的保护,并通过言论自由来促进司法权的正当行使,通过媒体与司法的合作来缓解双方的紧张关系,并以此来构建民主法治社会应所需的媒体与司法关系。
二、媒体审判在中国:应然与实然
国内第一部新闻传播法教材《新闻传播法教程》将其界定为“新闻报道干预、影响审判独立和公正的现象”,认为其最主要的特征是:媒体在案件审理过程中“超越司法程序抢先对案情作出判断,对涉案人员作出定性、定罪、定量刑以及胜诉或败诉等结论” .也正是基于此,有人批评“媒体审判”干预了司法独立,影响了司法公正。从“张金柱案”、“刘涌案”以及“许霆案”的审理来看,媒体确实也发挥了不小的作用,张金柱甚至发出了“我是死在了媒体手里”的临终之言。
但笔者认为,“媒体审判”在中国是个理想与现实纠缠不清的问题:应然层面,中国的司法制度设计中没有给媒体舆论留出影响司法审判结果的空间,中国媒体的力量也不足以影响司法审判的公正;实然层面,媒体却往往成为案件审理结果的决定性力量之一,甚至扮演“包青天”的角色为民众对抗司法不公提供强援。
1、应然层面上的分析之一:“媒体审判”与司法独立
首先,司法独立是司法权独立于其他国家权力,而不是独立于民众的权利。
虽然司法权的独立还包含着相对于舆论、民意的独立性,即要求司法机关既不受代表民意的立法机关的干涉,也不为社会舆论和新闻媒介的报道、评论所左右。 但这更像是一种宣言,而非具有操作性的规则。因为只有权力与权力之间才存在某种权力受到其他权力干涉而失去独立性的问题,权力与权利之间永远都只存在权力滥用侵害权利的问题,而不存在权利干涉权力的问题。因此,以作为权利体现的媒体报道妨碍司法独立为由,而试图对其予以限制甚至制裁,是有违权力与权利自身及二者相互关系的逻辑的。
其次,以媒体报道为代表的自发性评价和以司法审判为代表的制度性评价 ,是两种并行不悖、相得益彰的社会评价。司法审判是国家用以解决纠纷的制度性设计,而对司法审判发表评论则是人的本性使然,是无法避免的。
而且,一方面,媒体报道可以给法官提供一定的参考与帮助;更重要的是,媒体可以使难以通过司法实现的正义得到另一种伸张。即对于因司法程序的原因导致的司法结果的不公,媒体的报道实际上就是正义通过另一种方式得到了伸张。
2、应然层面上的分析之二:“媒体审判”与司法公正
司法公正作为一种价值,仅仅是司法审判追求的目标,是一个应然的观念性的要求,而不是司法审判的必然结果。司法公正与否涉及认识和评价问题,在应然状态下,每一个法官都会认为自己所作的判决是公正的,但是,任何法官都只能对纷争本身作出裁判,并由国家强制力强令当事人接受裁判结果,而不能对自己所作判决是否公正作出裁判并强令人们接受。因此,司法公正与否,需要接受民众的评判。
其次,媒体的报道和种种舆论(其中不乏专家、学者的言论),可以给法官认识问题提供充分的知识补给,虽然这不可避免地会对法官产生影响,但一个合格、称职而理性的法官理应清楚媒体报道与司法审判是什么关系,应该明白自己判案是以法庭审理查明的“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而不是以媒体报道的“事实”为依据,以“舆论”为准绳。在此意义上说,媒体对司法的影响应该是正面效果居多的。
总之,只有经历舆论的风雨,法官才能变得更为强大与坚韧,才能更独立、更公正,更赢得人民的信任、尊敬与服从,从而树立司法的真正权威。如果司法的独立与公正是以公众的缄默来维持,这样的司法无异于专制者的大棒。
3、实然层面上的分析之一:媒体影响司法的方式
下面,笔者将通过对“媒体审判”中的代表性案例——“张金柱案”和“刘涌案”的分析,对中国媒体在司法过程中发挥影响的过程做一推测。
张金柱案
张金柱酒后交通肇事案进入司法审理程序后,当地媒体《大河报》率先介入进行了报道,其他各大媒体也陆续跟进,在央视“焦点访谈”节目介入报道后,媒体对此案的渲染到达顶峰。其实该案成为媒体报道的焦点具有一定的偶然性,如案发现场的惨象极具煽情价值,在当地当时公众与权力阶层矛盾丛生的背景下,被告人又恰恰是个“肥硕的醉酒的公安局长”。但是经过媒体的热炒,一起简单的交通肇事案却出现了“不杀不能平民愤”的局面,河南省委书记等省市有关领导也相继表态,要求对此事抓紧时间严肃查处,公开见报,决不姑息。4个月后,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交通肇事罪、故意伤害罪数罪并罚判处张金柱死刑。
刘涌案
由于媒体的热炒以及最高法院破天荒的提审,刘涌案几乎成了当年最为火爆的话题。本案一审宣判前,就有诸多主流媒体先后报道了本案在侦查起诉等各阶段和环节的情况,公安机关还向媒体披露了刘涌黑社会组织犯罪的种种犯罪事实、当地官员为其充当保护伞、中纪委领导参与调查该案等等内幕,总之在审判前就先造成了必将其置于死地的舆论氛围。这期间,却没有法院的新闻发言人出面来呼吁公众不要依媒体报道而对未决案件形成确信,更没有对大肆进行着的偏向性报道的限制。所以二审改判刘涌死缓后,媒体及网络舆论会再次沸腾。各大媒体相继发表评论质疑辽宁省高院的判决,甚至还有网友发出了“刘涌不死,则正义必亡”的评论,一些专家学者牵扯其中发表的意见更是成为了大多数民众批判的对象。于是,最高人民法院对受到舆论广泛关注的刘涌一案高度重视,并破天荒地启动审判监督程序提审该案。最终的结果自然是刘涌被最高法院提审并判处死刑,媒体的“审判”最终借由最高法院的领导意志得以实现。
4、实然层面上的分析之二:媒体的强势与司法的弱势
顾培东先生认为,媒体影响司法的方式有通过影响社会公众间接影响司法机构、以其自己行为直接影响司法机构、通过影响能够指导司法机构的机构间接影响司法机构等三类。 但笔者认为,最终能够实现影响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还是通过影响领导而影响司法,顾先生提到的前两种形式最终还是、也只能是通过第三种形式来实现其影响。这在我国是有其现实根源的。
我国的媒体因其“党政喉舌”的身份而具有超出媒体的政治优势,许多官办媒体本身就代表着党政意志来引导民意与舆情,媒体权力的扩张在所难免。同时,媒体天生以民意的代表自居,以揭露社会丑恶、抨击不公为己任,道义上的优势使得媒体在介入司法时坦然无惧。
相对于媒体的强势,我国的司法权却显得弱势许多。司法权的独立性尚不完全,各方面的有实际意义的牵制过多,使司法权缺乏独立对抗媒体的底气。而法官素质普遍不高,公众对司法的评价过低等等,进一步导致了司法在媒体面前弱势地位。另外,我国法院在应对媒体介入时缺乏经验,司法与媒体的沟通协调仍处于相互试探阶段。强势的媒体在介入弱势的司法时发生矛盾,造成关系紧张也就在所难免了。
三、媒体与司法关系的和谐重构
由于国情各不相同,每个国家处理媒体与司法关系的方式都有不同,但无非是在媒体代表的言论自由与司法代表的公权力之间的寻找平衡。1994年的马德里规则指出,“媒体自由是表达自由的一部分,是民主社会实行法治的基础。法官的责任是承认和实现言论自由,适用法律时作有利于言论自由的解释。只能根据《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明示授权才能对媒体自由予以限制。……”这与现今国际主流社会的发展趋势是相一致的,即以保障言论自由为基础,并以言论自由、新闻自由来促进司法公正的实现,以二者的良性互动代替矛盾与冲突。对我国而言,这一良性互动的前景应体现为以下几方面:
1、根据党对加强法治社会建设的要求,建立健全规范媒体与司法关系的相关法律,使媒体报道司法、司法限制媒体介入均能有法可依,被限制报道自由的媒体也能有法定的救济途径,而行政文件和领导讲话不再具有大过法律的约束力。
3、媒体与司法之间通过协商、互动形成良性的合作。法院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闻宣传工作,积极主动地依法公开必要的信息,掌握住新闻宣传中的主动权;媒体则通过广泛而深入的报道,促进司法公正与独立,并通过提高自身业务素质以减少对民众的误导,避免造成针对司法的不正当的舆论氛围。同时,司法还要通过自身程序的完善来抵消媒体介入司法可能造成的不良影响。
但在现实的国情下,我们应当充分考虑司法权独立性不强、法官素质不高、法院应对媒体介入经验不足等因素,以及媒体权力扩张的现实、媒体从业者素质良莠不齐等因素,在构建媒体与司法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时,我们应当采取循序渐进的方式。
1、在新一轮的司法制度改革中,加大对构建媒体与司法良性互动关系问题的关注,并通过完善独立审判的制度保障来消除媒体介入对司法审判可能造成的不良影响。
2、完善、细化审判公开的相关制度规则,以公开促公正,只要是法律没有规定应当不公开审理的案件,均可接受媒体的报道。同时,媒体在参加庭审进行报道时,也应当遵守法庭规则,服从审判长的指挥,并做到三无,即无闪光、无声音、无大幅度的身体活动,避免对庭审活动造成不良影响。
3、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法院新闻发言人制度,使法院得以在案件报道中掌握主动权。对此,肖扬同志曾有过精确的论述:“掌握大量信息源的人民法院,要更好地为自身的发展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和舆论氛围,就必须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闻宣传工作,注意尊重和遵守新闻工作的规律和特点,积极主动地依法公开必要的信息,以实现司法审判工作与媒体报道工作的良性互动。……在突发性事件中,新闻发言人在第一时间把真实可靠、准确无误的新闻发布出去,就能抢占先机,把握主动,具有权威性和可信度。”
在前文对刘涌案的分析中笔者曾提到,案件报道中法院声音的缺失,是导致法院在给刘涌量刑时不得不考虑所谓民意的重要原因。如果能掌握新闻报道的主动权,避免媒体报道被控诉机关提供的材料引向一边倒的情况,事情也许能有不同。
4、在必要的时候,法院可以发布命令限制检察院、公安机关、当事人及其代理人(辩护人)和证人等等知情者在判决之前对外披露案件情况。但是,这种限制应当是在有法律法规明文依据下的,为了司法公正的目的不得已而为之的限制,且该限制应“以尽可能最低的程度和最短的时间,可以用较低限度的方法达到目的时,不能使用较高限度的方法。”
5、督促媒体从业者提高法律素养,改善法制报道的法律水平,减少因报道错误引发的不必要的麻烦。这里特别应当提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法律顾问、高级编辑徐迅女士提出的媒体自律12条规则 .虽然笔者不完全赞同徐迅女士的看法,但媒体这方面的努力值得赞赏。笔者认为,媒体在介入司法时最重要的就是不能在判决生效前直呼刑事被告人为罪犯,这是当前最急需更正的一个错误。至于其他的方面,徐迅女士有点对自己过于严格了。
6、最后,法院队伍的建设,尤其是业务水平的建设仍应进一步加强,法官业务素质普遍不高是激发民众对司法不信任感的重要原因,也是中国司法权威迟迟不能建立的重要原因。进一步提高法官队伍的素质,并针对性地提高法官在面对媒体时的交流技巧,也是重构媒体与司法良性互动的和谐关系的重要保障。
查看更多
904名中国成年人第三磨牙相关知识、态度、行为和病史的横断面调查思维导图
 U633687664
U633687664树图思维导图提供《904名中国成年人第三磨牙相关知识、态度、行为和病史的横断面调查》在线思维导图免费制作,点击“编辑”按钮,可对《904名中国成年人第三磨牙相关知识、态度、行为和病史的横断面调查》进行在线思维导图编辑,本思维导图属于思维导图模板主题,文件编号是:10b9a8a2dd2fb4593f8130ef16c320fc

9.战斗的基督教思维导图
 U582679646
U582679646树图思维导图提供《9.战斗的基督教》在线思维导图免费制作,点击“编辑”按钮,可对《9.战斗的基督教》进行在线思维导图编辑,本思维导图属于思维导图模板主题,文件编号是:33d168acd0cd9f767f809c7a5df86e3a

相似思维导图模版
首页
我的文件
我的团队
个人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