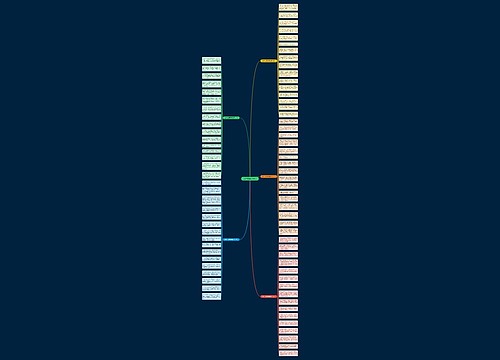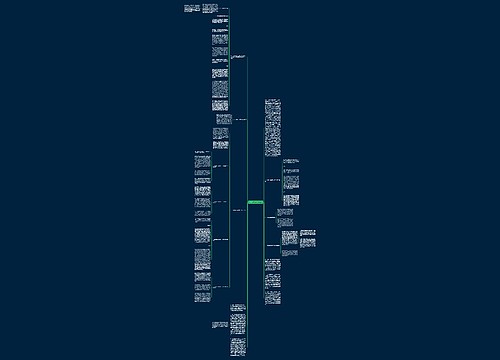十年前,中山大学的刘星教授写过一本书,书名就叫《法律是什么:二十世纪英美法理学批判阅读》,这是一本中国学者解读、评述现代西方法学理论的学术著作。透过这本著作,我们可以发现,现代西方的“法学诸子”尽管持论轩轾,“一人则一义,十人则十义”,但是归根到底,关键的分歧仍然在于对法律本身的理解大相径庭,即,面对“法律是什么”这一永恒追问的回答各不相同。
法律是什么?在这个说不尽、道不完的主题上,尽管已经诞生了许许多多的说法。譬如,按照欧洲中世纪的神学观,法律是上帝的旨意,是上帝或先知为人类规定的行为准则;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卢梭认为,法律是公意的体现;19世纪的英国法学家奥斯丁主张,法律是主权者的命令;在20世纪的美国法学家富勒看来,法律是使人类的行为服从规则治理的事业。在中国古代,管仲认为,法律就是规则,他说:“法律政令者,吏民规矩绳墨也”;在商鞅的论著中,法律是权力的表现或派生物,他说:“法者,宪令著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这些形形色色的说法,尽管已经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侧面,描述了法律的本质特征,丰富了我们关于法律的认识。然而,立足于当代中国、当代世界,我们仍有必要提出一个新的说法:法律乃是最低限度的社会共识。
法律作为最低限度的社会共识,主要是指,当代的法律应当体现、反映、记录我们这个社会的基本共识,应当成为社会共识的文字载体。表面上看,这是一个较低的目标,但在实质上,它也是一个需要努力才可能实现的目标。考诸中外历史,很多法律其实并没有达到这样的目标。譬如,在传统中国,当某一个人的意见就是法律,某一个人享有“言出法随”的特权,那么,由此产生的法律就是典型的君主专权体制下的法律;这样的法律,曾经是正当的,但是现在,它已经不具有正当性了。现在,为了建设和谐社会,为了保障每个人的政治参与权及其他权利,有必要培育一个新的法律观念:法律源出于社会共识,是对社会共识的提炼和总结。
不能反映社会共识的法律,既是偏颇的法律,也是不能严格实施的法律。譬如,1908年颁布的《钦定宪法大纲》,第一条就规定:“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第二条规定:“君上神圣尊严,不可侵犯”。按照这些规定,宪法是君主的意志,只有封建君主才是真正应当握有统治权的主人,议会只能被君主所支配,而不能反过来支配君主。概而言之,这部《宪法大纲》只不过是用法律的形式,把专制皇帝的绝对权力加以确认而已,这就像马克思在批判普鲁士宪法时所说的:“国王用这个宪法给自己钦定了新的特权”。这样的宪法文本,即使体现了君主的意志,却没有体现与反映当时的基本社会共识———走向共和,因而必然会激起更加强烈的反对和抗议。
当法律不能得到严格实施的时候,人们总是习惯于指责守法者不认真守法,执法者不严格执法;似乎只要守法者、执法者“觉悟”过来,“认识到”认真守法、严格执法的重要性、必要性,问题就解决了,这样的看法,即使有一定的合理性,也是肤浅的,并没有真正触及问题的实质。因为,是否认真守法、严格执法,绝不能简单地、一厢情愿地寄希望于人们的幡然觉醒。关键的问题,还在于法律是否体现了社会共识。
举个反面例子。前两年,包括《人民日报》在内的主流媒体,连续报道了多起“见死不救”、“见危不救”的事件。面对冷漠的世风,有学者发表文章,建议在刑法的框架下,专门设立见死不救罪或见危不救罪,对那些见死不救或见危不救的人,给予刑事上的制裁。这样的立法建设,虽然愿望是良好的,出发点也是正当的,但却是一个不切实际的设想,即使立法机关采纳了这样的建议,颁布了一个“关于惩罚见死不救”的单行刑法,也是无法推行的。原因很简单,它在相当程度上脱离了社会共识,在这个问题上,基本的社会共识是:法律只能惩罚那些损害了他人的行为。换言之,只要我没有损害别人,我就不应当受到法律的惩罚,不应当作为法律惩罚的对象。
法律作为最低限度的社会共识,意味着法律是人类行为的最低标准,或者说人类行为的底线伦理,它只能规定最基本的人类行为。更明确地说,法律规定的行为标准,应当是大家一伸手就可以达到的;它不能规定一个过高的标准,让人无论怎么努力往上跳,也够不着。

 U633687664
U633687664
 U582679646
U5826796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