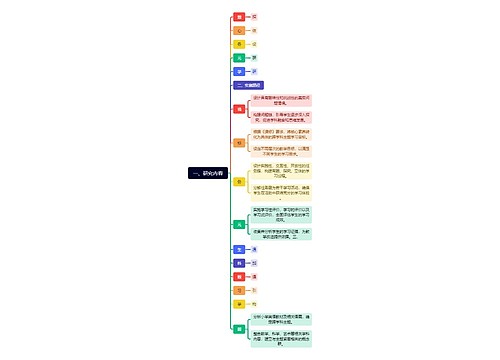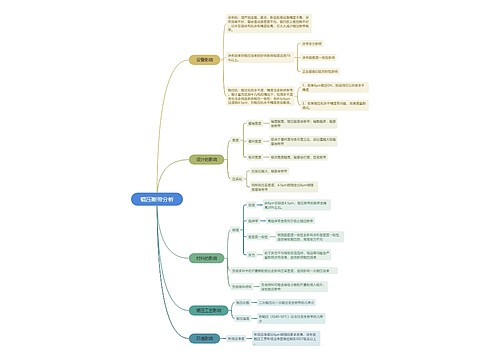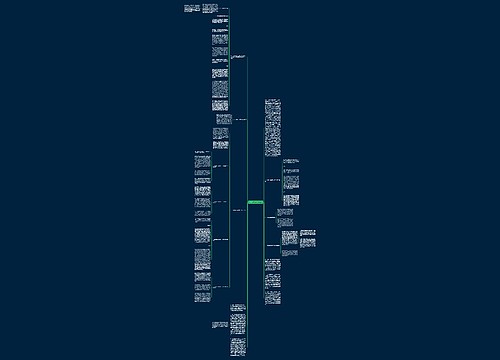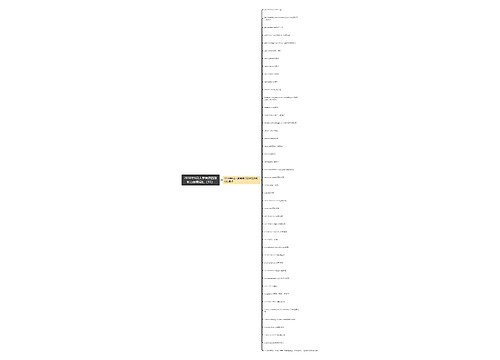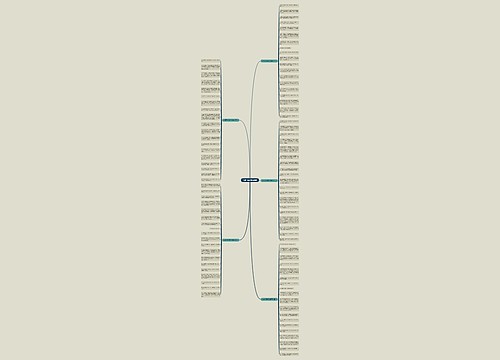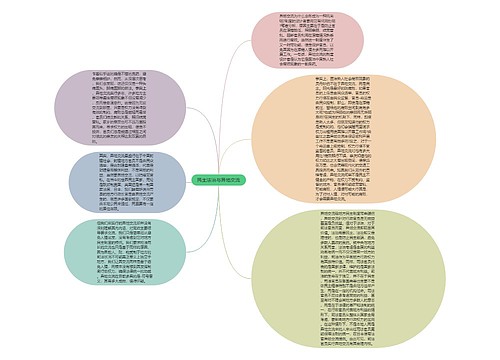正如模糊数学不是让数学放弃它的精确性,使数学变得模模糊糊,而是用定量的数学 方法去处理具有模糊性的现象,从模糊性中寻求确定的信息,①(注:参见《模糊系统 与数学》1987年第1期之《发刊词》。)研究法的模糊性,也并不是要否定法的明确性, 去追求模糊,“而是在法律的确定性中寻求不确定,在不确定中寻求确定性”②(注: 葛洪义、陈年冰:《法的普遍性、确定性、合理性辨析》,载《法学研究》1997年第5 期。)也即试图通过引入模糊数学的思维方法,从多学科角度去认识和利用模糊性,克 服不必要的、消极的模糊,达到和接近确定性,以实现立法的准确客观和执法的合理公 正,从技术层面上推进中国的法治化进程。
在国内,一些学者在探讨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成文法的局限性、法律漏洞、法院错案 责任制及法律解释等问题时,直接或间接地触摸到了法的模糊性,但亦比较零散、感性 .本文试图从法的技术特征层面对法的模糊性从整体上作一专门的初步描述。
模糊,通常是指意思含混不清、态度不明朗,故在中文语境中带有贬义倾向。所以, 可以想象,笔者提出建立一门模糊法学,正如上文已经提到的那样,很容易招致诸多不 加思索的非议。作为一个专有学术用语,模糊(Fuzzy)意指“界限不分明”。而模糊性 ,在《辞海》中是被这样定义的:指事物所具有的归属不完全的属性,表示事物属性量 的不确定性。模糊性这一概念的本原意义源自模糊数学,出自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札德 (L·Zaden)教授提出的模糊集理论。在传统的二值逻辑看来,一个事物要么属于集合A ,要么属于非A,不存在既是A又是非A的情况,对于这类界限分明的对象经典数学可以 对其进行处理,使其量化、精确化。但是,现实世界中还有大量的客体是没有明确界限 的,存在大量的既是A又是非A的排中律破缺现象。例如,“高”和“矮”之间,“轻” 和“重”之间即不存在截然分明的界限。札德指出:“这种不能精确划定范围的‘类别 ’,在人的思维中,特别是在模式识别、信息传递和抽象中都起着很重要的作用”。⑨ (注:转引自伍铁平:《模糊语言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34页。)经典 数学无法处理人类这种模糊思维。模糊集理论突破经典集合限制,建立模糊子集,模仿 人脑的模糊思维过程,逐步实现了用数学方法对模糊现象进行模糊度量、模糊识别、模 糊推理、模糊控制和模糊决策。
自札德教授于1965年发表“Fuzzy Sets”(模糊系统)一文以后,模糊数学作为一门新 的数学学科在短短的不到40年的时间里得到了飞速的发展,极大地推动了人工智能技术 的发展,实际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在语言学、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等人文社会 科学中,模糊集理论亦得到推广和应用。人们应用模糊数学可以处理经典数学无法解决 的人文科学中大量的模糊现象和模糊概念。模糊数学为人们提供了对事物模糊属性的精 确认识。
一般认为法的明确性是法的本质属性,但法同样具有模糊特质,而且我们将在下文中 看到,法的模糊性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这是康德二律背反原理在法律王国的印证。
法的模糊性是法的一种不确定性,是法的类属边界和性态的不确定性。而法的不确定 性除了指法律概念的边界(外延)不确定外,还包括法的不稳定性、歧义性、含混性等等 ,二者之间是属种关系。在一些探讨法的不确定性、法的局限性、法律漏洞的论著当中 ,都或多或少地提到了法的模糊性。如梁慧星先生认为“可将法律漏洞定义为,现行法 体系上存在影响法律功能,且违反立法意图的不完全性”,“所谓不完全性,是指现行 法上欠缺当前事态所必要的规范,或规范不完全或有补充必要”,开放的不确定概念的 特征“在于其具有开放性,即其可能的文义不足以确定其外延”。(11)(注:梁慧星: 《民法解释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51、253页。)这里面蕴含了本文 关于“法律的模糊性是指法律所具有的归属不完全的属性”这样一层含义。而英国学者 哈特在他的巨著《法律的概念》中反复强调,法律的不确定性仅存在于涉及词汇边缘含 义的疑难案件,而法律概念的核心意义都是明确的。而模糊理论一再强调“模糊概念出 现在概念的边缘区域;在中心区域,概念的区别往往是清楚的”。(12)(注:伍铁平: 《模糊语言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88页。)可能哈特先生自己也没想 到自己对法的不确定性的认识会与模糊理论如此貌合神同。但是,这些论著都不是基于 模糊集理论而提出法的模糊性,而是一种不自觉的发现。因此,他们对法的模糊性的认 识必然会产生偏差,与法的其他不确定性相混淆。例如徐国栋先生在他的得意之作中分 析法律的局限性时,虽然指出了法律具有模糊性,但他所说的这种模糊性恰恰不是模糊 集理论所指的那种模糊性,不是概念外延的不确定性。而他所说的法律的另三种局限性 :不合目的性、不周延性、滞后性,综合起来恰恰是模糊数学意义上的模糊性。(13)( 注:徐国栋:《民法基本原则解释——成文法局限性之克服》,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 92年版,第139—143页。)
马克思说:“法律是肯定的、明确的、普遍的规范”,(15)(注:《马恩全集》第1卷,第71页。)法的对象永远是普遍的,它绝不考虑个别的人及个别的行为“。(16)(注: 卢梭:《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50页。)法律从来只对它所调整的社 会关系作普遍的规定,它反映社会成员的共同要求,是对个体共性的一般抽象和提炼, 不考虑具体的、个别的、特殊的情况。”法对于特殊性始终是漠不关心的“,(17)(注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58页。)法为了普遍正义的实现 不得不牺牲个别正义。而法的适用、实施又是一个将这些抽象、普遍的规则应用到活生 生的具体法律事实当中的过程。现实生活是千差万别的,人们发现总是难以找到与具体 个案能够准确对应无误的法条。执法者总是感到法律不够用,不够具体、详细。目前, 我国立法主义盛行,某种程度上即反映了这种社会心态,人们总是感到法不够用,很多 地方缺乏”游戏规则“,总是不断地呼吁立法,人大会议上立法议案一年比一年多。事 实上,法律规定与它所调整的对象之间不是一一对应关系,前者不能完整无误地将后者 不留空隙地扣合在自己的集合之内,二者之间的边界总是模糊的。尤其是在哈特所指的 疑难案件中,案件是否属于所对应条款的集合之内,有时很难判定。例如,我国新刑法 将1979年刑法当中的”拐卖人口罪“修改为”拐卖妇女儿童罪“。应该说”妇女“这一 概念的意思是非常清楚的,但在《羊城晚报》1999年12月9日报道的一个案例中却是模 糊的。四川一人贩子将一女青年卖给一安徽人,而买主同居时发现买来的妻子是两性人 .案发后,人贩子辩称他拐卖的不是妇女,不构成犯罪。两性人是不是新刑法所指的” 妇女“,明确的概念在边缘情况下模糊起来了。
克服法的模糊性,我们不能通过繁琐、细密的立法来实现,“绝大多数立法历史表明,立法机关并不能预见法官所可能遇到的问题”。(19)(注:(美)梅里曼:《大陆法系 》,知识出版社1984年版,第50页。)一旦通过立法的方式解决了法的模糊性缺陷,法 的普遍性也将因此丧失殆尽,结果是针对每一具体行为都有一套相应的法律,那时,人 们将如同生活在牢笼中一样。解决法的模糊性问题,现有的办法:一是加强法律解释工 作;二是提高法官素质并引进判例制度,创造性地运用法律。但是,“人们寄以厚望的 所谓解释理论和方法都不像人们想像的那样可以信赖,人类发现的一个又一个似乎日益 完美的解释法律的方法并没有取得多大的进展。不仅其中任何一个都不可能充分有效, 而且其加总也无法构成一套方法”,“我们无法在逻辑层面或分析层面上提出一种完美 的法律文本的解释方法,无法用一种没有内在矛盾和冲突的语言文字表述出来”。(20) (注:苏力:《解释的难题:对几种法律文本解释方法的追问》,载梁治平编《法律解 释问题》,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58—61页。)而通过提高法官素质更不可能彻底解 决问题。有没有更为快捷有效的方法呢?
以上例举的法的模糊性现象都可以看成是一种集合——模糊数学所要研究的模糊集合。模糊数学经常使用“高个子”这样一个典型例子来说明经典数学无法处理的模糊现象 和概念(到底1米几才算高个子?这是不确定的,高个子和矮个子之间是没有明确界限的) ,说明模糊数学可以将数学导向传统数学无法问津的模糊性领域。刑法中的罪轻与罪重 问题以及民法、行政法、经济法中的法律责任轻重问题与模糊数学中的“高个子”问题 ,二者是性质毫无二致的模糊概念,完全相通。既然札德可以对“高个子”这样一类模 糊性概念用建立模糊集合的办法实现对其定量化分析,使计算机也能像人脑一样对模糊 概念进行识别与测量。由此推理,法的模糊性问题(单维模糊)也可以用同样的方法实现 其定量化分析。那么,很多法律概念就都可以用模糊数学的方法实现其定量化。如果这 种推理成立的话,法官们就再也不会为“某人行为是属于情节严重还是特别严重”、“ 商标近似还是不近似”之类的问题而大伤脑筋了,因为只要将有关数据输入能够进行模 糊测度的计算机,马上就会得出结论。
看来,前人关于用机器来审判的设想并非不切实际的空想!
法的模糊性除呈现为法的基本技术特征外,还呈现在多重层面上:
(一)法律语言的模糊性。由于受语言分析哲学高度发达的影响,二战以后,西方法学 界完成了法学的语言学转向,法与语言的关系的探讨已成为近20年来法理学界谈论的主 题话语,且有不少高水平的研究成果。(23)(注:舒国莹:《面临机遇与选择的中国法 理学》,载《法学》1995年第9期。)在美国,各级法院甚至开始用词典作为一种审理案 件的辅助工具,对法律进行文义解释。(24)(注:参见陈金钊、尹绪州:《法律的文义 解释与词典的使用——对美国司法过程中词典使用的述评》,载《法商研究》1996年第 3期。)哈特对法的模糊性的分析采用的就是语言分析方法。前面提到的G·皮勒亦是如 此。由于语言是法律的载体,文义解释是法律解释的一种最主要方法,因此,法理学界 历来比较关注法律语言的不确定性。
所以,法律条文往往无法准确传递立法者的本意,词不达意的现象在法律文本中是不 难发现的。法律条文的中心语义一般来讲是明确的,例如前面提到的“拐卖妇女儿童” ,其中妇女一词的含义是非常清楚的,甚至不需要解释。但一旦遇到特殊情况,在它的 边际上其含义却会发生模糊现象。例如两性人的出现,便会使男人与女人的界限开始模 糊。由于存在既是A又是非A这样的模糊现象,同一法律条文有时在不同的地点或不同的 法官那里,有时甚至在同一法官那里会出现大相径庭的理解与运用。例如,对于王海是 不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所保护的消费者,人们的理解就大相径庭,以致不同法院甚 至同一法院在不同时期对大体相同的案件作出了完全相反的判决。在有的法院,王海被 认定为消费者,而在另一些法院王海却不是消费者。当代中国之所以会形成这一奇特的 法律现象,正是由于“消费者”这一法律概念的边界模糊(尽管它的核心含义是非常清 楚的),立法者万万没相到会出现既是“消费者”又是“非消费者”的王海们。
(二)法律裁判的模糊性。法律裁判(包括行政裁决、仲裁裁决、司法裁判,这里主要以 司法裁判为例)的模糊性又体现为三个方面:
第一,如前述,裁判所引用的法律本身就是模糊的,即法律推理的大前提模糊。
第二,裁判所依据的案件事实是模糊的,即法律推理的小前提模糊。法院判决乃是以 事实为依据,故传统的诉讼法学认为,可以通过收集证据恢复案件事实的本来面目,据 此法院可以准确作出判决。但事实上,我们不可能采集到反映事实全貌的全部证据,有 的甚至根本无法获取证据。我们无法“让时间倒流”,重现事实真相,我们认识到的案 件事实永远只是真相的一部分,事实本身对我们来说永远是模糊的。可能正是因为这个 缘故,有的历史学家认为从来就没有真正的历史。“我们过去的诉讼制度和诉讼理论要 求法院查明案件的‘事实真相’,不仅是一种浪漫的、不切实际的幻想,而且不符合诉 讼活动的内在规律,违背了诉讼法的有关规定。”(26)(注:丁以升:《论司法判决的 不确定性》,载《现代法学》1999年第1期。)
第三、裁判结果具有模糊性,即法律推理结论的不确定性。一般认为每一个具体案件 相应地只有一个唯一正确的判决。而事实上,一个案件的判决往往有多项选择,答案并 不是唯一的。判决结论的这种模糊性(多样性、不确定性)会产生这样一种困境:某一案 件可以作出若干个正确的判决(A、B、C……),假如一审作出A判决,二审作出B判决, 再审作出了C判决,能够说A和B都是错判吗?这种现象实际经常发生,例如,某区法院对 某少年轻微犯罪行为判处有期徒刑一年,而二审法院却改判为有期徒刑两年缓期三年执 行。正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那样,错案责任制是不合理的。(27)(注:参见王晨光:《 从“错案追究制”谈法律运行中的不确定性》,载梁治平编:《法律解释问题》,法律 出版社1998年版。)更有价值的疑问是:二审、再审改判是必要和合理的吗?这样,我们 有必要将错案责任制改造成为限制改判制度,禁止对已经作出的正确的判决作出改判, 从而减少当事人的任意上诉、申诉,减轻当事人的讼累;抑制任意改判,减少司法腐败 ;节约司法制度运行成本。
(三)法与道德界限的模糊性。这是一个古老而新鲜的话题。说古老,是因为法从产生 开始,道德就与其纠缠不清,千百年来,不知有多少先哲先知在二者的关系问题上耗费 了宝贵的心血。说新鲜,是指后继者们总能从这个无底洞中挖掘出新的货色。而本文也 正是从一个新的角度,用模糊理论来认识二者关系的。
法与道德的界限从来就是模糊的,二者之间从来没有一条明确的边界。道德可以入法,成为对社会成员的强制;法也可能成为道德,成为人们的内心操守。一项规则可能既 是一种法律强制,也是一项道德要求,亦此亦彼的现象在法律与道德之二元世界里非常 普遍。法律与道德之间交叉重合的部份非常大。但是,即便二者之间的边界无法确定, 我们也必须对二者作用的领域有所界定。任意把道德要求纳入法律强制中,会有可能侵 犯个人人权;而把法律要求降格为道德制约,则又可能引起社会混乱。
(四)部门法中的模糊性。民法、刑法、经济法、行政法等部门法中还存在大量的模糊 性现象。如经济法与行政法界限的模糊性、企业法中国企产权的模糊性、民法中民事权 利的模糊性等等。部门法中的模糊性问题具有极大的实践价值和理论价值,有待我们深 入、广泛地研究。
总之,法永远是模糊的,法的模糊性是其绝对属性,而法的明确性则只在相对意义上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