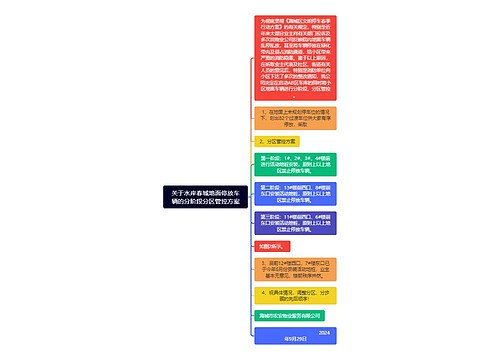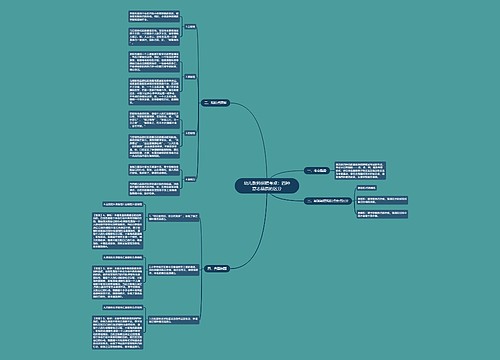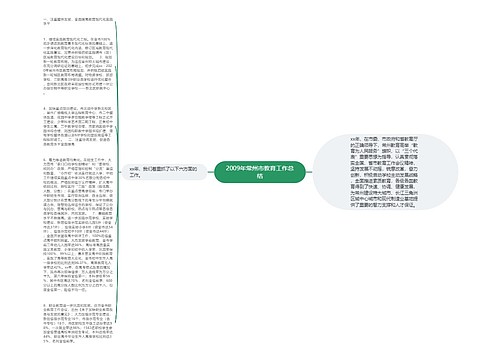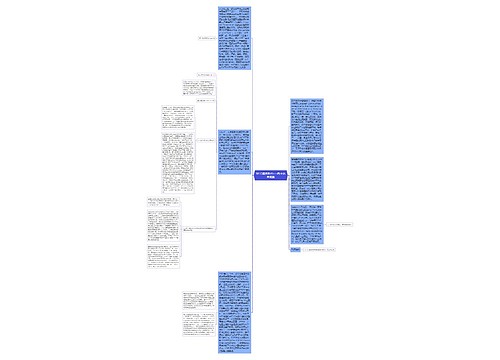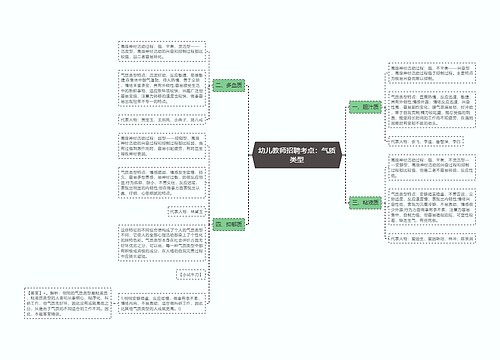在本案中,首先涉及的是对美国具体承诺表的解释。在以前的或与本案同步进行的涉及GATS的争端中, 也曾涉及了具体承诺表的解释问题,但都远没有本案所涉及的问题复杂。虽然本案上诉机构维持了专家组的关于“美国对赌博服务做出了具体承诺”的结论,但纠正了很多专家组所运用的条约解释方法方面的错误。
根据上诉机构的分析,对于如何确定包括具体承诺表中的条款和条目的含义,应该注意下列问题:
第一,在确定具体承诺表中的条款和条目的“通常含义”时,可以援引和参照词典中对相关措词的定义,但不应将该方法作为唯一的方法。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词典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归纳词语的所有含义,无论该含义是普通的还是罕见的,是通用的还是专用的。在这种情况下,往往可能出现一个两难的问题:在常用词典中对某一措词的含义的界定,既支持起诉方的主张,也支持被诉方的主张。这时,更需要对词典含义持谨慎保留态度,并需要进一步运用其他解释方法来确定相关措词的正确含义。
第三,在解释具体承诺表时经常会援引的两个参考文件(具体承诺表指南和第W/120号文件)以及这些文件所“连接”的联合国核心产品分类(以下简称CPC)的法律地位应该是“补充手段”而不是“上下文”。在本案中,上诉机构的最终结论和专家组的结论一样,即“美国具体承诺表第10.D分部门包含对赌博服务的具体承诺”,而上诉机构做出这一结论,也是参照CPC而得出。但是,与专家组不同,上诉机构不是将具体承诺表指南和第W/120号文件以及CPC作为解释具体承诺表的“上下文”或“后续惯例”,而是将其界定为“补充手段”。有人也许会问,既然结果一样,有什么必要对有关文件是上下文还是补充手段做这么严格的区分呢?我们认为,这不是上诉机构为彰显其“高明”而“多此一举”,而是在审慎的政策考虑和严密的法律思考基础上的“明智之举”。
本案中,具体承诺表是各成员之间的条约,对其解释即为对条约的解释。所谓条约的解释,是指对条约的整体、个别条款或词句的意义、内容和适用条件所作的说明,其目的在于明确条约含混不清或模棱两可的地方,从而有利于条约的善意履行。在执行条约的实践中,当事国往往由于对条约约文的含义理解不同而产生分歧和纷争,致使条约无法执行,所以就产生了条约的解释问题。1969年《条约法公约》制定时,国际法学界存在着三种条约解释方法的主张:第一种是“主观解释”或“意图说”,强调考察准备资料来确定条约谈判者的实际意图;第二种是“约文说”,强调按照条约约文的含义来进行解释;第三种是“方法说”,强调按照条约的“宗旨和目的”进行解释。不同的方法可能导致相似的结论,但也可能导致完全不同的结果。1969年《条约法公约》基本上采用了“约文解释方法”,但也采纳了其他学说中的合理因素,最终形成了《条约法公约》第31条和第32条。
按照《条约法公约》第31条“解释的通则”中包含的解释规则,对条约条款的解释应该先分析其条文,即“条约应依其用语按其上下文并参照条约之宗旨和目的所具有的通常含义善意地加以解释”。在考察上下文时,应当考察条约的整体规定以及条约的后续惯例。条约法公约第31条的标题为“general rule of interpretation” 而不是“general rules”,按照国际法委员会的起草意见,这是为了表明在第31条中列明的解释方法是一个整体方法,而不是相互独立的方法。 相应地,在第31条中所涉及的有关文件(条文本身、上下文、后续惯例、条约整体)在解释中具有相同等级的法律地位。而《条约法公约》第32条“解释的补充手段”(supplementary means of interpretation)规定了可以运用考察条约的准备资料和条约缔约时的背景,但其作用仅在于两个:一是“证实”根据第31条解释规则获得的条文含义;二是在第31条规定的解释方法不足以确定相关条约条文的正确意义时,“确定”条文含义。可以说,在第31条和第32条之间存在着解释效力和顺序方面的等级,相应地,在第31条和第32条中所涉及的文件(后者涉及准备工作等)也具有效力层次的差别。
尽管本案中所涉及的具体承诺表指南和W/120号文件及CPC对于澄清具体承诺表的条目,特别是部门和分部门涵盖的服务类别的问题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但毕竟这些文件本身不是WTO“适用协议”的一部分,具体承诺表等文件甚至不具有法律约束力。按照上述关于《条约法公约》第31条的分析,如果在本案中,将相关文件(具体承诺表指南和W/120号文件及CPC)作为“上下文”来解释具体承诺表,就会引发一个现实的矛盾:相关文件不是WTO适用协议甚至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但由于它们是上下文,因此作为解释渊源与WTO适用协议的效力等级相同,其实际效果就会使其法律效力“上升”,等同于GATS及其具体承诺表的效力。进一步来说,如果将相关文件当作上下文,还存在着下列问题:如果相关文件不是对GATS及其具体承诺表的“印证”或“具体表述”,而是存在矛盾和冲突,那么在解释上,采取哪一文件的规定才是正确含义?如果采取相关文件的含义,那么,一个不是WTO协议的甚至不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件的法律效力却要高于GATS及其具体承诺表,这在法律上是矛盾的,也是WTO争端解决机制和WTO成员所难以接受的。
将相关文件作为上下文的做法,还可能会对WTO法律体系的确定性产生负面后果。WTO将其法律体系看作“自成一体的”(self-contained),WTO协议和法律规则应经过谈判、修正、解释等严格的法定程序而形成,如果将相关文件作为与GATS及其具体承诺表同一级的解释来源,那么,会不会不适当地扩展WTO协议的法律框架或混淆规则之间的界限和等级?另一个国际组织制定的文件(如联合国制定的核心产品分类)作为与GATS及其具体承诺表同一级的解释渊源,WTO的“自成一体的”法律体系会不会受到侵蚀?推而广之,多边环境条约、国际人权条约以及国际劳工组织制定的核心劳工标准,是否可以作为解释WTO协议的“上下文”进而与WTO协议的条文具有相同的法律效力?
显然,将不属于WTO协议的甚至不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相关文件作为上下文的做法,存在着诸多问题,在实践中可能引发极大的争议,而这些显然是WTO上诉机构在目前所不愿直接面对的。相反,将其作为“补充手段”,用考察补充文件来“证实”或“确定”对条文通常含义的理解,就是一种相对“合理”和“安全”的解释方法。
最后,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在对具体承诺表的解释中,强调条约解释应依据缔约国的“共同意图”(common intent)。专家组和上诉机构的法律分析方法本无可非议,但是,它们似乎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事实:美国制定GATS具体承诺表是在乌拉圭回合期间,即20世纪90年代早期,而当时网络赌博服务正处于萌芽状态,美国政府当时无法预见到网络赌博在后来发展如此迅猛并进而会危害其社会安全的情况,因此,其谈判代表在具体承诺表有关条目中并没有明文将赌博或网络赌博服务从其承诺中排除。但是,这并不必然意味着美国同意开放网络赌博服务。专家组和上诉机构报告强调“共同意图”的严格解释,防止了相关成员对具体承诺表的单边任意解释,强化了具体承诺和GATS的义务的法律效力,但是,如果在强调共同意图的同时却忽视了当事国本身的意图,似乎也会对当事国产生无法预见的义务。

 U249128194
U249128194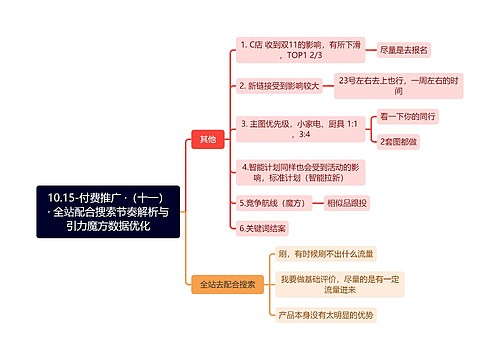
 U882214155
U8822141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