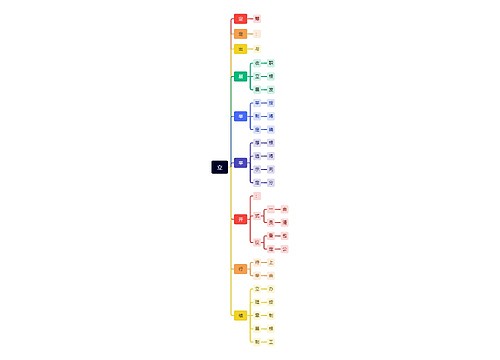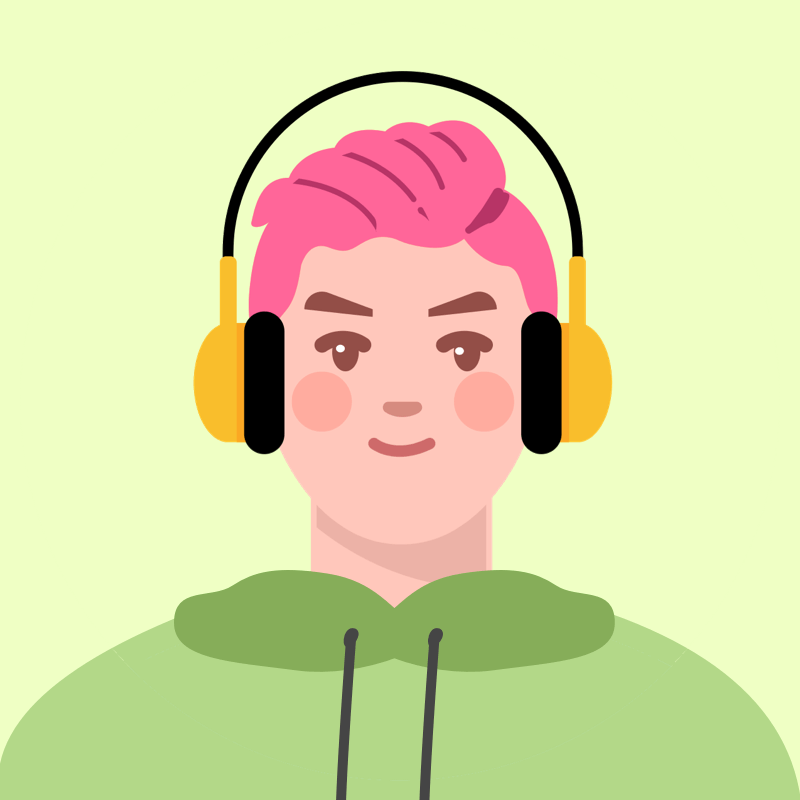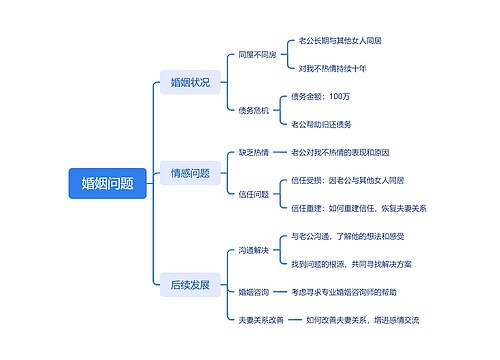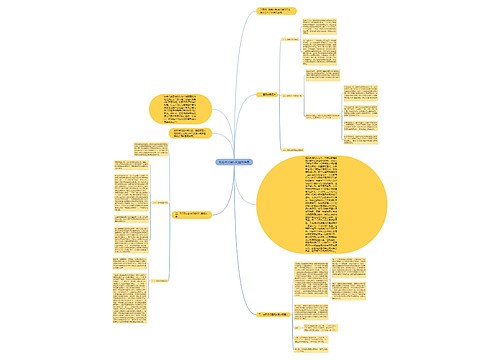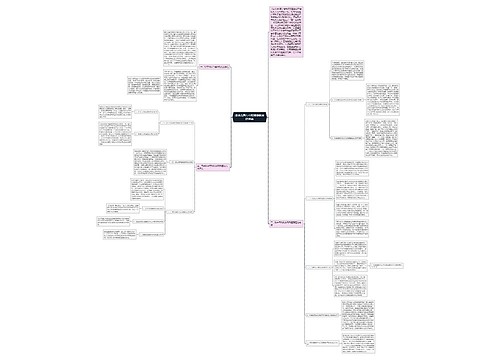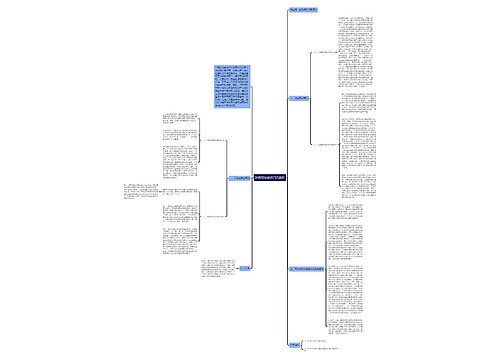婚姻法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国家或民族的道德观念在立法上的反映。对于我们这个历来重视家庭道德的民族来说,婚姻法的制定或修改具有特别的意义。正因为如此,新中国成立后较早制定了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改革开放之初,当国家启动大规模的立法工程时,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任务就被提到议事日程。于是有了1980年的《婚姻法》。世纪之交,立法机关又一次把修改此法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提上议事日程,而且,此次修改,民众参与之广、酝酿时间之长是少见的。正因为如此,新《婚姻法》无论是在立法技术上还是在内容上都有较大的进步。但是,由于主客观原因的限制,新《婚姻法》仍然存在诸多问题,包括人们已经意识到的但没有在立法上表现出来的问题。
新《婚姻法》的突出进步在于吸收了市场经济的精神,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第一、在新《婚姻法》中系统地规定了责任机制。
新《婚姻法》共分六章,即总则、结婚、家庭关系、离婚以及救助措施与法律责任。从立法体例上看,增设救助措施与法律责任的内容,不仅是立法技术上的进步,更主要的是反映我国人民及立法机关对婚姻的价值观念的进步。
第二、强化了法律对婚姻关系的监控力度。婚姻关系关系社会的稳定,因而现代国家和地区都把它纳人法律调整的范围。但许多国家和地区—尤其是资本主义世界同时也注人了过量的自由主义精神。比如在一些国家,婚姻关系的建立与解除具有较大的任意性,国家对此一般不作过多干涉,如非当同居形成的事实婚姻等。在我国,由于历史原因,一部分地区的人们的婚姻关系长期游离于法律轨道之外,若把它们简单地确定为无效婚姻,从表象上看,似乎是强化了对婚姻关系的法律监控,但实质上是把大量的婚姻关系排斥在法律约束之外。新婚姻法在第八、十、十一条加强了对婚姻关系的监控力度。
第三、在夫妻财产关系中注人了私法精神,主要体现在明确了夫妻共有财产的范围,同时,明确了法定夫妻财产制与约定夫妻财产制并存在的夫妻财产制。原《婚姻法》对夫妻财产基本上实行的是法定财产制,即夫妻共有财产制。这种制度不但无视财产主体对自己财产所有权的主观能动性,甚至强制性地改变了一定范围内的财产所有权的主体。同时,对夫妻共有财产的界定也过于模糊。原婚姻法只是简单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双方另有约定的除外”。这一规定并未明确夫妻财产约定制度,对夫妻共有财产显然也没有明确界定。
但对照20多年来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新婚姻法的进步性是有限的。
一是亲属制度之规定缺乏系统性。亲属是指基于婚姻、血缘、或者法律拟制而形成的社会关系。它是人类社会关系中最普遍的形式。人们一生都处于一定范围的亲属团体中,以调整亲属关系为主的婚姻家庭继承法律体系和原理始终为人们所普遍关注。亲属制度的内容涉及亲属的范围、种类、亲系、亲属关系的发生、终止及效力等。从国外立法体例来看,实行成文法的国家一般都是在民法典中对此作严密的规定,如瑞士、法国、德国、日本等国家,但我国并没有民法典。我国的立法是把《婚姻法》作为基本法来制定,即把《婚姻法》从民法中分离出来,并赋予《婚姻法》以调整家庭关系的责任。我国《婚姻法》实为“婚姻家庭法”,只是考虑到1950年立法时使用的是《婚姻法》这一名称,1980年修订《婚姻法》是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进行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及《立法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无权改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定下来的法律名称。既然如此,新《婚姻法》实为婚姻家庭法,对亲属关系作完整的规定是其应有之义。但目前,我国只是在《婚姻法》、《收养法》、《继承法》、《民法通则》、《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刑法》、《国籍法》等法律中从不同角度对亲属关系及其效力作出了某些具体的规定。但是这些规定是零散的,不系统的。
二是对离婚标准的规定没有实质性的进步,没有解决司法实践中审判机关认定离婚理由的困难。
确认婚姻关系破裂的标准,是近几年来法学界讨论的焦点问题之一。以夫妻关系破裂为标准已是法学界之共识。从理论上原《婚姻法》以夫妻感情破裂为离婚的法定理由,其依据是马克思恩格斯的有关观点,不过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简单应用于现实立法的实践,而没有考虑到把它作为法律标准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从司法实践来看,以夫妻感情破裂为判决离婚的法定标准早已暴露出其难以回避的弊端。正因为如此,最高人民法院在1989年n月21日作出了《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如何认定夫妻感情确已破裂若干具体意见》的司法解释,一共规定了14种情形作为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的判断标准以便于司法操作。而新《婚姻法》之所以维持这一原则性规定,主要是“考虑到怎样更好地维护平等、和睦、文明的婚姻家庭关系,避免草率离婚,给当事人及其子女带来不幸。”因此新《婚姻法》在修订时只是将上述司法解释的第七、八、九、十、十二、十三、十四条作了浓缩,在其第三十二条的第三款、第四款作了规定。从操作性来看,并没有原司法解释明确,不易操作。
三是忽视了法律对婚约的规范作用。“婚约”是男女双方以将来缔结婚姻为目的的一致协议。旧中国和西方国家的婚姻法中对此都给予了必要的规范。新中国成立后,婚约被视为旧社会的恶习而受到否定。因而,我国《婚姻法》对此一直持否定态度。笔者以为,旧中国的婚约制度的确存在着许多弊端,但简单地否定它的意义,并把它排除出法律约束的范围,也是不可取的。一方面,婚约本质上是一种包含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的约定,即不管它过去或将来的作用如何,它终归是一种契约。从国外立法实践来看,发达或较发达国家,即使国情差异很大,对婚约或婚约的解除在法律上的后果都作了必要的规定。
1978一1979年版本的法国民法典,虽然没有直接设立规范婚约的条款,但在实践中对因违反婚约而给对方造成的某种损害按民法典一千三百八十二条的规定作为侵权进行赔偿。德国民法典将婚约作为第四篇即亲属法的有机组成部分。瑞士民法典在第二篇亲属法中对婚约的建立、效力及违约后果均作了明确规定。至于英美法系国家则把婚约作为婚姻的重要阶段,视之为一种债权契约。另一方面,在我国完全无视婚约的作用也不具有现实性。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对因解除婚约引起的财物纠纷,法院一般都予以受理,这主要考虑到它是债法上的法律关系,同时这类纠纷如得不到及时妥善的处理,有可能引起矛盾激化,不利于社会稳定。因此,笔者认为,在《婚姻法》中对婚约予以规定是有必要的。
四是对区际婚姻家庭关系也没有给予必要的重视。改革开放以来,区际婚姻关系问题已摆到立法机关的面前。为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及最高人民法院不得不通过制定临时性的法律文件以应付之,但即使是这一措施也仅仅是作为民法的一个部分提出来的。1986年《民法通则》对此作了原则性的规定,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和外国人结婚适用婚姻缔结地法律,离婚适用受理案件的法院所在地法律。”然而,这些规定并不完整,更不系统。更重要的是,如果专门的婚姻立法对此没有任何规定,或者规定不全面,不但是婚姻立法的一大缺陷,也使得通过其他形式制定的规范难以发挥作用。
新《婚姻法》的颁布实施并不意味着我国婚姻法的修订工作已告结束。为进一步完善我国婚姻立法,并使得新《婚姻法》在实施中尽可能减少立法本身的缺陷而导致的问题,立法机关以及最高司法机关还需要投入必要的精力制定补充性的规范文件,或司法解释,以弥补新《婚姻法》之不足。
参考文献:
杨大文。亲属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
梁建达。外国民商法原理〔M].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1996.
王光仪。婚姻法教程〔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88.
夏吟兰。婚姻家庭与继承法学原理〔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