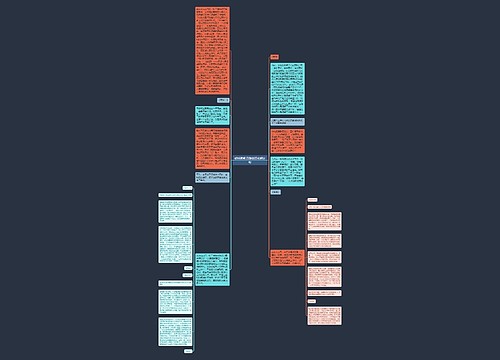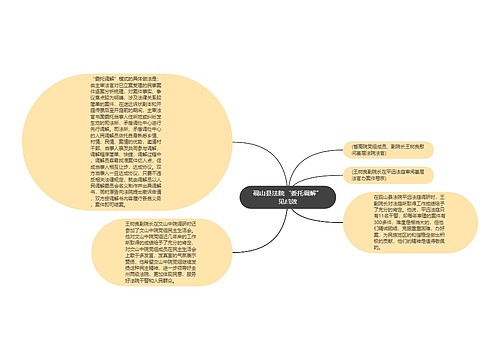从称谓上看,“诉前委托调解”极易让人联想到“诉前财产保全”这一存有多年的法律术语。依据《民事诉讼法》第93条第3款之“申请人在人民法院采取保全措施后十五日内不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解除财产保全”的规定,“诉前财产保全”中的“诉前”一词应理解为“起诉前”,这一字面解释式的理解不仅符合既有的法规范,而且与社会公众的认知习惯相契合。社会公众接受存有多年的法律术语后,会产生认知上的依赖与惯性。基于这种依赖与惯性,社会公众会不自觉的、通常不细加分析的将“诉前委托调解”中的“诉前”一词与诉前财产保全”中的“诉前”一词作等同理解。而若将“诉前委托调解”中的“诉前”一词理解为“起诉前”,则将与诉前委托调解发生于“起诉后,立案前”的实践作法相异而无法对这一法律现象作出妥当的解释;若将“诉前委托调解”中的“诉前”一词削足适履式的解释为“起诉后,立案前”,固然可以牵强的解释实践中的作法,但由此诱发的字面理解的不可行性将造成社会公众对“诉前委托调解”这一术语的接受困难,与此同时,必然发生的“字同意异”的情形将导致委托调解之理论阐释与提升难以顺利进行之风险的出现。
从规范上看,“各方当事人同意”是委托调解得以发生的前提,也是委托调解的绝对构成要件之一。这符合处分原则的基本要求,是当事人程序主体之地位的体现,也是保障当事人之程序选择权的体现。不管“诉前委托调解”中的“诉前”一词被理解为“起诉前”,还是被理解为“起诉后,立案前”,都意味着诉前委托调解开始时民事案件是否被受理尚没有确定性结论,此时诉讼法意义上的“当事人”无从确定,即便是作为发动诉讼程序的一方,起诉者也未获得“原告”之地位。“当事人”尚未确定,尚未从虚拟走向实在,向他们征求是否同意委托调解的意见便无法进行,于是,“诉前委托调解”因“经各方当事人同意”的不可行性而不得不出现异化式的变通,“起诉方同意”取代了“各方当事人同意”,“单方表态”取代了“双方合意”,委托调解的最大特征——交涉性在程序启动之初便出现了缺位,相对一方对是否以委托调解的方式解决民事纠纷的程序选择权被剥夺,作为各种类型的诉讼调解之最根本、最基础原则的自愿原则被轻而易举、明火执杖的背离。另一方面,诉前委托调解将导致暂缓立案,而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12条的规定,人民法院收到起诉状或者口头起诉后七日内必须作出立案或不予立案的结论,这一必为性义务规则没有给人民法院在“立案”和“不予立案”之外谋求第三种选择的余地和机会,因诉前委托调解而暂缓立案构成对必为性义务规则的违反,属于法外行为。
从学理上看,人民法院是委托调解中的委托人,特定的单位或个人是委托调解中的受托人,委托调解的合法性首先取决于人民法院与特定的单位或个人之间的委托关系的合法性。换而言之,人民法院与特定的单位或个人之间的委托关系若不具有合法性,将对委托调解的合法性形成釜底抽薪式的否定作用。除委托人适格和受托人适格外,人民法院与特定的单位或个人之间的委托关系的合法性还取决于作为委托人的人民法院事先对委托事项(民事案件)是否拥有管辖权。但显而易见的是,由于立案是决定人民法院对民事案件是否拥有管辖权的分水岭,人民法院不可能在“起诉
前”或“起诉后,立案前”取得对民事案件的管辖权,这反向传导式的否定了人民法院与特定的单位或个人之间的委托关系的合法性,调解的诉前委托因此成为缺乏正当权源的不当举措。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撰写此文,无意否定委托调解在扩充人民法院的行为能力、推动民事诉讼的社会化、增加民事司法的社会认同感和可接受性、力争民事纠纷的共同解决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对委托调解这一民事司法改革中谋求诉调对接而产生的新事物,笔者也赞成给予其更多的呵护和支持,只是笔者一直认为缺乏法理依据的创新性举措不会有长久的存续力并很难生成为制度。

 U633687664
U633687664
 U582679646
U5826796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