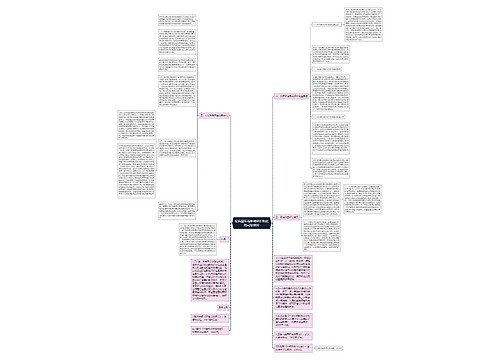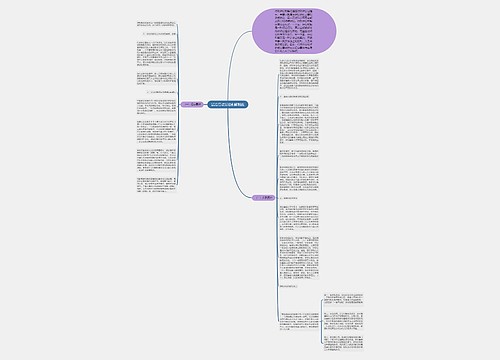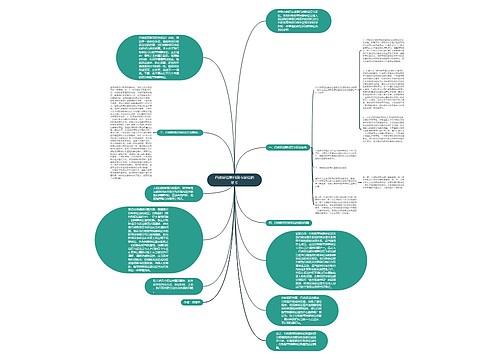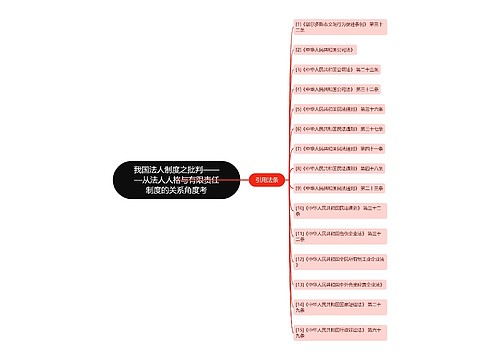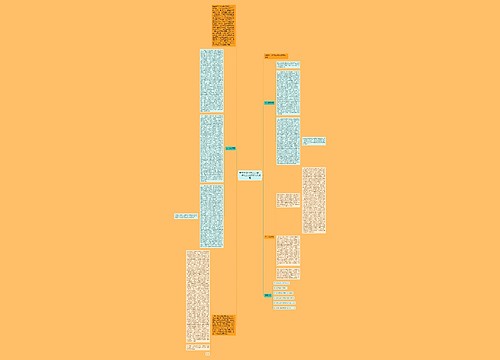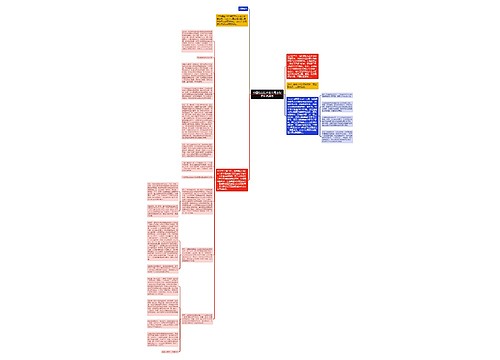(一)法律渊源的矛盾性。法律与司法解释构建了我国法律渊源最主要的内容,然而二者在制定机关、效力位阶、职能等方面有着很大的区别。“所谓司法解释,是指我国最高司法机关根据法律赋予的职权,在实施法律的过程中,对如何具体运用法律问题作出的具有普遍司法效力的解释。”[⑥]据此,司法解释应当具有这样几个特征:第一,司法解释是包括最高法院在内的最高司法机关在审理案件过程中,为适应复杂多变的社会生活和审判实践的需要,依据法律赋予的职权,对现行的成文法所作的解释。第二,司法解释是“解释”而不是立法。根据我国宪法规定,立法权由法定的立法机关行使,立法是纯粹的创制法律;而法院是司法机关,行使的是审判权,其职权决定了它只能解释法律,而不可以创制法律。解释法律应当有对象,也即有被解释的法律规范存在,应以法律规范为基础,对其加以理解和说明。第三,司法解释一经公布,即具有普遍的司法效力。反观分配方案异议制度,在民诉法上是没有相关规定的,那么出现在司法解释中的这个规定是解释民诉法的哪个条款呢?而且从这一规定的体例和内容上分析,存在很多需要解释的地方,比如“分配方案异议”存在哪行情况在司法实践中需要作出一定的解释,如对受偿顺序、受偿数额等方面存在异议,然而对司法解释再行解释又是什么性质呢?所以这一规定出现在司法解释中实为尴尬。
(二)提起异议的主体范围宽泛。引起执行程序启动必然存在执行根据,而执行根据已就被执行财产的归属作出认定,即不再属于被执行人,余下的只是债权人如何分配被执行财产的问题,这与债务人并无实质性的利害关系,因此分配方案异议只能由参与分配的债权人提出。若债务人对分配方案有异议的,可作为一般执行救济中的执行异议进行处理。而本次解释中规定,提出分配方案异议的主体包括债权人和被执行人,笔者认为主体过于宽泛,实际上并不需要将债务人纳入分配方案异议的主体范畴。
(三)未提出异议当事人在分配方案异议之诉中的地位。司法解释中只明确异议人作为原告,持反对意见的债权人或被执行人为被告,那么其他不提异议也不反对的当事人诉讼地位如何确定,权利如何保障?相对于原执行程序,分配方案异议之诉属于衍生的独立之诉,而执行程序中的各方当事人存在复杂的关系,新诉产生后,未异议也未反对的当事人就是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甚至证人还是其他的什么角色,在规定中是模糊的。规定中表述“诉讼期间进行分配的,执行法院应当将与争议债权数额相应的款项予以提存”,其意在于未异议的实体权利按照正常的程序执行,那么部分债权人如果对整个被执行财产存在争议,未异议也未反对的当事人将会被无辜的拖进新的诉讼中,权利受到损害,而且还产生了一个棘手的问题,即主体身份是什么,如果是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不服裁判结果可以提起上诉,很可能陷入复杂的境地。
(五)执行中的分配方案异议应由法院的哪个部门受理未予明确。分配方案异议的处理部门是执行机构还是审判机构应当予以明确,这直接关系到异议能否得到公正快速的处理。一直以来,由于审执关系复杂而微妙,理论界与实务界争论颇多,有支持审执分离,有崇尚审执结合。然而,越是存在争议的就应该在法律上予以明确,否则将对审执实务带来不利影响。异议受理部门的不明确,可能使各级法院、各地法院出现受理部门不同、处理程序不同的情形,使异议的审查和处理具有较大的随意性、主观性,造成适用法律混乱的不利后果。
(六)执行效率降低存在可能。英国法谚有云:“迟来的正义非正义”。执行所追求的目标,就是以经济、便捷的方法,迅速实现债权人之权利,否则,不仅债权人私权难获保护,而且可能损害社会经济及司法威信。 从某种意义上说,效率是执行的第一价值目标,执行工作的性质决定了执行措施必须迅速及时,执行的目的就是让债权人公正合理的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分配方案异议制度将利害关系人带入新的诉讼,按照普通诉讼的程序,存在一审、二审、再审甚至循环诉讼的问题,这不但可能影响执行效率,还可能影响其他当事人的权益。另一方面,诉讼的增加无形中加大了司法成本,当今我国司法人员特别是法官队伍力量不足是个不争的事实,这在基层法院尤为突出,诉讼的增加势必加重法院压力,为了实现执行程序的效率目标,我们应当重新审视业已确立的该项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