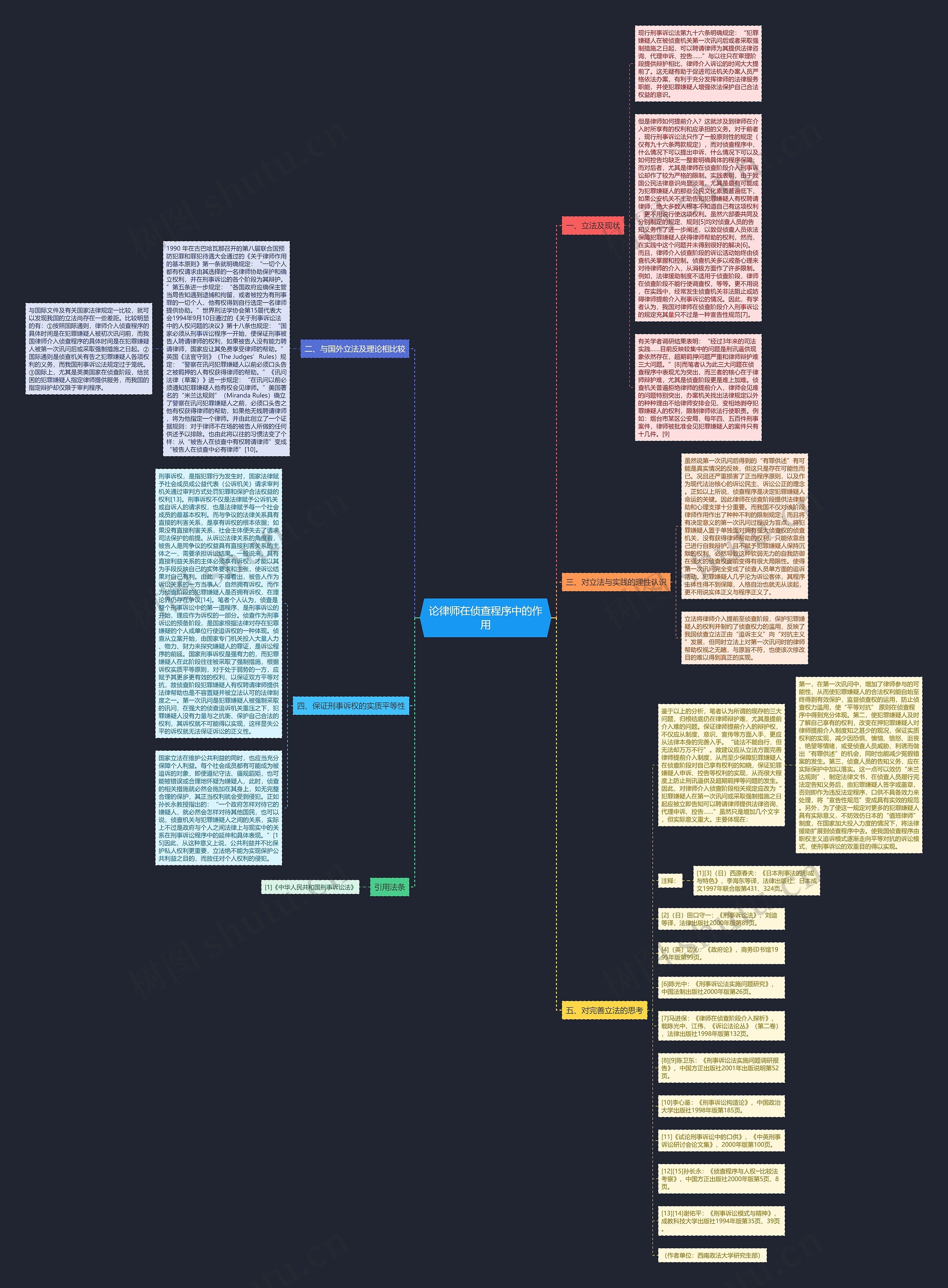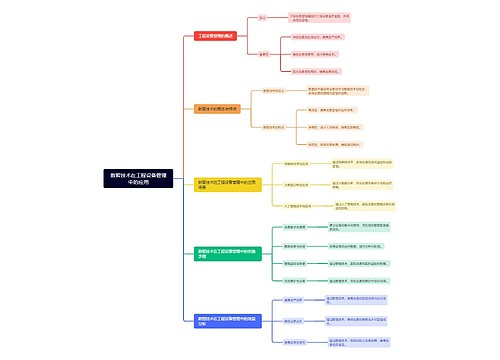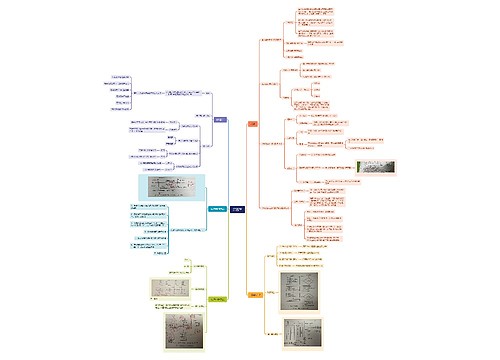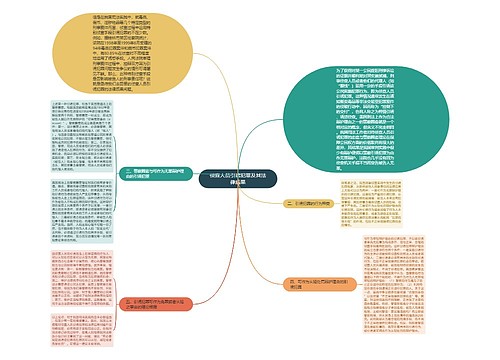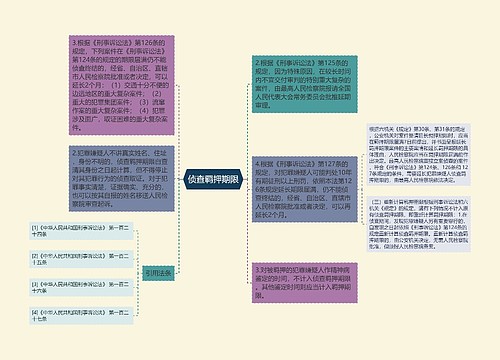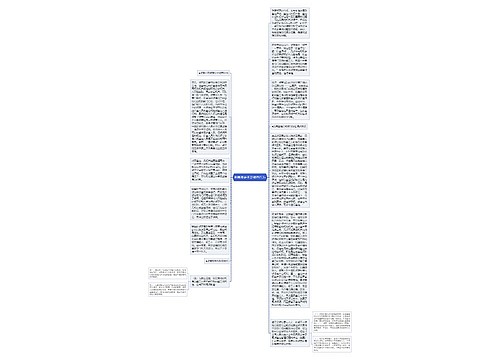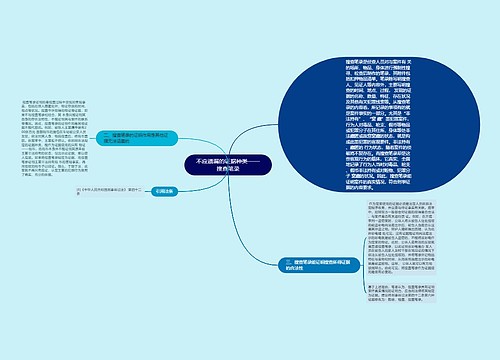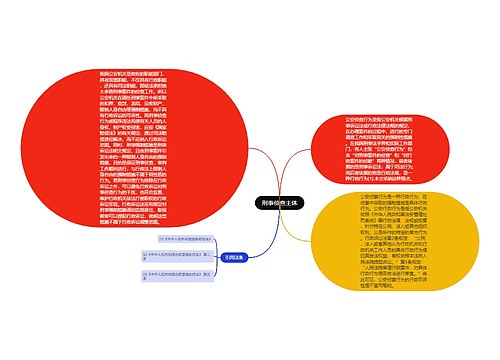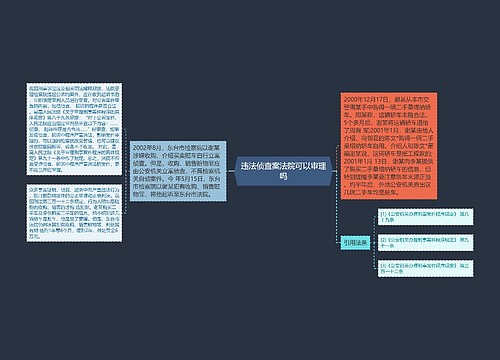鉴于以上的分析,笔者认为所谓的现存的三大问题,归根结底仍在律师辩护难,尤其是提前介入难的问题。保证律师提前介入的辩护权,不仅应从制度、意识、宣传等方面入手,更应从法律本身的完善入手。“徒法不能自行,但无法却万万不行”。故建议应从立法方面完善律师提前介入制度,从而至少保障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对自己享有权利的知晓,保证犯罪嫌疑人申诉、控告等权利的实现,从而很大程度上防止刑讯逼供及超期羁押等问题的发生。因此,对律师介入侦查阶段相关规定应改为“犯罪嫌疑人在第一次讯问或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应被立即告知可以聘请律师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虽然只是增加几个文字,但实际意义重大。主要体现在:
第一,在第一次讯问中,增加了律师参与的可能性,从而使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利能自始至终得到有效保护,监督侦查权的运用,防止侦查权力滥用,使“平等对抗” 原则在侦查程序中得到充分体现。第二,使犯罪嫌疑人及时了解自己享有的权利,改变在押犯罪嫌疑人对律师提前介入制度知之甚少的现况,保证实质权利的实现,减少因恐惧、懊恼、愤怒、沮丧、绝望等情绪,或受侦查人员威胁、利诱而做出“有罪供述”的机会,同时也能减少冤假错案的发生。第三,侦查人员的告知义务,应在实际保护中加以落实。这一点可以效仿“米兰达规则”,制定法律文书,在侦查人员履行完法定告知义务后,由犯罪嫌疑人签字或盖章,否则即作为违反法定程序,口供不具备效力来处理,将“宣告性规范”变成具有实效的规范。另外,为了使这一规定对更多的犯罪嫌疑人具有实际意义,不妨效仿日本的“值班律师”制度,在国家加大投入力度的情况下,将法律援助扩展到侦查程序中去。使我国侦查程序由职权主义追诉模式逐渐走向平等对抗的诉讼模式,使刑事诉讼的双重目的得以实现。
注释:
[1][3](日)西原春夫:《日本刑事法的形成与特色》,李海东等译,法律出版社、日本成文1997年联合版第431、324页。
[2](日)田口守一:《刑事诉讼法》,刘迪等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89页。
[4](英)边沁:《政府论》,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99页。
[6]陈光中:《刑事诉讼法实施问题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第26页。
[7]马进保:《律师在侦查阶段介入探析》,载陈光中、江伟,《诉讼法论丛》(第二卷),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132页。
[8][9]陈卫东:《刑事诉讼法实施问题调研报告》,中国方正出版社2001年出版说明第52页。
[10]李心鉴:《刑事诉讼构造论》,中国政治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85页。
[11]《试论刑事诉讼中的口供》,《中英刑事诉讼研讨会论文集》,2000年版第100页。
[12][15]孙长永:《侦查程序与人权─比较法考察》,中国方正出版社2000年版第5页、8页。
[13][14]谢佑平:《刑事诉讼模式与精神》,成教科技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5页、3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