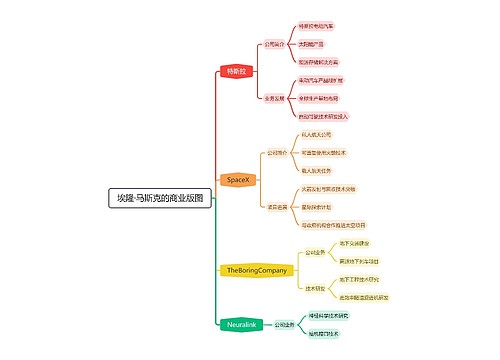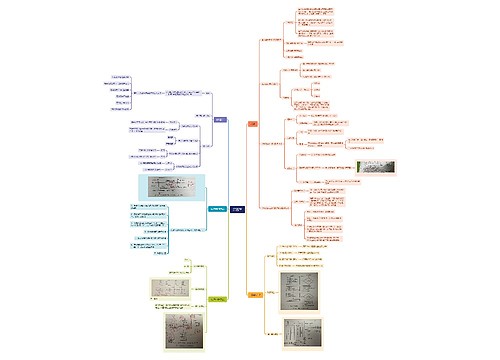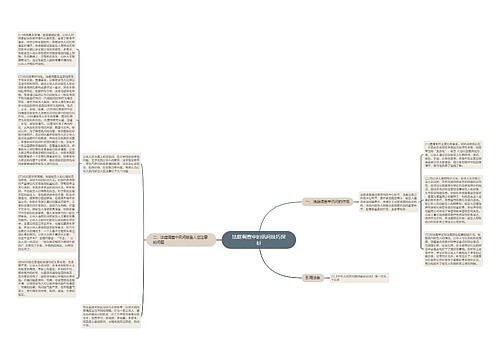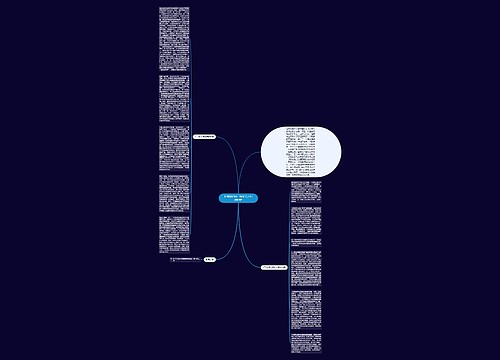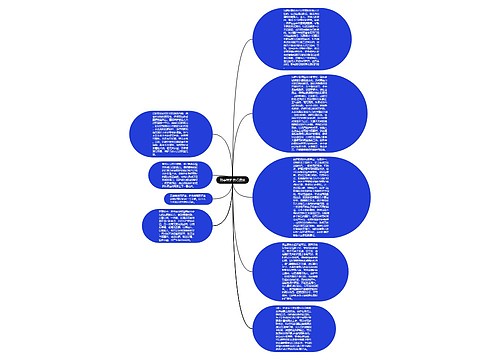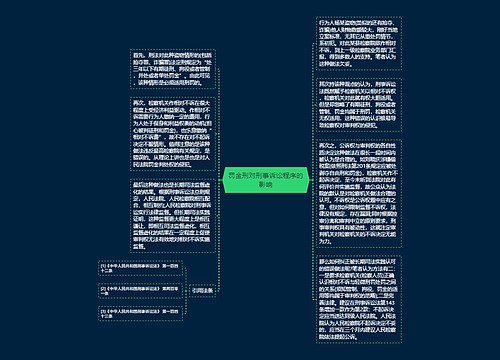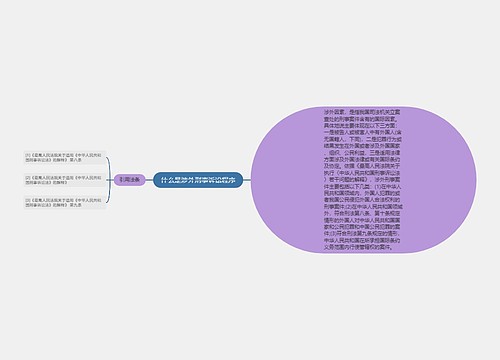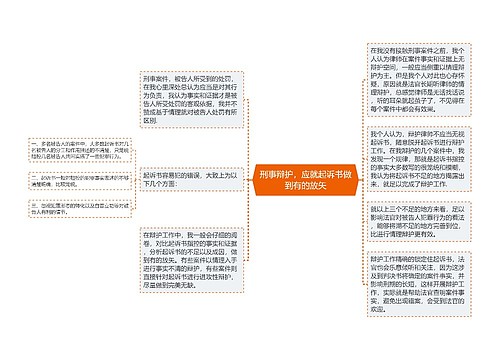重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风雨兼程整整走过了四个年头,其中不乏艰辛和汗水,“无罪推定”、“罪疑从无”等西方法律思想的移植,使刑诉法的价值理念日趋完善和成熟。然而,四年多来,刑事案件尤其是恶性案件和重大经济犯罪案件大幅上扬,刑事审判陷入一个颇为尴尬的境地,作为维护被告人权益屏障的辩护律师,其诉讼权利亦得不到应有的保护,刑事诉讼程序公正受到挑战,具体表现在:
一、角色的错位
1.最高法院关于刑事诉讼法的司法解释第一百七十六条第二款规定:“起诉指控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的罪名与法院审理认定的罪名不一致的,仍应当作出有罪判决。”而事实上,法官的职责中并没有提起公诉的权利,对指控的罪名只能有认定成立或不成立的二元论,根本不存在法官认定与控诉方指控罪名不一致的情况,但在司法实践中,改变定性时有发生,法官充当了控方的角色,使得控辩双方的对抗成了控审与辩方的搏击。
2.最高法院等六机关1998年1月19日公布的《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八条的规定,对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公诉案件,无论人民检察院是否派员出庭,都应当向人民法院移送全部卷宗和证据材料。法官在庭审前对移送的材料进行梳理、归纳、确认,并对重点部分进行圈点,以便庭审的顺利进行。不觉中站在控方的立场上看待问题,先入为主,使得案件的庭审流于形式。
3.美国律师界有句名言“最好的辩护就是主动进攻”,事实上,律师在现实中有种种顾虑,“不善于”、“不愿意”、“不敢于”与公诉方进行激烈的对抗。面对强大的公诉力量,辩护律师为了维护当事人的最低利益,很少作无罪辩护(即使无罪成立,控方也绝不放过抗诉的机会),“往往不得不从有罪的角度作从轻辩护,引导法庭确立另一项相对较轻的罪名和法定刑,实际上演变成对当事人的变相指控”。
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最大的贡献是法官从对被告人进行积极追诉的角度转变为居中裁判、主持正义的消极角色,吸收了英美法系的当事人主义,无疑是诉讼法学的一大进步。而实践却与立法精神背道而驰,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辩护律师提前介入的作用未能体现。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四条至第一百二十七条的规定,侦查机关羁押犯罪嫌疑人的期限可达7个月之多,甚至更长,侦查机关利用国家赋予的强制措施,收集了大量的证据,检察官依照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条的规定,已获得公安机关移送的主要证据。而刑事诉讼法第九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律师在侦查阶段只能提供法律咨询,并未规定律师可以调查取证,律师没有权利知悉案件的任何证据,只能在案件移送起诉后才能调查取证,律师输在起跑线上已成定局。律师在侦查阶段不能调查、阅卷,使得律师提前介入成为走过场,对改变犯罪嫌疑人的地位作用甚小。
2.层层设防。(1)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律师在查阅、摘抄、复印相关证据范围由检察院确定,检察院移送的证据材料往往是部分证据的复印件,使得一些有价值的材料与律师擦肩而过,先天不足的律师难以在激烈的法庭辩论中有所作为,只能在初犯、偶犯、认罪态度等无关痛痒的酌定情节上为被告人争取。(2)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七条第二款规定,辩护律师经人民检察院或人民法院许可并且经被告人或者其近亲属、被害人提供的证人同意,可以向他们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无疑让缺少司法救济(强制措施)的律师雪上加霜。证人作证对国家是义务,而对辩护律师却是权利,许多有价值的证据因被害人或其证人的不配合而灭失(有些案件如杀人案件,如果积极配合,岂不有助纣为虐之嫌),使律师的努力付诸东流。(3)人力与经济的悬殊。我国刑事诉讼法明文规定,被告人最多只能聘请两名律师,而对检察院办案人员却没有相应的限制,甚至全院出动也在所不惜。由于种种立法及现实的限制,使得律师付出的艰苦的劳动难以得到成正比例的回报,浪费了本来就有限的律师资源,被告人的经济实力也成为辩护律师是否能有效辩护(取证)的重要影响因素。
为保护国家和广大人民的安全,维持良好的社会秩序、公共利益而有效的控制犯罪已得到普遍的重视,而在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基本权利却未得到足够的关心。要实现社会的“权力本位”向社会的“权利本位”过渡,通过刑事诉讼法程序公正而获得实体的真正公正,就必须彻底清除封建思想及法律心理意识对刑事诉讼的影响,从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尊重被告人的人权,切实的维护辩护律师的合法利益,笔者从以下几个方面提出解决措施:
“司法权一旦与冲突的一方具有某种价值取向和利益性的偏异倾向,就会使人对裁判的公正性产生怀疑,因此法官在诉讼中必须保持中立,对控辩双方主张的利益给予同样的关注,在诉讼中只能根据双方提供的证据去判断‘是与非’,而不能身体力行去证明冲突一方的‘是与非’,严禁法官先入为主,对冲突一方产生偏见”。因此建立均衡对抗制,法官居中裁判意义重大。
1.取消控方开庭前移送证据或者全部卷宗的做法,实行英美法系的“诉讼一本主义”,即“只能向有管辖权的法院提出具有法定格式的起诉书,而不得载入可能使法官对案件产生预断的文书和证物”。实际操作中,只需提供起诉书及证人名单即可,从源头上防止先入为主情况的发生。
2.建议律师介入调查取证的时间提前,即在犯罪嫌疑人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采取措施之日起即可介入调查并参与当事人的活动,取消对律师调查取证权的不合理限制。
3.程序公正集中体现在权利的分配上,因此必须建立理性的举证分配制度,给控辩双方平等的调查取证权。
证据是诉讼的核心,是事实的再现的载体;诉讼是证据的搏击,使证据的价值得以界定。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刑事诉讼证据制度的滞后弊端日趋明显,以合法性、维护人权为视角,建立与时代合拍的证据制度迫在眉睫。在此,美国在证据规则方面的“毒树之果”原则值得借鉴。(“毒树之果”原则在国内的很多著作中均有介绍,不在论述。)但切不可全盘照搬,或简单的加以否定。我们应当顺应民主的潮流,在对法律文化传统和民族心理差别分析的基础上,吸收美国“毒树之果”原则的精华,“在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中找到平衡的支点”。
三、废除“可以派员”的规定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九十六条的规定,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侦查机关“可以派员”参加。在现实中“可以派员”变成“经常派员”,在被监督的情况下,犯罪嫌疑人如实向辩护人陈述案情存有顾虑,无法按照真实的意愿向律师供述有关事实,也无法就辩护事由与律师协商,对律师工作开展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四、修改刑法关于伪证罪的主体规定,赋予律师庭审言词的“豁免权”
刑法关于伪证罪的规定,成为律师头上一把“达摩克里斯剑”,刑事辩护陷入两难,律师如临深渊,顾虑重重,不敢大胆行使辩护权,不能达到预期的庭审目的,被告人的利益也得不到应有的维护。在实践中,律师被追诉(律师的犯罪要由控方追究,难免折射出控方职业报复的倾向,同时,对侦控的违法取证却没有相应的惩处规定,公正难以实现),更多律师选择了中庸之道,在正义和安全利益之间小心翼翼,绝不“越雷池一步”。伪证罪不仅使律师的辩护效果大打折扣,更严重地挫伤了律师参与刑事诉讼的积极性。
立法公正是公正的基础,要实现刑事诉讼法程序的真正公正,就不能忽视从立法、制度政策上关怀辩护律师,刑事诉讼法“作为保证刑法实施的程序性法律,应从过去强调社会保护机能向人权保障机制倾斜,其基本价值应当在于对被告人利益的保障体现司法公平与公正,以一种看得见的争议来实现司法目标,从而保护社会正常秩序的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