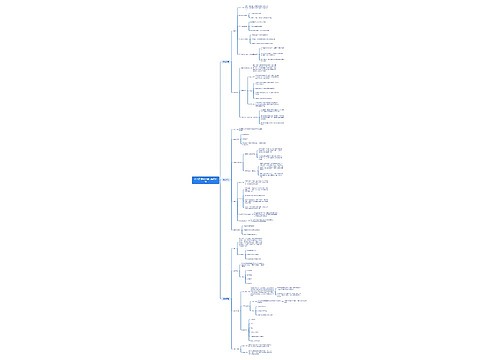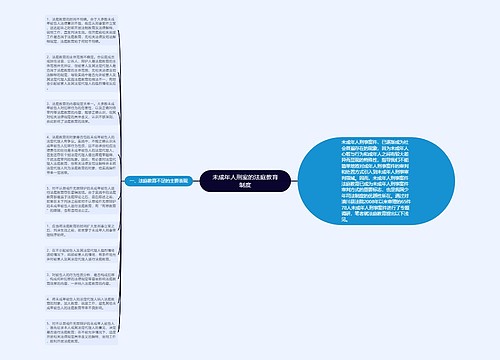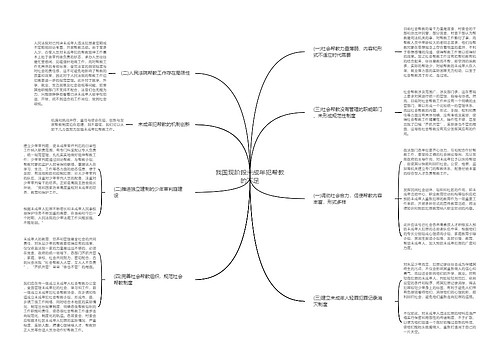《刑法》第65条第一款规定,“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分子,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在五年以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的,是累犯,应当从重处罚,但是过失犯罪和十八周岁的人犯罪的除外。”
然而,同时《刑法》第66条规定“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的犯罪分子,在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在任何时候再犯上述一类罪的,都以累犯论处。”即特殊累犯的规定。在《刑法》第356条针对毒品犯罪规定:“因走私、贩卖、运输、制造、非法持有毒品被判过刑,又犯本节规定之罪的,从重处罚。”即毒品再犯。这两种情节与累犯一样,都是对再次犯罪的犯罪分子加重处罚的情节,尤其是特殊累犯与毒品再犯的构成条件更加相近。这样在审判实践中,对于未满十八周岁的被告人是否如同不构成累犯那样,不构成特殊累犯和毒品再犯则存在较大的分歧、困扰。
争议中有一种观点认为,《刑法修正案(八)》只规定了未成年人犯罪不构成累犯,对于特殊累犯和毒品再犯没有做出相应的修改,应认定未成年人犯罪可构成特殊累犯和再犯。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刑法修正案(八)》对于累犯的修改是立足于保护未成年人权利的,从刑法宽囿、谦抑的原则出发应认为未成年人重新犯罪不构成特殊累犯和毒品再犯,这样既符合刑法修正的目的,更有利于对于未成年人的教育、挽救。另外有第三种观点认为,未成年人重新犯罪不构成特殊累犯,但可构成了毒品再犯。
笔者同意第三种观点。笔者认为,对于刑法法条的理解不能片面的从字面上分析或一概的从刑法原则考量,应当从立法意图和刑法体例、刑事政策等方面综合分析。就本文争议而言。
第一、关于未成年人是否能构成特殊累犯。
从法律体例上看,《刑法》第65条、第66条都归属在总则中累犯规定之内。前者是一般规定,是对“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在五年以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的”加以规定,而后者规定“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的犯罪分子,在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在任何时候再犯”是对前者的一种补充规定,强调了在这种情况下“以累犯论处”,是特殊情形下的累犯,两者是递进关系。前者的“但书”是把未成年人罪犯排除在累犯之外,而后者则是为前者补充入了其他形式的累犯,是包含在前者规定的累犯之内的,是包括在“但书”之内的。
从立法上看。通过修改第65条把未成年人排除在累犯之外,是《刑法修正案(八)》加大对未成年人保护的亮点之一,但《刑法修正案(八)》同时修改了第66条增加了两个特殊累犯的罪名。如果认为特殊累犯包括未成年人犯罪的话,那么立法时在把未成年人犯罪排除在累犯之外的同时又把未成年人犯罪纳入特殊累犯之中,岂不是自相矛盾,有违了立法意图。故不能构成累犯。
第二,关于未成年人是否构成再犯。
从法律体例上分析。《刑法》第65条、第66条与第356条,分属总则和分则。前者是对累犯的规定,认定累犯的依据,后者是针对毒品犯罪的特殊规定。前者是总则中的一般条款,虽然是对分则有指导意义的原则性规定,而后者是分则中针对具体罪名的特殊规定,是优于前者的特别条款,因而两者相不能等同。
从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上来讲。毒品犯罪一直是立法者打击的重点。从修正前的《刑法》第17条第2款规定的已满十四周岁未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负刑事责任的八项罪中,包括了贩卖毒品却没有包括特殊累犯的三种罪,可见这一立法现实。毒品再犯罪作为分则中的特别规定,体现出立法者对毒品犯罪的打击的力度、打击的决心,从立法开始就明显强于一般犯罪或是特殊累犯中的“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的犯罪”。基于这种打击力度的差异,毒品再犯对于未成年人犯罪也成立是正常的。另外,如果立法者有意把未成年人排除在再犯之外,修改《刑法》时对第356条也可增加“但书”内容,实际上却没有这样做。这种立法上的改或没改,也正是体现了宽严相济的政策。
从审判工作中考量。根据《刑法修正案(八)》修改的第74条规定,对于“累犯和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不能适用缓刑。如果认定未成年被告人系累犯,那么被告人失去了判处缓刑的机会,而未成年被告人被认定毒品再犯,虽多了从重量刑的情节,但仍不排除适用缓刑的可能。故把未成年人犯罪排除在累犯之外,毒品再犯对未成年人犯罪成立,与对未成年人审判中的教育、挽救的原则仍相一致。
综上,笔者认为未成年人犯罪不构成特殊累犯,但仍能构成毒品再犯。
引用法条
[4]《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 第六十六条
[5]《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 第七十四条

 U633687664
U633687664
 U882673919
U8826739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