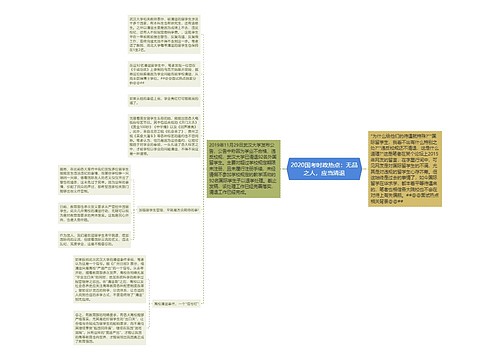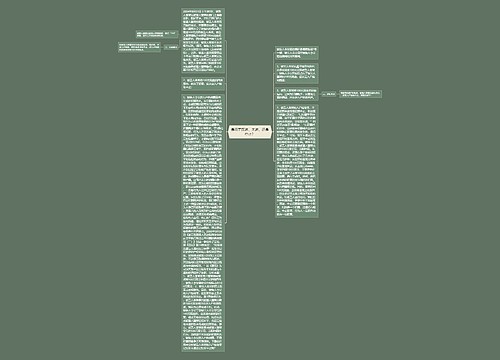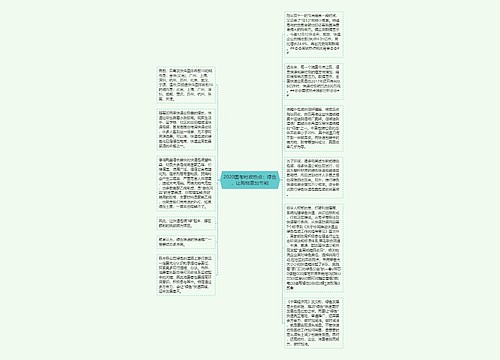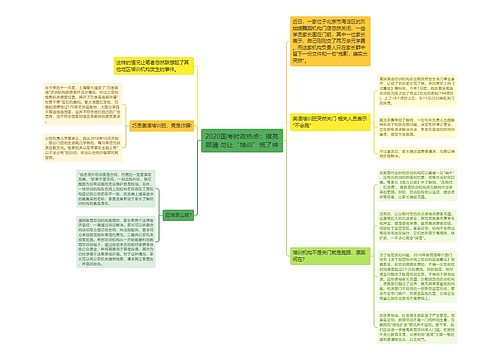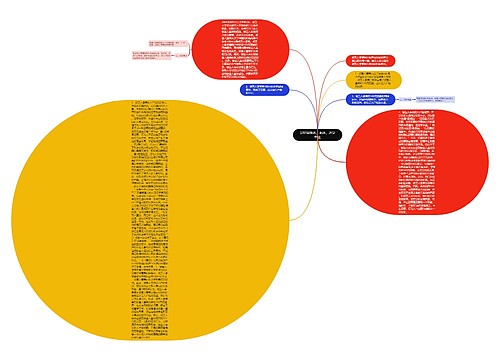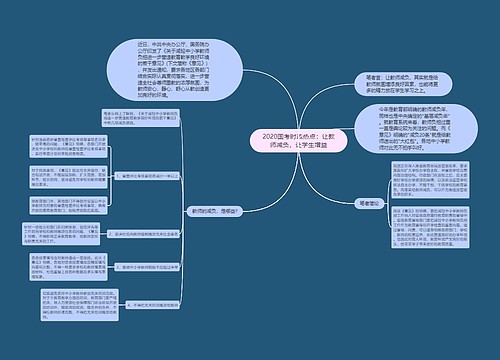从法律规定来看,刑法第二十四条规定:“在犯罪过程中,自动放弃犯罪或者自动有效地防止犯罪结果发生的,是犯罪中止。”所谓“犯罪过程”,即指从犯罪预备到犯罪结果出现之前的整个过程。犯罪既遂后,结果出现前,只要行为人采取了积极措施有效防止犯罪结果的发生,仍可能成立犯罪中止。刑法对犯罪中止与犯罪未遂的评价并不是采用同一标准,既遂以行为是否符合刑法分则规定的全部要件为标准,中止以是否自动防止犯罪结果的发生为标准。从逻辑上讲,分类标准的不统一,可能造成外延的重叠,因此,犯罪既遂与犯罪中止完全有可能并存。
从刑法理论来看,犯罪中止的成立有“四性”,即时间性、自动性、客观性、有效性。时间性是要求中止要发生在犯罪过程中。自动性是要求放弃犯罪或者有效防止犯罪结果的发生,是出于内心自愿,而非意志外的原因强制。客观性要求行为人要有中止的行为。对于未实行终了的犯罪而言,中止行为表现为放弃正在进行的犯罪;对于实施终了结果尚未发生的犯罪而言,中止行为表现为采取积极措施有效防止犯罪结果的发生。有效性是要求没有发生行为人所追求的犯罪结果。符合上述四条件的,就是犯罪中止。行为人实施了投放危险物质的行为并出现危险状态后,又主动采取措施有效消除危险的,符合犯罪中止的四个条件,应当认定为犯罪中止。
从刑事政策来看,认定危险犯既遂后仍可成立犯罪中止,有巨大的社会意义。它会鼓励行为人采取积极的措施尽力防止危害结果的发生,从而使社会免受侵害,使刑法的作用从事后的消极惩罚转变为事前的积极防范。这符合设立危险犯的立法初衷。刑法之所以将危险的出现而不待实害结果出现时就将其作为犯罪予以打击,目的就在于竭力防范实害结果的出现,避免两败俱伤。因此,将上述行为认定为犯罪中止无疑更符合立法原意。
认为犯罪既遂后仍可以成立犯罪中止,不可避免地会受到以下诘难:“犯罪既遂后不可能存在犯罪中止”是刑法理论的通说,经典的案例就是行为人盗窃他人财物后,主动又将财物送回原处,仍应认定为既遂,而不能认定为中止。其实,通说是有其适用条件的,对于结果犯而言,既遂后不可能存在中止,而对于危险犯(准确地说是具体危险犯)而言,犯罪既遂后仍可以成立犯罪中止。上述盗窃案与投放危险物质案有本质的区别:在盗窃案中,即便是行为人将财物送回,刑法所预防的结果已经出现,财产所有人或占有人对其财物已经失控,这种占有和支配状态已经受到破坏,这种危害结果并不能因财物的回归而消除,正如将人打伤后,又医治其痊愈一样,对被害人所造成的伤害结果并不能随着伤口的愈合而消除;在投放危险物质案中,刑法所预防的结果还没有出现,在这种危害结果还没有出现之前,行为人完全可以将可能引起危害结果的危险消除,因此,在危险犯中,即便出现了法定的危险,行为人又消除了这种危险,仍有犯罪中止存在的余地。
认为犯罪既遂后仍可以成立犯罪中止面临的另一诘难是:犯罪的预备、未遂、既遂、中止是故意犯罪的四种独立形态,如果认定犯罪既遂的同时,又认定为中止,就破坏了犯罪形态的独立性,导致犯罪形态的混乱。其实,犯罪预备、未遂、既遂和犯罪中止的分类根本就不是同一标准,前三者是按故意犯罪的阶段或曰犯罪的推进程度为标准而进行的分类,因此,它们有两种含义:一是指犯罪的阶段,另一含义是指犯罪的形态;而犯罪中止是根据犯罪开始后有否自动抑制犯罪的行为为标准所作的分类,它仅指犯罪形态,并没有犯罪阶段的含义。从理论上来讲,对犯罪的抑制行为可能出现在犯罪的任一阶段,因此,根据抑制行为出现的不同阶段,可以将犯罪中止分为预备阶段的中止、未遂阶段的中止、既遂阶段的中止。由于每一犯罪各自有不同的特点,并非每一犯罪都必然存在上述三个阶段的中止。对于结果犯而言,由于犯罪的既遂与结果的出现是在同一点上,因此,不存在既遂阶段的中止;对于危险犯而言,犯罪的既遂与结果的出现不在同一点上,因此,可能存在既遂阶段的中止。总之,犯罪的预备、未遂和既遂都是在排除了犯罪的中止形态以后才讨论的话题,在存在既遂又存在中止的时候,中止形态就具有优先性,当然应认定为犯罪中止,而不能认定为犯罪既遂。其他犯罪阶段亦然。因此,承认既遂与中止的并存,并不会导致犯罪形态的混乱。
对于预备阶段可以存在中止,学界并无异议,而对于未遂和既遂阶段的中止,则不无争议。笔者认为,既然承认预备阶段存在犯罪中止,就没有理由否认未遂和既遂阶段犯罪中止的存在。在未遂阶段,完全有可能出现犯罪中止,放弃重复侵害行为即是最佳范例;同理,既遂阶段也能出现犯罪中止,投放危险物质后,又采取有效措施消除危险即为一例。

 U633687664
U633687664
 U582679646
U5826796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