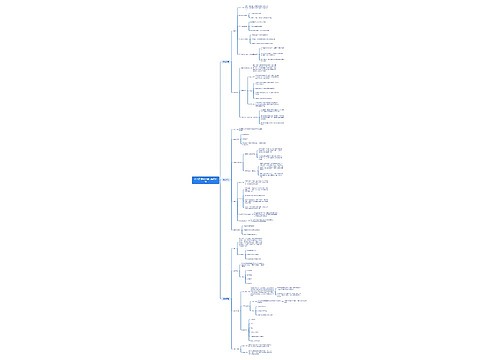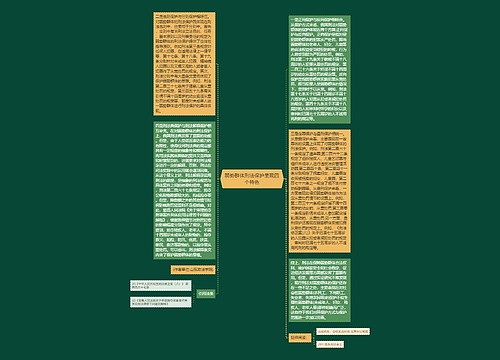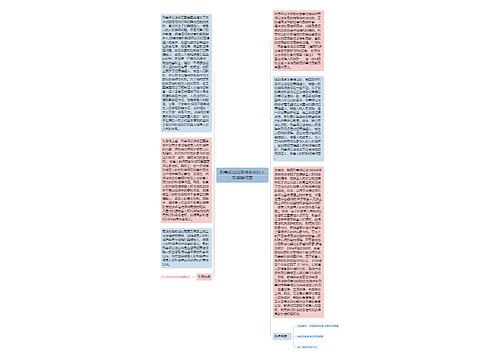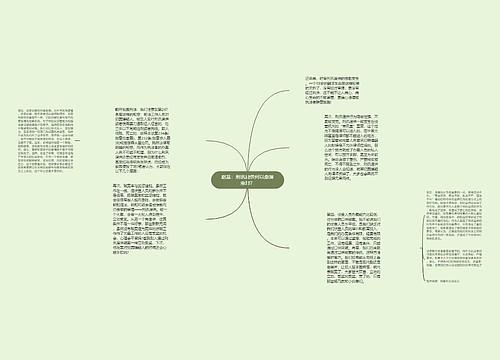李A奸杀少女、摔死3岁男童的行为无论从其作案手段的残忍还是直接后果来看,都赛过前段时间引起全国关注的药家鑫杀人案,一审判处李死刑,二审则改判死缓。云南高院解释改判的理由,一是基于少杀慎杀理念;二是其是由邻里纠纷引发的杀人案,此类案件社会危害不大;三是李有自首的表现,并积极赔偿;四是审判程序合法。
正是云南高院的这个改判解释,引发了公众的广泛质疑。不仅是普通的网民认为此四点理由很难说得通,包括一些法律界人士,乃至一些主张废除死刑的法学家,也认为少杀慎杀不适合这个案子。
公众之所以质疑此判决,其实还担心法官选择地理解和执行国家少杀慎杀政策。比如,几乎与李案同时,浙江高院将奸杀女警抢走其宝马车的3名男子均判死刑。在中国,如果被害者是国家公职人员,杀人者多半会被法院判处死刑。这种判决结果的细微差异使人们有理由怀疑,法官并不是一视同仁地执行国家的少杀慎杀政策。
但法官对死刑判决的自由裁量权也使得一些人呼吁废除死刑。要求废除死刑的另一理由是,现实中存在法院滥用死刑判决的现象。当然,呼吁废除死刑,更在于人权观念的进步。罪犯的人权也是人权,需要保护,即使一个人罪该至死,但只要有可能,也不应剥夺其生命。这与过去认为只要一个人犯了罪,其权利就不受法律保护的做法相比,确是进步很大。
就生命的一次性来说,在剥夺一个人的生命和权利时,必须慎之又慎,少杀慎杀,在法律的许可范围内,可杀可不杀的,不杀,直至在条件成熟时,最终取消死刑。但另一面,在死刑的废存问题上,要有一个正确的理解。取消死刑是对生命的尊重,而不是对罪行的宽容,罪行本身是不可宽恕的。换言之,取消死刑当且仅当与对生命的理解有关,决不意味着罪行可以宽恕或辩解。如果因为要尊重杀人者的生命,就连他犯下的杀人罪行也可宽恕,则陷入了另一种误区。
从废除死刑的一些国家来看,必有一种可替代性的措施来执行原先死刑对罪行的惩罚功能,比如“终身监禁”。像本案中的李A,数罪并罚,在一些国家也许会判处几百年的监禁,而且不得减刑和假释。但在中国,还没有发展出一套类似的替代规定,除死刑外,最严厉的惩罚就是死缓。然而,死缓的减刑和假释条件过于随意,只要在服刑期间表现得好一点,一般都能得到减刑,因此,一个人被判死缓后,实际等于有期徒刑。而有期徒刑的最长刑期是18年,若再表现得好一点,可以再减刑。所以,一些罪大恶极的罪犯但凡有可能,都会极力争取判死缓,最后,如果服刑期间积极表现,就有可能在监狱里呆上个10多年时间后出狱。这对受害者及其家属来说,显然不公正。从而客观上给人造成一种感觉,似乎取消死刑的呼吁,只是为了尊重和保护死刑犯的生命,而受害者及其家属的权利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这是少数精英废除死刑的要求不能赢得大众呼应的原因所在。
法律的本质在于公正,只有公正才能服众。无论是保留还是取消死刑,若不能做到公正,人们就会丧失对法律的信心。而公正的本质,按照中国哲学家赵汀阳的看法,是一个对称原则,即行为和报应的对称,付出与收益的对称,或者行为与回应行为的对称,中国传统的所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尽管随着时代的进步,社会不再提倡“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之类观念,更不鼓励个体的报复行为,但前提是法律必须为受害者伸张正义。如果法律做不到这点,就不要简单地去否定民间“杀人偿命”天理观的正义价值。因为“杀人偿命”的观念其实正是基于对社会公正的一种朴素的理解和期望。受害者家属要求法院能够秉公执法,判处杀人犯死刑,而不自己行复仇正义之举,恰恰是对法律能够主持正义的一种信赖。站在受害者家属的角度,对此理应抱以同情和理解。
“公正”的价值体现在刑法中,就是“罪罚相当”,这是刑法一个基本原则。它的含义是,轻罪轻罚,重罪重罚,轻重适度,罪刑相当,罚当其罪,不枉不纵。法官在具体判案时,无论是基于人道考虑,还是其他原因,只能在这个原则的前提下去裁量,不可逾越这一原则,否则,就会造成枉判,制造不公。
因此,在社会还未准备好替代条件去取消死刑的情况下,对少杀慎杀政策的把握要准确,准确包括两个方面,可杀可不杀的不杀,但同时也就意味着,该杀的必杀。不能只强调前一面而忽视后一面。事实上,中国最高院对死刑的适用条件是,罪大恶极,以及证据充分不允许出错,符合这两个要件的,都属于必杀之列。本案中,唯一可以不判李死刑的理由是他得到受害者家属的谅解,可惜受害者家属没有选择谅解他。
社会之所以要法官,是因为人们相信,法官能让这个社会变得更公正。法官的这个作用是通过具体案件的判决体现出来的。所以,法官判案,的确不能被舆论和社会情绪所左右,但也不能刻意为保持判案的独立性而罔顾基本的民心和道义,否则,很难谈得上公正。而一个不公正的判决,只会使人们对法律和法官群体更疏远、更怀疑。

 U582679646
U582679646
 U882673919
U8826739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