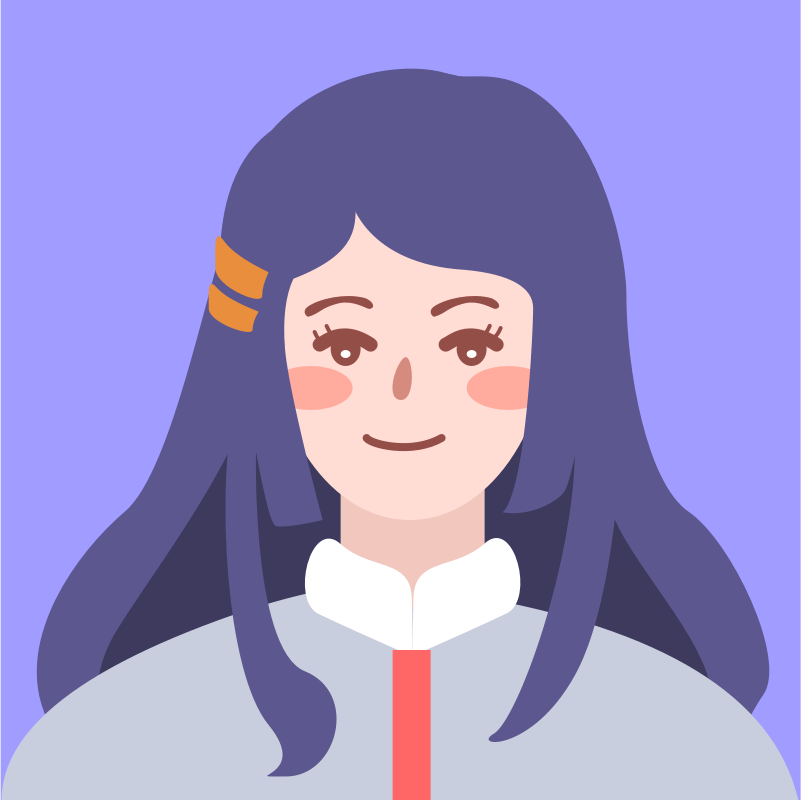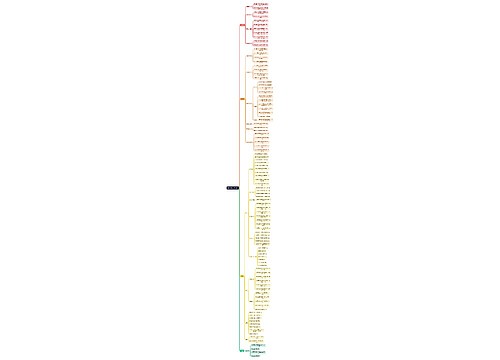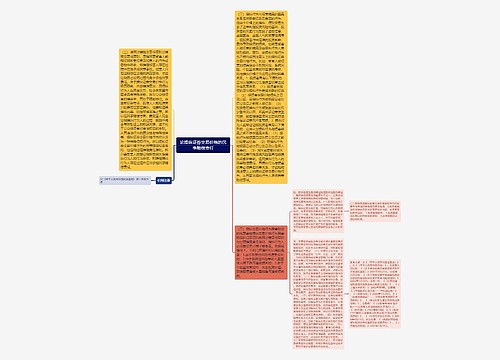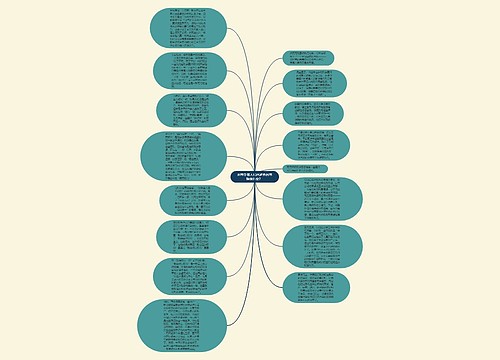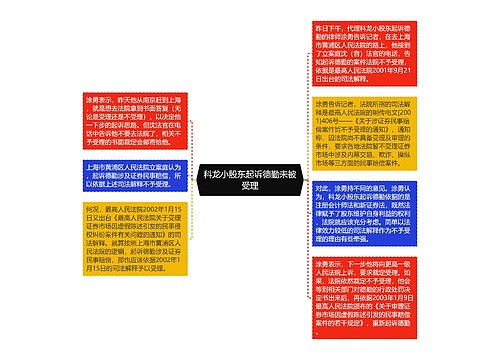草案关于民事赔偿部分的规定只有一句话:“经营者违反本法规定的行为给他人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损害赔偿等民事责任。”这一规定在立法理念上没有认识到垄断损害与传统侵权损害的重大差异,以及这些差异对损害赔偿制度设计的不同客观需求,把传统侵权法中的填平损失原则应用于反垄断损害,其结果是不能对受害人提起赔偿之诉形成足够激励,基本上不具备可实施性。
垄断行为与传统民法中的侵权损害相比,主要有两个显著差异:在受害主体的数量方面,一般侵权受害人多为数量有限的特定人,垄断损害的受害主体当中有特定人,但主要还是某行业领域中的不特定经营者,以及这些经营者的相关利益人,而且垄断损害通过这些主体像涟漪一样向周围渐次传递,形成损害的“涟漪效应”,使得受害人数量庞大;在损失计算方面,由于市场状况瞬息万变,原告要证明自己受到垄断损失的额度相当困难,从国外反垄断司法实践来看,垄断损失计算过程须借助大量市场数据的采集汇总、数学模型的复杂运算和经济学专家的证人证言。
垄断损害与传统侵权损害的上述差异,导致了三个“稀少”:第一,受害人在垄断损害赔偿之诉的举证难度,远高于一般侵权损害,胜诉的希望更加渺茫,所以具有起诉意愿的受害人稀少;第二,反垄断诉讼所需的成本远高于一般侵权损害,所以具备起诉财力的受害人稀少;第三,上述两个“稀少”的彼此叠加,使得实际被追究垄断损害赔偿责任的人稀少。上述三个“稀少”是一切国家和地区的反垄断法都面临的困局,要破解它,就必须关注赔偿之诉的成本收益问题,使制度设计能够让受害人基于理性判断,认为有足够的激励去起诉垄断者,使经营者基于理性判断,认为有足够的激励去遵守反垄断法。
按照反垄断法草案的规定,受害人提起赔偿之诉的收益以其所受损失为限。而诉讼成本高、胜诉概率小是反垄断案件的特点,所以受害人的预期收益(可能获得的民事赔偿金)远远小于实际损失、诉讼成本之和。受害人缺乏追诉激励,宁愿自行承担垄断损失也不愿提起反垄断民事诉讼。
违法者在面对受害人提起的民事赔偿诉讼时,败诉的概率远远小于1,所以因败诉支付的民事赔偿金少于其预期违法收益。哪怕每一名垄断受害人都提起民事赔偿诉讼,违法者也仍然有预期违法净收益。由此可见,反垄断法草案在没有为受害人提供足够追诉激励的同时,反倒为加害人提供了继续违法的激励。
如果反垄断专司机关的执法活动能够有效抑制垄断行为,那么民事责任制度是否可行其实倒不重要。但是,若单一依赖行政执法,反垄断法的实施效果将令人堪忧。专司机关执行反垄断法最大的局限性,在于其人力资源有限、办案经费受到财政预算的约束。在其工作人员数量、年度预算和办理每一起反垄断案件的执法成本固定的情况下,其一年最多能够办理的案件数量也就是固定的,超出这一固定数量的垄断案件,就是执法机关力所不及的部分,即违法者逍遥法外的安全空间。可想而知,垄断违法案件越多,违法者逍遥法外的空间就越广阔。
从世界上许多国家或地区的反垄断立法和司法经验来看,如果损害赔偿制度不可行,那么整部反垄断法的实施效果都会成问题。以日本为例,尽管卡特尔普遍存在,但从1947年颁布禁止垄断法至1994年这47年间,共发生过6起反垄断民事诉讼,而且没有一起案件原告胜诉。其禁止垄断法几乎全部依赖公平交易委员会的执法活动,但执法状况很不理想,至于“一只从来不叫也不咬人的看门狗”就成为日本国内外嘲讽日本公交委的一个习语。
与此形成极其强烈对比的是,美国反垄断法实施3倍赔偿原则,即胜诉的受害人可以获得3倍于其实际损失外加诉讼费和合理的律师费。这种具有惩罚性的赔偿制度有两种突出功能:一曰补偿,二曰威慑。其中最具特色的当属威慑功能,即:使潜在的违法者惮于不法行为败露的可能性和招致的不利后果,从而自我抑制不从事违法行为的作用。芝加哥学派领军人物、法经济学和反垄断法著名学者波斯纳认为,反垄断法救济制度的主要目的就在于威慑违法行为。
痛感日本反垄断法民事赔偿制度之弊的竹内昭夫先生,在其《私人在法实现中的作用》一书中有一段振聋发聩的评语,用在这里再合适不过:“一个国家法律制度,如果只能在诉讼人豁出去的时候才能运转,那就不是好的制度。换句话说,法律制度要等到堂·吉诃德这样的人物出现才能运作,那么,法律界人士还能无动于衷吗?一般老百姓并不认为自己的权利意识低,他们只不过拨拉一下算盘,觉得经济上不合算,所以才不去利用这个制度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