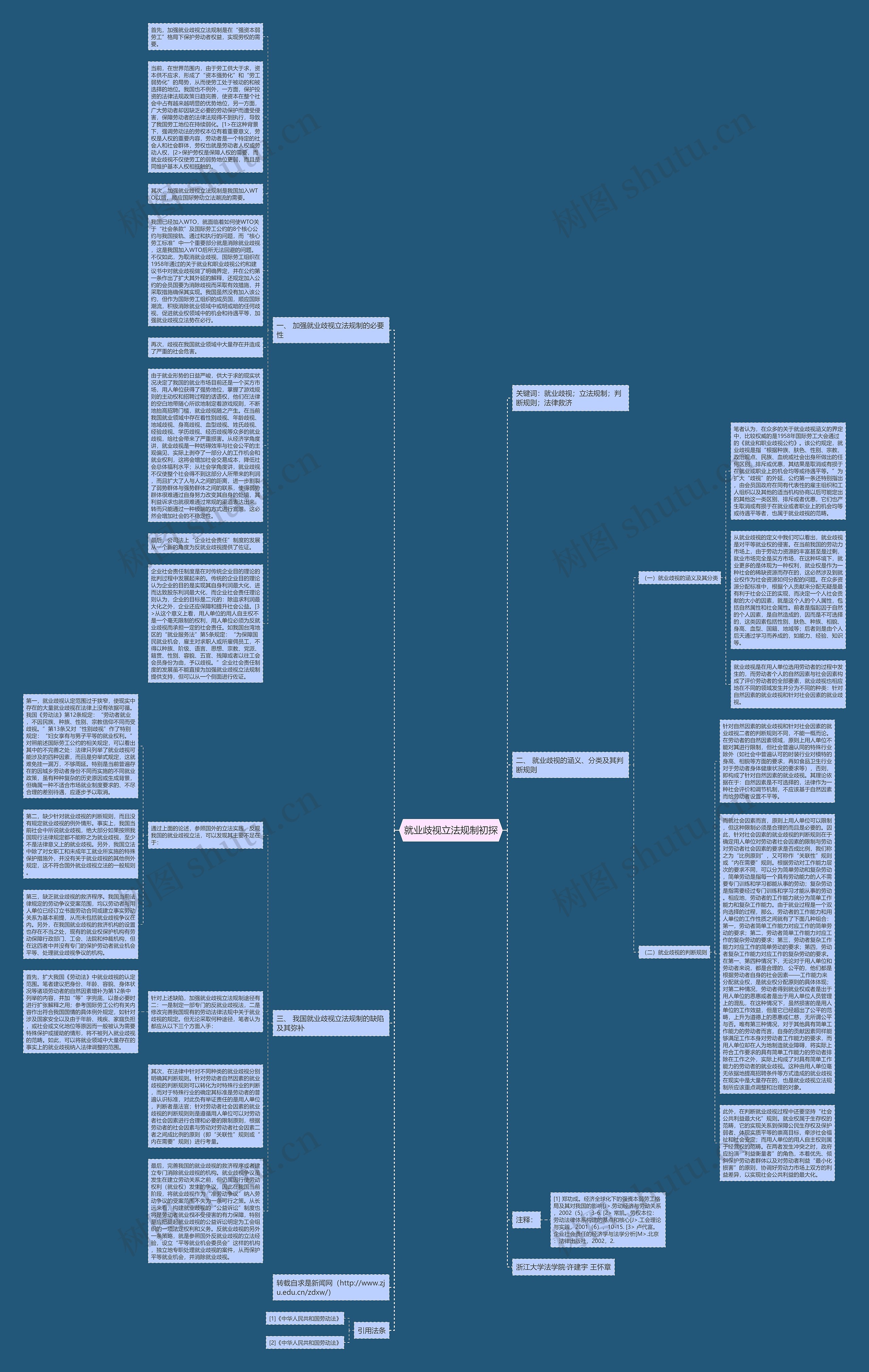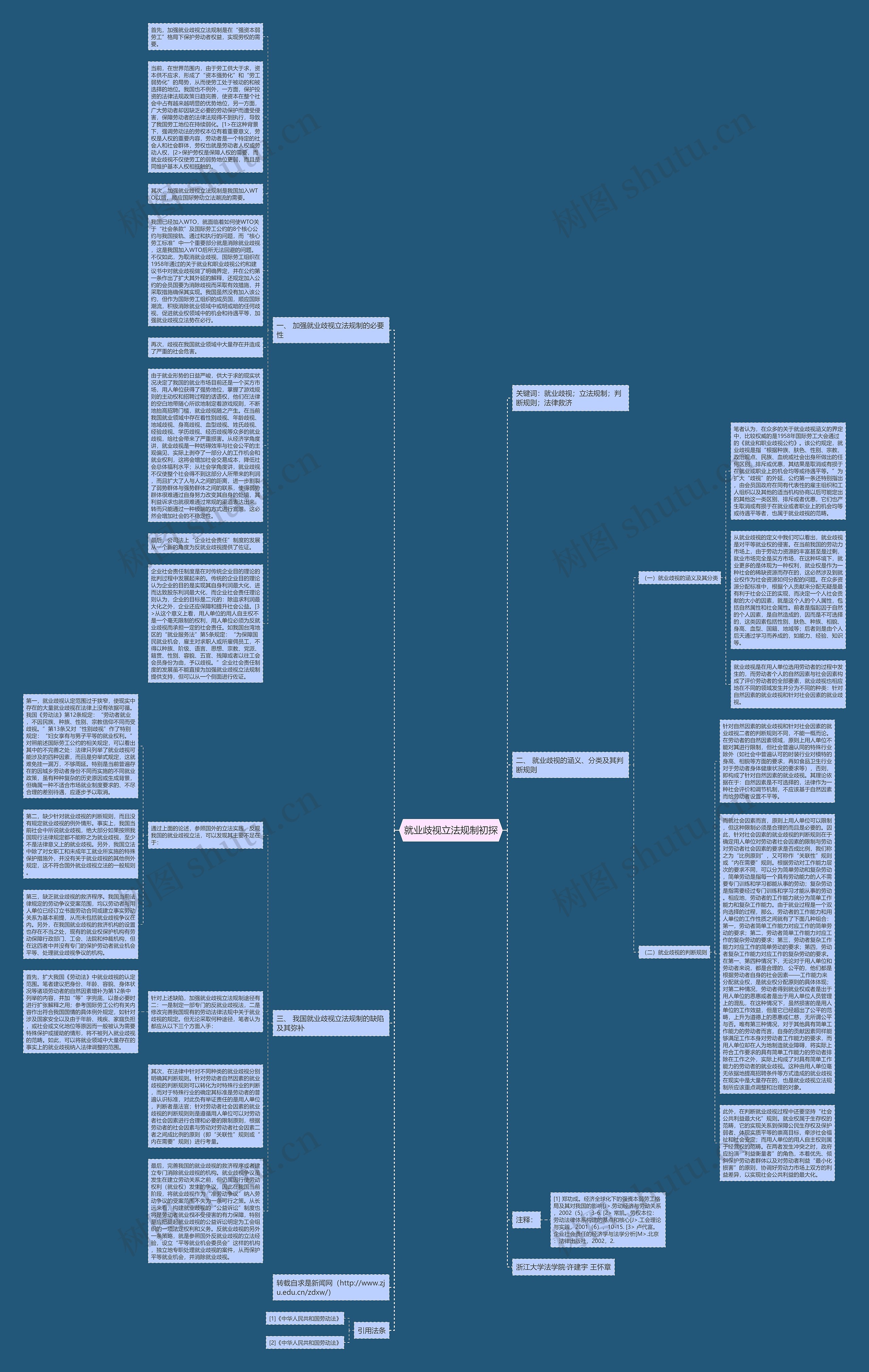首先,加强就业歧视立法规制是在“强资本弱劳工”格局下保护劳动者权益,实现劳权的需要。
当前,在世界范围内,由于劳工供大于求,资本供不应求,形成了“资本强势化”和“劳工弱势化”的局势,从而使劳工处于被动的和被选择的地位。我国也不例外,一方面,保护投资的法律法规政策日趋完善,使资本在整个社会中占有越来越明显的优势地位,另一方面,广大劳动者却因缺乏必要的劳动保护而遭受侵害,保障劳动者的法律法规得不到执行,导致了我国劳工地位在持续弱化。[1>在这种背景下,强调劳动法的劳权本位有着重要意义,劳权是人权的重要内容,劳动者是一个特定的社会人和社会群体,劳权也就是劳动者人权或劳动人权,[2>保护劳权是保障人权的需要,而就业歧视不仅使劳工的弱势地位更弱,而且是同维护基本人权相抵触的。
其次,加强就业歧视立法规制是我国加入WTO以后,顺应国际劳动立法潮流的需要。
我国已经加入WTO,就面临着如何使WTO关于“社会条款”及国际劳工公约的8个核心公约与我国接轨、通过和执行的问题,而“核心劳工标准”中一个重要部分就是消除就业歧视,这是我国加入WTO后所无法回避的问题。不仅如此,为取消就业歧视,国际劳工组织在1958年通过的关于就业和职业歧视公约和建议书中对就业歧视做了明确界定,并在公约第一条作出了扩大其外延的解释,还规定加入公约的会员国要为消除歧视而采取有效措施,并采取措施确保其实现。我国虽然没有加入该公约,但作为国际劳工组织的成员国,顺应国际潮流,积极消除就业领域中或明或暗的任何歧视,促进就业权领域中的机会和待遇平等,加强就业歧视立法势在必行。
再次,歧视在我国就业领域中大量存在并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危害。
由于就业形势的日益严峻,供大于求的现实状况决定了我国的就业市场目前还是一个买方市场,用人单位获得了强势地位,掌握了游戏规则的主动权和招聘过程的话语权,他们在法律的空白地带随心所欲地制定着游戏规则,不断地抬高招聘门槛,就业歧视随之产生。在当前我国就业领域中存在着性别歧视、年龄歧视、地域歧视、身高歧视、血型歧视、姓氏歧视、经验歧视、学历歧视、经历歧视等众多的就业歧视,给社会带来了严重损害。从经济学角度讲,就业歧视是一种妨碍效率与社会公平的主观偏见,实际上剥夺了一部分人的工作机会和就业权利,这将会增加社会交易成本,降低社会总体福利水平;从社会学角度讲,就业歧视不仅使整个社会得不到这部分人所带来的利润,而且扩大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进一步割裂了弱势群体与强势群体之间的联系,使得弱势群体很难通过自身努力改变其自身的处境,其利益诉求也就很难通过常规的渠道表达出来,转而只能通过一种极端的方式进行宣泄,这必然会增加社会的不稳定性。
最后,公司法上“企业社会责任”制度的发展从一个新的角度为反就业歧视提供了佐证。
企业社会责任制度是在对传统企业目的理论的批判过程中发展起来的。传统的企业目的理论认为企业的目的是实现其自身利润最大化,进而达致股东利润最大化,而企业社会责任理论则认为,企业的目标是二元的:除追求利润最大化之外,企业还应保障和提升社会公益。[3>从这个意义上看,用人单位的用人自主权不是一个毫无限制的权利,用人单位必须为反就业歧视而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如我国台湾地区的“就业服务法”第5条规定:“为保障国民就业机会,雇主对求职人或所雇佣员工,不得以种族、阶级、语言、思想、宗教、党派、籍贯、性别、容貌、五官、残障或者以往工会会员身份为由,予以歧视。”企业社会责任制度的发展虽不能直接为加强就业歧视立法规制提供支持,但可以从一个侧面进行佐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