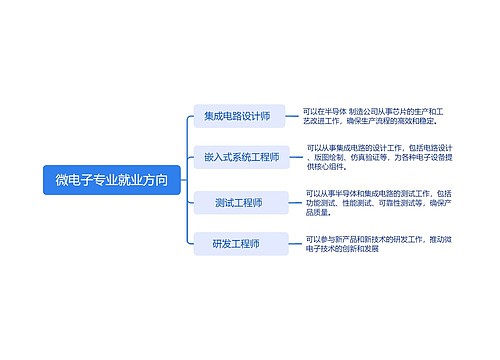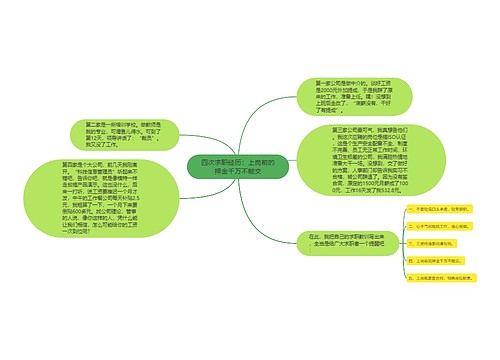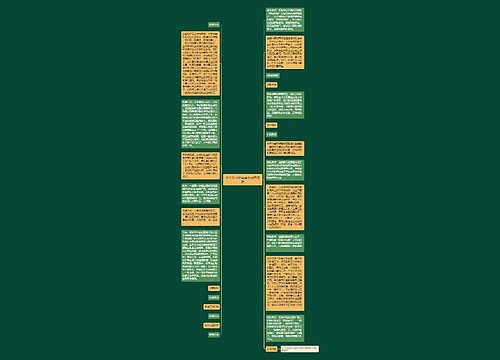诚然,用人单位在血型、属相、姓氏等与工作无关的项目上设槛,令人愤愤不平,然而对岗位的“性别、年龄”要求也算歧视,却有些匪夷所思。什么是“歧视”,究竟有没有清晰的界定?以劳动力市场竞争之激烈,消除歧视又如何可能?
在严峻的就业压力之下,2007年新一轮求职大战再度打响,怎样创造一个公平和谐的就业环境,恐怕需要求职者、招聘方乃至相关部门等各方面冷静下来,理性思考。
主持人:课题组的调查数据显示,多达85.5%的人感到找工作时受到歧视,与您说的“集体无意识”岂不是自相矛盾?
蔡定剑:被歧视感,与对就业歧视的权利意识,是两个不同的层面。调查数据只是作为求职者的感受,这85.5%的人如果成为雇主,很有可能也会采取同样的歧视行为对待他人。有时候人们感到受过歧视,并不代表就能站在一个公正的立场上,对歧视有清楚认识。事实上,提出“反就业歧视”之后,我听到不少反对意见,最受认可的观点就是,在市场经济、竞争社会中,“性别、年龄、学历”等作为优胜劣汰的竞争条件,让用人单位挑挑拣拣无可厚非。全社会都默许了这些现象的发生,并习以为常。对自身拥有的公平就业权,究竟包含哪些内容,应该公平到什么程度,大多数人并没有概念。树立正确的就业权利意识,是人们当下急需补上的一课。
我国已批准加入的国际劳工组织《1958年就业和职业歧视公约》对就业歧视作了明确界定,简单点说,就是不能以种族、肤色、性别、宗教、民族血统、社会出身、政治见解等原因,给人的就业和职业机会平等造成不利损害,除非职业本身有内在需要。通常“先天条件”是最严厉禁止的歧视。这是宪法保障的“人人平等”的权利,没有人能够抹杀。但有些用人条件,比如年龄、身高等,确实涉及企业的人力资源成本,与企业效率有关,在国外审查标准也比较宽松。然而宽松并不意味着允许任意设限。举个案例:考虑到体力要求,荷兰足协曾规定裁判年满45岁必须退休,结果却被告歧视,而且经法院审理败诉了。其败诉理由是,既然足协每年都有体能检测,可以更准确、更直接地鉴定员工是否符合职业要求,那么以年龄来限制裁判就业显然就是不合理的,属于歧视行为。
不难发现,当就业歧视成为某个行业的个案时,判断歧视与否还是要看具体的就业条件与职业要求是否必然冲突。比如学历要求,以此招聘家教是合理的,招聘家政保姆就有歧视之嫌了。所以,除了法律规定的硬约束,离开对具体岗位的要求,是否属于歧视很难一概而论。大众的常识判断,对公平就业影响深远。宣传反就业歧视,就是希望更多的人能了解一个在我国还没有成为常识的常识:平等权是基本人权,每个公民拥有的公平就业权,其实大得超乎我们的想象。
主持人:然而企业完全可以只做不说,在一轮轮考试中隐性筛选求职者。就业条件与岗位竞争之间的冲突,在现实中仍然难以界定。您不认为法律手段最后很可能沦为一纸空文吗?推进反歧视的可操作性在哪里呢?
蔡定剑:企业只做不说,被称为隐性歧视,世界各国都有可能出现这类情况。这是再严苛的执法,都难以消除的,但有一点却可以做到,那就是一旦有求职者上诉,司法应该给予他告赢的机会。国际上比较通行的做法,是实行举证责任倒置,由雇主方来证明自己选择甲而不选择乙的理由足够充分。这对求职者非常有利。一旦雇主方败诉,罚款金额非常之大,动辄几十万,甚至几百万。所以在国外,雇主设置岗位要求、对待招聘条件和流程,极其谨慎。你可以翻一张国外的报纸看看,招聘广告上,几乎找不到年龄、性别、种族、婚姻状况的只言片语。
很多人都认为反歧视影响单位的择优用人权。其实,就业公平与择优录用没有必然的矛盾,而且有利于敦促单位不拘一格选人才,促使企业最大限度地开放就业机会。
制度层面上,中国反就业歧视的突破口,不仅在于立法,还在于建立解决纠纷的机制。我们不完全缺乏条文,宪法、劳动法等对歧视有相关规定,缺的是,状告无门。只要有部门能够受理此类诉讼,受害者一开始虽然很难打赢官司,但随着时间推移,一旦有一例成功,那必然会对整个行业标准产生敲山震虎的影响,提升全社会权利平等和尊严意识。
主持人:就业歧视,如果从2003年“乙肝歧视案”算起,进入公众视野已经4年有余,别说按性别、年龄,甚至按星座、血型、属相来设置门槛的都大有人在,且越演越烈。劳动力市场竞争越激烈,类似事件就越难避免,课题组在这个时候起来号召公平,究竟出自何种考虑?
蔡定剑:现代社会要实现公平,有两个领域最为关键:其一是教育机会公平,其二就是就业机会公平。如果没有后者,优秀人才找不到工作,社会不能人尽其才,那么教育公平也是白费。
西方社会的就业平等机制,也是上世纪70年代才建立发展起来的。欧盟对就业平等的重视,来自它想推进欧洲经济一体化的目标,为了推进市场的一体化,不可避免需要劳动力条件和标准的相对统一,给予劳动力市场不分国别的公平就业机会。可见,就业平等权的提出和发展,不是一蹴而就的,它与当前经济发展程度和想要解决的社会问题息息相关。